文|毒眸
《异人之下》再次播出后,许宏宇接连发了十几条微博,“我很好奇,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异人之下复播了!”
前段时间,许宏宇在微博介绍了“热血动物联盟”的新成员,一只叫14的小猫。评论区挤满了等待复播的观众,他挨个回复大家。“辛苦,但坚持着,等我们一下。”
《异人之下》的出现,既是偶然,也像是许宏宇经历过思考、转向,进入了某些人生修行后,人生道路和职业生涯所产生的交汇点。
决定拍这部剧后,他成立了公司,厂牌取名“热血动物”,意为“一场志同道合暖热相宜的结伴逍遥”。这个厂牌集结了一批和他同样热爱青春热血题材的创作者,誓言“要丈量无数个宇宙”。
而在丈量这些新的宇宙之前,许宏宇所做的事情,是寻找。
2020年春节前,许宏宇回到香港,一连在家住了好几个月。自大学毕业后离家以来,这是他头一次在香港住这么久。
世界瞬息万变,人们却被迫安静了下来。在那段时间里,许宏宇开始向内寻找,并思考:“接下来拍什么?”
对许宏宇而言,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每结束一部戏,这问题就会出现在他的脑海中。
2017年,《喜欢你》上映后,许宏宇从默默无闻的剪辑师,成为备受瞩目的新锐导演。很多项目找过来,他形容自己像是“小朋友走进糖果屋”,不知道选哪个才好。
那段时间里,许宏宇接连拍了几个短片,主题大都是对内心的探寻和对自我的确认。拍完《穿越火线》后,他又花30天拍了《一点就到家》,讲一个在外漂泊的人回到家乡、寻找自我的故事。
与自我对话,从中寻找新的表达,是许宏宇多年独处养成的习惯。做了十年剪辑,时常身处小黑屋,几天不出门、不跟人说话、只对着电脑,虽然孤独、但也激活了他向内探寻的通道。
每次这样思考过后,新的表达方向便会解锁,上一次是《穿越火线》,这次是剧版《异人之下》。
许宏宇爱讲“与众不同”的人:不同世界却陷入爱情中的两人,与乡村格格不入的创业者,用游戏感受热血青春的人和群体,“异人”……而这,或许正是许宏宇当下的注脚。
谁说孤独的异类,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热血动物”呢?
闯入“异人”世界
彭昱畅是《一人之下》的忠实推广者,在拍《一点就到家》时,就反复跟许宏宇念叨,推荐他一定去看。加上鹿晗也向他力荐,对这个故事的好奇,便种进了许宏宇心里。
电影拍摄进入尾声的某一天,许宏宇从剪辑房出来,拉着同事一起,打开了第一集。一口气看到大半夜后,他心里便有了决定:就拍这个。
那是一种久违的、遇到好故事的兴奋感。
《一人之下》的文化根基,及对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语境下的呈现,让他产生了“研究”的冲动。“它用了很新鲜的方式去呈现传统文化,我觉得很厉害,有点东西。”
兴奋的另一面,是可预测的难度与压力。原著有着相当数量的忠实读者,他们期待又害怕看到自己喜爱的故事被搬上荧幕。剧版《异人之下》看片会后,有原著粉开玩笑,“当时看到要出剧版,其实是不太高兴的。”许宏宇马上回应,“对不起,对不起。”

对于喜欢《一人之下》的人来说,下意识的“反对”是一种保护,“他们在保护这个世界,”许宏宇深知这点,“当我要从另外一种角度切入时,我能不能对得起他们?”
他想读懂他们喜欢《一人之下》的原因。
剧本创作前期,他和编剧团队在B站联系了很多喜欢《一人之下》的UP主,开了场交流会,听他们分享对原著的解读与感受。
即便抛开这个项目本身不谈,许宏宇仍然认为那天对他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人生时刻”。
和一群90后、00后坐在一起,感受他们纯粹的热情、新鲜的想法和蓬勃的创造力,这让许宏宇第一次直接地看到了“时代赋予年轻人的一种可能性”。
对于批评和质疑,许宏宇也愿意接受,“我想说,我们没有忽略他们(原著粉),可能这次还是差一点,下次会做得更好。”但都不足以让他放弃,如果遇到一点阻力就停下来,“谁还敢去拍漫改呢?”
“可能不是所有人都爱看漫画,但我又希望这么好的故事能被更多人看到,”许宏宇解释,“也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国漫真的有很多好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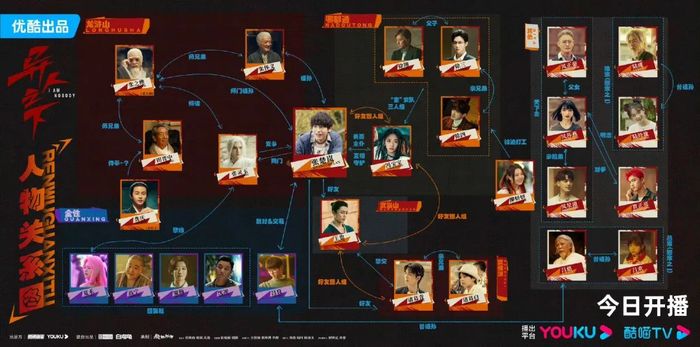
“所以我觉得不要叫漫改吧,”许宏宇停了一瞬,纠正了这个大众熟悉的表达,“‘漫改’好像是说我把大家很珍视的漫画拿来改掉了,其实不是的,是把这个故事放在真人的语境下去讲述。”
《异人之下》播出后,有不少包括原著粉在内的观众,都在社交平台上表达了对剧集改编方向的认可。或许比起“漫改”,更准确的词语应当是“有机还原”:既有创新,也保留了原著的精神内核。
决定启动这个项目后,许宏宇一直在问自己,“你到底懂不懂,这里头讲的是什么?它的‘魂’是什么?”对他来说,如果这个答案找错了,那么即便复刻了名场面,还原了造型,仍然算不上成功。
《一人之下》最初的名字是《异人》,‘THE OUTCAST’,原义“被排斥者”。这是许宏宇读到的“魂”,“每个人都有一条不同的道路,我们能不能找对自己的经历,在得到这份能力的时候,我们该怎么用,做什么。”
这与在龙虎山拍戏时,道长们带给他的感受有些相似。一位师傅告诉他:“不是我有多大的本事给人调理身体,只是上天给了我这个能力。”
龙虎山是《一人之下》原著的主要发生地之一,能在那里拍摄,被其道场接纳,这对许宏宇和团队而言很重要。“你们拍这个戏,是做好事情,那我也会帮你。”那位师傅告诉他。
《异人之下》的英文名是“I am nobody”,某种程度上,也暗合了他的理解。
回想那段日子,似乎有种奇妙的力量感,始终环绕在他们身边,一切都推进得很顺利,氛围也“很不一样”。虽然连续拍了几个月,每天只睡几个小时,但“所有人的状态都很热烈”。
剧版开播第一天,许宏宇罕见地更新了朋友圈,“感谢天师,感谢天地,感谢龙虎山。”
遇见这样的机缘,许宏宇觉得自己很幸运,但同时,他也是努力的,“我要做的就是拍好的作品,而所谓的‘好’,可能要用一生去寻找和努力。”
寻找
在寻找“好作品”之前,许宏宇花了一些时间,去理解电影的意义。
在史蒂芬·斯皮尔伯格的半自传电影《造梦之家》里,年仅6岁的法贝尔曼在电影院完成了他的“观影初体验”。每个人感知电影的起点都不同,这让许宏宇开始回想自己的“起点”。
直到进入大学之前,许宏宇都没觉得自己会成为一名导演。他是理科生,中学时和大部分高中男生一样,玩乐队,加入游泳队,学无聊的数学,背梯形面积和三角形面积的计算公式。“现在谁在日常生活中需要算三角形面积?”
考上香港城市大学之后,在师姐的推荐下,他选择了创意媒体学院。从平面开始,走进了影像的世界。
选择这个方向的大都是艺术生,初次上课,大家破冰的话题是“你最喜欢哪位导演?”许宏宇显得格格不入,“我不知道都有什么导演,有人说最喜欢希区柯克,我都不知道是谁。”
《造梦之家》里,法贝尔曼的父亲伯特这样给儿子解释电影的概念:“……就像一个巨大的手电筒发出亮光,这些照片在灯光前一闪而过,跑得快极了,每秒钟二十四张照片!在你的头脑里,每张照片能停留十五分之一秒。”
许宏宇理解电影,也是从每秒钟的那24张照片开始。很多瞬间只靠肉眼是没办法捕捉到的,必须借助机器。“就好像一匹马在跑,如果它不是变成单帧的画面,我们可能看不到它有一个瞬间是四条腿都离开地面的。”
现在回头去看,接近这些瞬间的过程,构成了许宏宇感知电影的起点。而此后接触的移动影像,则放大了这种感知。
拍照的时候,咔嚓一下,画面就定格在那里,完成一个瞬间的记录。而当摄像机动起来的时候,画面一下子“活”了,所有的东西都被赋予了一种生命感。“我们叫moving image,就是移动影像,它只是一张影像,但是里面可以有无数变化。”
后来,他经朋友介绍进入陈德森导演的剧组。进入电影行业之后,这种感知又再次被放大。此前,大学时期的现代艺术教育屏蔽掉了“人”的存在。承载这一切的媒体才是主角,在画布或是相机里,人和一朵花、一棵树没有区别,都是“被拍摄的对象”。
从事电影行业后,许宏宇发现自己“更关心人类”了。
《异人之下》里,太师对王也说:“有因才会有果,但并非所有的因,都在你的意识之中,世间万物皆是因。”而这,也是影像对许宏宇最大的吸引力。

“人与人的相遇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两个人会莫名其妙地相爱?”在他的眼里,一部戏的主角为何选择走入某种挑战,又将怎样与世界发生碰撞,这些不是剧本里写好的故事,而是命中注定的因果。探寻这种因果的起源,是许宏宇影像的母题之一。
获取知识很容易,人工智能如今已经有能力解决大部分问题,而拥有细微的感受却很难。
许宏宇寻找这些答案,不是从导演、剪辑师或创业者视角出发,而是“人类”。“我用什么身份做电影?用人类的身份吧,如果说有什么是我们这个物种不可替代的东西,那可能就是情感。”
“小黑屋”
公众人物在大众眼里的人生是非线性的。大家更熟知的故事总会被摆到台前,拉得很长,而成名前的那个部分,却被浓缩进百度百科,成为“前情提要”。
大学毕业后,一门心思想要“做电影”的许宏宇经朋友介绍,加入了陈德森导演的团队。虽然是生活助理,但好歹是跟电影有关的工作。“不管了,我心想,先去吧。”
陈德森的公司在尖沙咀,车位很难找,在成为助理的头几个月,许宏宇的主要工作就是帮他停车,跟在他身边旁听大大小小的会议。
现在看起来很常规的工作流程,在当时的许宏宇眼里都很新鲜。“感觉像是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原来他们是这么理解影像的,要聊一个人的背景、人设,要写人物小传,聊分场和故事。”
2006年,许宏宇离开香港来到内地,在一部中美合拍的电影里担任副导演。虽然是副导演,但他在剧组几乎什么都做,从灯光、录音,到摄影、制片,因为普通话还很不标准,有时候大声说话,都没人理他。
许宏宇职业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次转机,是和陈可辛的相识。他进了《投名状》的剧组,一开始是担任拍摄纪录片的工作,后来因为素材太多,被剪辑组喊去帮忙。陈可辛看了一段许宏宇剪的戏,决定让他加入《投名状》的剪辑团队。
这是许宏宇剪的第一部长片。从这里开始,许宏宇走进了一个令他愉悦的新世界。
在剪辑室的那段岁月,对许宏宇来说深刻而强烈。剪辑不是标准的团队工作,大部分时候不需要和其他人交流。“很多时候我好几天都不跟任何人说话,就只是对着电脑。”
一天的工作,并不是从坐在电脑前那一刻才开始,而是从睁开眼睛的那一秒。
“就像我今天要剪一场李连杰的戏,从起床开始,到坐上公交车,那段时间其实就已经在剪了。坐在电脑前的时候,其实要做的只是把脑子里的东西放出来而已。”
剪辑室的感觉,像一个“小黑屋”。
十年身处小黑屋,许宏宇的感受是孤独的。不过,那种满脑子只想一件事的状态,至今都让许宏宇觉得珍贵。
有某几个瞬间,许宏宇觉得自己好像会魔法,在剪辑室内限时生效。“剪辑室是比片场更神奇的地方,在现实里,我们是被动的,是连贯的,但在剪辑台上,一切都可以重新选择。”
许宏宇一直认为,好的剪辑师也是好的创作者,一切都可以打碎重组,诞生新的故事。“就好像我们现在坐在这里聊天,但第一个镜头要给谁呢?谁先开口?还是说我们就这样坐着,很久都不说话?”
这种选择严格来讲没有标准,也无法从任何教科书上习得,只能依赖于剪辑师对故事和画面的感受。“先从全景开始,切近景,再移到这儿,”许宏宇边说边比划着,“这样有什么意思呢?套路化的剪辑是没有生命的。”
这或许是许宏宇的某种天赋所在。陈可辛在很多场合提起他的这位御用剪辑师时,都会用“天才”来形容。天赋与努力不是反义词,在剪辑室孤独作业的夜晚,帮助他一步步解锁了这种天赋。
这段孤独而漫长的暗房岁月,以身份的转换暂时画下句点。现在的许宏宇仍然会做一些剪辑的工作,但他参与影像的主要身份,已经从剪辑师变成了导演。
在刚入行的时候,有工作人员跟他说,“你是不可能做导演的,你的想法不够天马行空。”
此后十多年,他一边躲在“小黑屋”里,一边尝试证明这个观点的错误性。“为什么不可以呢?很多东西都在我的脑海里,只是我还没有能力和机会去呈现。”
时间来到2017年,导演许宏宇的第一部电影《喜欢你》上映。
在正式公映前,《喜欢你》在大学生电影节上第一次向公众放映,在一个能容纳几千人的放映厅。电影放到一半,许宏宇从后门偷偷溜进去,观察观众的反应。
“可能是一些特别俗套的情节吧,但大家都笑得很开心,”他已经不记得大家因为什么情节而笑,但他一直记得自己在那一刻的感觉,“我站在边上,眼泪就流了下来。”
“不是觉得自己的辛苦被确认了,我只是觉得太迷人了。”那是许宏宇最喜欢的时刻。在《异人之下》的映后,他又表达了这个观点,“看到大家看片的投入感 ,是作为导演永恒的动力。”
“不是拍来拿奖的,是拍给观众的”
对观众感受的重视程度,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导演会走怎样的路。
许宏宇的选择似乎已经偏向于市场化,尽管他对电影的初印象,是从艺术片开始的。甚至读大学时,“反好莱坞”是他世界的主流,“大家都觉得好莱坞电影是不好的,电影不应该是那样的。”
市场化还是自我表达?这个对于大部分导演而言的灵魂拷问,对许宏宇而言,却并非最难的问题。对他来说,选择成为导演,第一个难关是得先“走出那间暗房”。当然,走出来的过程,也是他解这一题的过程。
做剪辑时,一周需要交流的人不超过三个。而成为导演,意味着要为作品的全部负责,每天都要和很多人说话,处理剧组的一切大事小情,回答各种不同的问题,做所有决定。
许宏宇对自己的影像表达有自信,但他并不确定自己能否成为一个剧组的“领导者”。那个阶段,陈可辛成了他的“模仿对象”。
在《喜欢你》的片场,许宏宇会观察陈可辛,看他如何与人沟通,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像小朋友学父母说话一样。”以至于拍完《喜欢你》后,身边有很多人跟许宏宇说,他有时说话都“有点像陈导”。
他从陈可辛身上习得的,不是简单的“沟通技巧”,还有电影工业的运转方式:只有将自己的想法精准地传递给能帮助他的每个人,才能够诞生一部好的作品。因此,《喜欢你》的另一位监制许月珍觉得,培养许宏宇成为导演的,不是他们俩,而是电影工业。
“电影是艺术,但也不完全是艺术,除非你是个天才,”在许月珍看来,只有拍艺术片的人才是天才,一旦进入电影工业,需要说服这么多人,带领好几百人完成一件事,“天才才不想和别人沟通那么多,我不太相信电影工业里有天才。”
成为导演之前的诸多经历,帮助许宏宇快速地融入了电影工业。许月珍评价他是“懂得观众期待”的那类导演,因为他从纪录片拍摄和电影剪辑入行,有高度的“服务意识”,这让他成为一个“目标更清楚”的人。
第53届金马奖公布入围名单时,《七月与安生》总共获得了7项提名。当时,许宏宇和陈可辛在《喜欢你》的剧组,陈可辛跟他说,“你别想了。每个戏都不一样,你这个戏更多的是商业片,不是拍来拿奖的,是拍给观众的。”
这话或许在许宏宇心里早早种下了种子,助他完成了某种“自洽”。拍完两部电影后,许宏宇开始拍网剧。
《穿越火线》是一种尝试。和电影不同,在许宏宇看来,剧中人的生命会被拉得更长,观众的参与度也更高。
不同于走进电影院,坐下来看完一整个故事,剧集的观众在某种程度上拥有选择权,可以选择跳过、快进或重复,也可以只看自己感兴趣的故事。“我只是把我的创作给到他们,他们有权利选择只看吴磊还是只看鹿晗。”
不过,考虑观众的需求,并不意味着许宏宇远离了自我表达。相反,当下的他把更多的时间花在思考自己身上。拍戏之余,他在进一步寻找“我是谁”,而这个阶段的寻找和短片时期不同,他似乎正进入另一维度。
大多时候,他选择顺从自己的灵感,对他来说,导演像一个“接口”,连接电影之神和时间,给一部作品找到它的魂。但当面临下一个故事的选择时,他又会选择将自灵感与诸多故事进行匹配,再得到“最优解”。
“很多事情都不是极端的,但如果一直摇摆,就没办法看清自己的位置,”这个时候,他希望自己能安静下来,先看看自己,“很多时候我们的价值都是被外在定义的,父母、老师和老板为我们制定标准,但如果只是追求这些,自我价值能兼顾吗?不可能的,对吧。”
当然,在“拍给观众”与“自我表达”之间,眼下的许宏宇还在寻找。而放之电影业诸多同阶段的导演,这种寻找,并非异类,而是常态。
异类
许宏宇总在拍异类,而他对自我的认知也是如此。
许宏宇近期最喜欢的电影,是获得去年奥斯卡最佳影片的《健听女孩》。第一次看的时候,许宏宇就看哭了。前段时间,他又把这部电影找出来看了一遍。
打动他的,是“不一样的人群”。“社会上存在这样的群体,他们只是因为缺乏了某一种能力,或是跟别人不一样,就被划为‘异类’。”
许宏宇很小的时候,声音比较细,说话也轻,班上的男同学会取笑他,“像个女孩儿”。
那时候的他很孤独,念了十几年男校,如今脑海中记忆清晰的一个画面,是“在一个天桥上,几个男生搭着肩在前面走,把我一个人落在后面。”
“也许他也不是真的想伤害你,可能是他的父亲告诉过他,男孩儿应该是什么样的,他就自然地那么认为了,”许宏宇回忆,“但那种感觉是很糟糕的,反正当时一说我就哭。”
小孩子的世界充满了由大人所设立好的规则,比如好学生应该是什么样的,男生又应该是什么样。而现在的许宏宇,已经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规则。
“慢慢长大以后,我觉得最近可能确实在某些事情上更感性一点,能拥抱这种力量,把这种能量释放出来,我是很自豪的。”许宏宇穿一件粉色的T恤,左耳挂着一只圆形的金色耳环,松弛地靠在椅背上。
这段年幼时的记忆,或许构成了某种潜意识,它也影响了许宏宇对于故事的偏好。
刚看完《一人之下》时,最打动他的就是“异类”。剧集开播后,鹿晗转发了许宏宇的微博,许宏宇回复道,“你知道吗?肖枫是我拍的第一个异人。”
即便是在《喜欢你》这样的爱情故事里,也能看到影子。影片结尾,路晋追到菜市场,跟顾胜男表白的那场戏,是许宏宇最喜欢的一个片段。“这个世界是属于顾胜男的,路晋因为爱她,主动走进了他的世界。”
这种闯入另一个人生活的勇气,对于自我认知为异类、习惯孤独的人而言,是“超现实”的。
但这种孤独也是相对的。路晋认为“吃饭是一件私密的事情”,是因为他没有找到一起吃饭的人。同样的,不耻于坦白孤独的许宏宇也很难说清,自己究竟是喜欢孤独,还是只是“恰好孤独”。
以前的好朋友大都已经结婚、成为父亲,人生遵循着社会时钟精准地迈入下一个阶段,每次回到香港,他都无法避免地要开始思考这件事。“其实我也挺羡慕他们的,但我已经选择了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
好在,一个创作者享受独处,似乎是种正确。
难得清静,许宏宇独处的方式,有时和自己在一起,有时则把自己放之大自然。出海、潜水、爬山、徒步……让自己的脑子清空,再存新的东西进去。
疫情结束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找到一片大海,然后一头扎进去。
在深海里潜水,好像失去了地心引力,进入太空,踏入月球。海底是完全不同的世界,“我们人类都在辛辛苦苦的工作,但是海洋生物们都是很安稳地在过自己的日子。”
观察海洋生物,是许宏宇的乐趣之一。海龟的家一般在悬崖边上的山洞里,很多叫不上名字的小鱼环绕在身边,有一次他潜到了水流很急的地方,有几百多条鲨鱼从他面前经过。而这种时刻对他而言都是宝贵的。
许宏宇用河豚标记社交平台上的自己。在生气或是兴奋的时候,河豚会鼓成一只炸刺的球,释放毒性。在深海里,大部分鱼成群结队,但河豚是独自行动的。“这么说起来,它也是海里的异类。”

几年前,他在一支个人宣传片里将自己形容为大男孩,说“我不会长大”,但命运的齿轮一直在转,时间似乎也没有给他选择,尽管这选择背后还面临着更多选择,一个维度外也还有另一个维度。
和许宏宇聊了几个小时后,他自言自语地提问道:
“就好像一滴水投到海里,你还是那滴水吗?还是你就成为了这片海呢?”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