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日前,新书《我,厌男》的豆瓣页面引来了诸多一星打分,打分者们对此书的控诉包括“无中生有,虚空打靶”、“挑起激化社会两性矛盾”等。一些男性读者认为,“厌男”一说是对男性的歧视。
许多男性不认为自己应成为被揶揄或批判的对象,为此感到委屈或者戒备,杨笠在脱口秀节目中“男人普通且自信”的表述就曾激怒过不少男性。在女性遭遇性骚扰的社会新闻评论区中,我们也常常能看到这类表态,认为自己从没骚扰过女性却也“中枪”十分不公。《我,厌男》的一则短评也体现了某种典型心态:“普通男性在这个社会也是很遭歧视或者无视的,(厌男)可以说是底层相轻。”身为男性,非但没感受到有过什么特权,甚至没有过压迫女性的意图和行为,为什么还要被说成有关联甚至有责任呢?

[法]波利娜·阿尔芒热 著 一千度 译
新星出版社 2023年
来自男性的控诉该如何理解?假设一位男性从来都没有对女性进行过性骚扰,在日常生活中还展现出了“绅士”特质,比如为女士拎包、开门,并在家中承担一些家务,他是否就是无可指摘的完美男性呢?
我从没感受到特权
只有男性,最懂男性在女性主义运动中产生的困惑。作为一位中产阶级白人异性恋男性,《性别打结》的作者Allan G. Johnson表示,男性都希望幸免于被指控性别歧视,如果他们说自己从来没有骚扰过别人,或者说自己对女性很和善,或者说从来没有因为身为男性能获得过好处,就仿佛可以免于被批评,拥有相对安全感。
一个问题是,男性身份真的没有带来任何好处吗?批评男性特权是“无中生有”吗?Johnson对自己作为男性拥有的特权进行了反思:“特权不是一种可以取得或有选择不去取得的东西。特权是社会体系赋予的,所以人们不必真的感受到自己拥有特权才真正变成特权阶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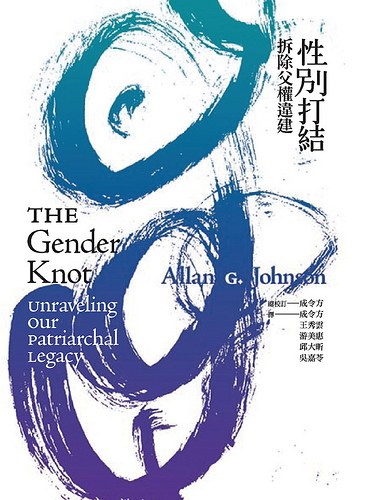
亞倫·強森 著 成令方 等译
群學出版社 2008
Johnson举例称,自己在公开演讲的时候自我感觉很好,如果有人问他为什么那么顺利,他可能会提到自己的能力、经验、论点、公众的兴趣等等,但可能不会意识到,是男性性别让自己如此顺利。研究表明,女性的言说可能不会得到严肃的对待,也更难得到正面的评价。在男女谈话时,男人打断女人的话比女人打断男人的话更频繁,男人会忽略女人提的意见而偏向自己的意见,或者用其他方式控制对话。
在八分钟短剧《女主角》中,汤姆·希德雷斯顿(男)去面试女主角,面试官说:“就是你了!”如果这时有人问汤姆,你为何获得了这个工作机会?他可能会说,因为足够优秀,因为履历丰富,因为适合这个角色……但实际上,汤姆并不知道,在他面试之前,已经有8位女性竞争过这个岗位了,她们被要求必须漂亮、必须微笑,要“性感苗条,有胸有屁股的淫荡处女”、“是女主角,不是女主角的妈妈”、“肤色更白一点”……不管男性想不想要拥有特权,特权就在那里。
“父权制的最大力量之一就是让男人忽视它,就像白人认为种族主义不存在,因为他们看不见,”康奈尔大学英语文学副教授、作家马科马·瓦·古吉 (Mukoma Wa Ngugi) 这样说。他看到,作为一个性别为男的女性主义者,自己依然从性别中获益——他和自己的妹妹在不同时间见了同一个人,他的拜访很顺利,妹妹却遭到了骚扰。这让他意识到,自己和妹妹对这个世界的体验截然不同。

“普通男性在这个社会也是很遭歧视或者无视的”这类说法来自一种观念,是个别男人——而不是所有男人——享有优势和特权。而女人总能感受到无处不在的男性特权,即便是那些被无视的普通男性,在面对同一阶层的女性时,他们依然拥有特权。在这个层面上,每个女人都会有讨厌或甚至憎恨“男人”的时刻,便更容易理解。
并非所有男人都这样
如果一个男性从来没有性骚扰女性,“厌男”话语何以把他也囊括进去?《哈佛商业周刊》刊发过一项研究,在试图探讨性别议题时,男性往往会展现出防御性,称“并不是所有男人都这样”。参与研究的男性被要求阅读历史上的不公正现象,例如20世纪初女性不被允许拥有财产或投票权,然后被询问一些问题。面对过去的不平等,男性的反应是防御性的,他们常常否认当今的性别歧视,并对性别平等的倡议表现出较低的支持。
其实,个人的动机和行为并不是问题的重点。Johnson意识到:“作为一个男人,无论我是否真的强暴了任何人,我都和其他男人所从事的暴力模式有所关联。”这是因为,“我所处的社会基本上鼓励对女性的性支配、物化以及剥削,而这些都会将性暴力的行为模式‘正当化’并给予支持;至于我个人是否鼓励或支持这种行为,根本就不是重点。”因此,一个男性没有强暴女人,并不代表他不参与这个鼓励男性特权和性别暴力的父权社会。
其实,就像白人不需要刻意作恶就可以助长种族歧视,男人也不需要刻意作出讨厌的行为,就可以成为厌女社会的一员,因为他们只要跟随主流、平常行事就可以。马科马·瓦·古吉谈到,他在酒吧和几乎不认识的男同事喝酒时,建立关系的最快方式就是谈论女同事、女顾客、女调酒师,或者一个随机走过的女人。
在旺加里·马塔伊(Wangari Wa Maathai)获得和平诺贝尔和平奖时,古吉和男性朋友在酒吧里聊天,他们讨论起了她的外表。事后他反思:这个被独裁政权折磨的女人,在为民主斗争的过程中牺牲了这么多,然而男子气概却需要“让她下降一个档次”。这种通过外表来看待女性成就的做法,是对女性的非人化,以牺牲女性为代价来连结男性纽带。他承认,“我一直是这种非人化对话的快乐一方,但这是我们必须超越和面对的事情。”
因为父权就是现状,我们很容易将其视为正常且没问题的。Allan G. Johnson看到,“父权制提供了阻力最小的路,以无声无息的方式,鼓励男人接受自己的性别优势以及持续对女人的压迫。”

我已经做得很好了
在日常生活中,我为女士拎包开门,非常绅士,为何还是会遭遇“厌男”?当然,怨恨一个压迫系统中的强势群体,和怨恨属于强势群体中的个人存在着差异。男性与性别歧视的社会之间的关系有很多种,也有男性会加入女性的行列共同对抗父权制。然而,拎包、开门这些“绅士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是值得称赞的、对抗父权制的行为?
父权制意味着社会由男性支配、认同男性,以男性为中心,在父权制社会中,高权威的位置一般由男性占据。男性获得较多的收入和财富,社会文化更多由男性形塑,服务于他们的集体利益,并对女性造成压迫。拎包、开门等行为虽然绅士,但是完全不构成对整体社会结构的改变。
也有一些男性认为自己承担了家务,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在《她们不是唠叨,只是受够了:不被看见的情绪劳动》一书中,作者杰玛·哈特莉的丈夫罗伯带着三个孩子出门,总是能够收获许多赞美。陌生人对他的勇气充满钦佩,许多人对他说“你真是个杰出的好爸爸”。一位老人以为他主动把那天当成“奶爸日”,以给孩子妈妈一些喘息的空间,为此一直称赞他。他遇到的几乎每个人都觉得,男人光是带着所有孩子出门就是一件非比寻常的成就。

[美]杰玛·哈特莉 著 洪慧芳 译
新星出版社 2023
承担了一些家务就会被看作是好男人。杰玛·哈特莉发现,不论单亲妈妈做得有多好,大家都似乎觉得她们付出得不够多,而单亲爸爸完全不受同样的标准约束。单亲爸爸帮女儿梳头、穿衣打扮,就变成了感人的故事;单亲爸爸说自己难以支付孩子的医药费,陌生人的善意回应立刻蜂拥而至。“母亲做同样的事情时,永远得不到同样的赞赏。即使那些单亲爸爸只想获得平等的看待,但社会为他们设立的门槛标准之低,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杰玛·哈特莉认为,一直以来,男人觉得任何家务事都不算自己的工作,而是伴侣的工作,他们只是帮忙而已。“即使是最优秀、最有自我意识的男人也难以免俗,因为这种观念在我们的文化中是如此普遍。”杰玛·哈特莉看到,虽然现在男性在家中承担的工作在逐代显著增加,但是男性做的家务仍然比伴侣更少,尽管如此,他们会觉得自己已经是很特别的伴侣了,因为他们在潜意识中认为那不是自己的分内工作。归根结底,日常的家务和情绪劳动被认为是女性的工作,不是真正有价值的工作,有偿劳动是男人的工作。这才是问题的根本。
《性别打结》一书提醒读者警惕男性认为自己没有过错甚至做得不错的想法,因为“这样他们也不会去探索父权制到底如何运作、为什么要改变和如何改变的问题了”。对于“厌男”话语引发的男性反攻,无论何种性别都应认识到,男人的过度敏感症是统治集团的典型特质。如果性别语境难以理解,置换到种族的层面,这个问题或许更加显而易见——当黑人说白人是白鬼(honkies),或表达愤怒抗议白人抗拒处理日常生活中的种族歧视的时候,白人也往往会有强烈的反应。但是白人没有注意到的是,种族的敌视是普遍存在于弱者生活中的。当女性谈论“厌男”时,也是如此。
参考资料:
https://qz.com/work/1415198/the-non-confrontational-question-that-helps-men-become-feminists/
《她们不是唠叨,只是受够了:不被看见的情绪劳动》
[美]杰玛·哈特莉 著 洪慧芳 译 新星出版社 2023
《性别打结》亞倫·強森(Allan G. Johnson) 著 成令方、王秀雲、游美惠、邱大昕、吳嘉苓 译 群學出版社 2008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