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瑞典文学院将2023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挪威作家约恩·福瑟(Jon Fosse),颁奖词称“他富有创新精神的戏剧和散文赋予了不可言说之物以声音”。
中文世界的读者或许对这位挪威国民度超高的作家并不十分了解,目前市面上能找到的福瑟中文译本只有两本剧作选集,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在2014和2016年译介出版的《有人将至》和《秋之梦》。由于久无加印和再版,诺奖公布之后,一些平台的二手书价格已骤升至上千元。值得期待的是,世纪文景和译林出版社之后将推出福瑟其他作品的中文版,包括小说《三部曲》《晨与夜》和他近年来最重要的长篇代表作“七部曲”(《别的名字:七部曲I-II》《我是另一个:七部曲III-V》《新的名字:七部曲VI-VII》)。
在诺奖公布后,界面文化采访了北欧文学专家石琴娥、《三部曲》中文译者李澍波,以及曾将福瑟剧作《一个夏日》搬上过中国舞台的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艺术总监喻荣军。在你读到福瑟作品的中文版之前,或许可以听听他们如何评说自己曾经见到的福瑟、正在翻译的作品,以及对福瑟作品的语言、风格的思考和讨论。
石琴娥:被称为当代易卜生是因福瑟国民度超高
(石琴娥,1936年出生于上海。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北欧文学专家。曾长期在中国驻瑞典和冰岛使馆工作,为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哥本哈根大学和奥斯陆大学访问学者和访问教授。代表作有《北欧文学史》。)

北欧文学专家石琴娥告诉界面文化,她早就觉得约恩·福瑟会得诺奖,并不感到意外,因为诺奖已经很多年没有颁给北欧作家了,福瑟这几年呼声很高。
石琴娥曾在2003年前后去挪威国家剧院看过福瑟的戏剧,也见过福瑟本人:“我到挪威后,无论是奥斯陆大学的文学系教授、作家还是文艺爱好者,都建议我去了解他的作品。他的国民度非常高,就像我们要谈中国现代文学,很多人会谈到王蒙、陈忠实一样。而且,因为福瑟的作品在世界各地演出,挪威国民也觉得他为国争光。他被称为当代的易卜生,并不是说风格相似,而是由于大家对他的了解比较多,国民度像是易卜生。”
石琴娥回忆说,当时去见福瑟,是因为有朋友让她翻译他的戏剧作品《有人找上门来》(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版本为《有人将至》),当时她在奥斯陆,福瑟在西部城市卑尔根,二人见面比较匆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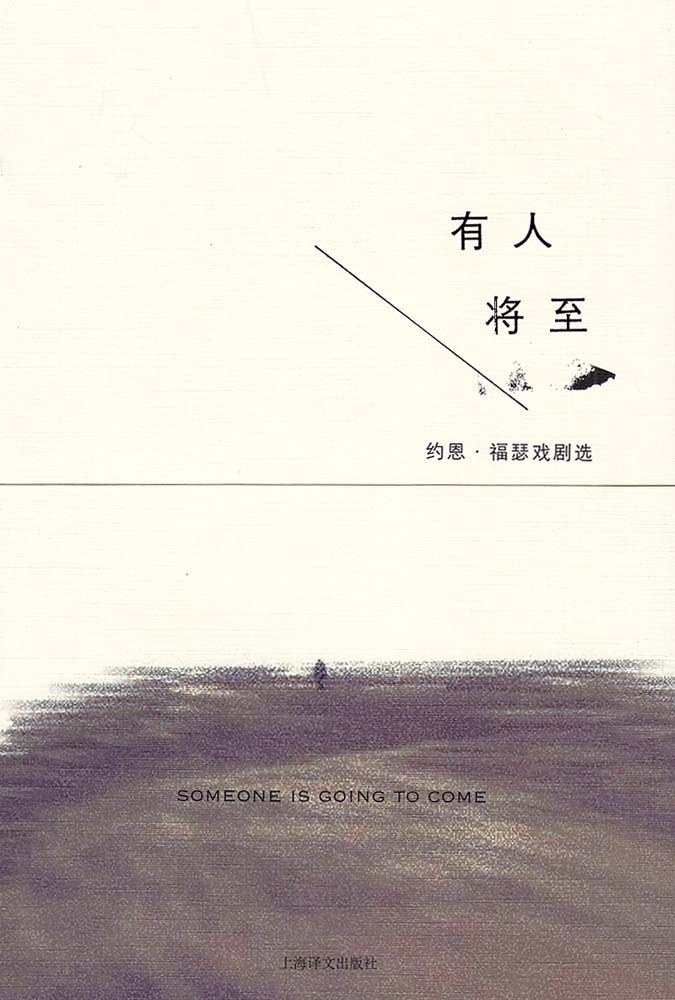
她认为福瑟是一个很全面的作家,既写长篇也写短篇,也有儿童文学,但主要的成就是戏剧。石琴娥评价说,他的作品打破了范式,人物就叫“男人”“女人”而没有名字,探讨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故事)放在任何时间地点都是可以的。此外,他的文字非常有音乐性和诗意,简练而紧凑,还会有很多语句的重复。“整体来说,作品介于现实和荒诞之间,有一种非常新鲜的感觉。”
福瑟一直用新挪威语写作。关于挪威语和新挪威语的发展脉络,石琴娥曾在著作《北欧文学史》里做过分析。她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解释道,因为挪威受到过丹麦和瑞典的统治,所以挪威语是丹麦语和挪威语的融合,而新挪威语是老百姓使用的语言,保留了民族特点,之前不被国家承认为正式语言。“新”并不是时间上的新,实际上,新挪威语更加传统,在奥斯陆还有一家专门出版新挪威语作品的出版社。福瑟从小在挪威西部长大,一直使用的就是这种语言,“就像中国国内也有作家用上海话写作一样。”

“挪威文学是跟它的独立运动、民族解放共同成长的,鲁迅《域外小说集》里就有挪威、芬兰的作品,也是把它们作为被压迫被侵略的民族文学来看待的。”石琴娥进一步阐释道,“芬兰语也有两种语言,一种是瑞典语,一种是芬兰语,因为芬兰之前是瑞典的殖民地,所以本地语言就不受重视,国家独立后芬兰语才逐渐受到重视。”
福瑟作为新一代作家,石琴娥分析称,“不能说他的写作有抵抗文化侵略的意思,但福瑟的作品非常能够反映当代挪威人的想法。”比如在剧本《有人将至》中,人物生活在一个偏僻的房子里,男主角觉得这样的生活很美好,而女主角总担心有人要来,果然房子的主人最后来了,这反映了挪威人的一种心理——想过这样与世无争的生活,但是做不到。“北欧人的性格就是如此,很内向,外国人也很难融入进去;但他们也是一个待人很真诚的民族,尤其是挪威人,他们叫你去家里做客,那就是认真的。”
李澍波:福瑟与克瑙斯高是师生关系
(李澍波,作者,译者,学者。英国威敏斯特大学媒体传播研究所传播学博士。曾在经济日报、南方都市报、奥斯陆大学、挪威米凯尔森研究所⼯作。写作聚焦文化、艺术和社会史,为《纽约时报中文版》《三联生活周刊》《中国新闻周刊》《新周刊》《旅行家》等报刊撰稿。现定居挪威奥斯陆。)
李澍波目前正在将福瑟的小说《三部曲》翻译成中文,译稿完成了30%。听到福瑟获诺奖的消息后,她说,“我想我应该加班了。”

挪威媒体认为福瑟等诺奖已经等了22年——早在2001年就有出版社说福瑟有可能问鼎诺奖,彼时大部分获奖作家都在70岁以上,相比之下福瑟还太年轻。李澍波提到,最近22年来有一些低于70岁的作家获奖,所以,“也该轮到他了。相对来说,或许其他人被纳入候选人的考量时间并没有那么长。福瑟今年获诺奖是因为他没有更强的竞争对手。”
以前李澍波读的挪威文学多数是以挪威语(Bokmål)写作的,而福瑟选择使用新挪威语(Nynorsk),七十多部戏剧基本都用新挪威语写成。在翻译一些新挪威语(Nynorsk)作家作品的时候,她开始慢慢熟悉福瑟等西部作家。在她看来,新挪威语更多是基于西挪威的口语,有很多词汇和表达方式更为本土和民族化,有着挪威语难以表达的东西。
大多数中国读者或许并不了解这位挪威作家,而对于挪威这个国家来说,福瑟是一位地位颇高的创作者,“得到政府和社会几乎全方位的认可。”李澍波说,“不管是写过去的西挪威人,还是写卑尔根(挪威西海岸最大港都)的大学生,福瑟的作品展现了西挪威的现实。他的写作把新挪威语带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上。在挪威,福瑟是在易卜生之后戏剧被搬上舞台次数最多的剧作家。他同时还是诗人和作家,特别高产,在戏剧作品之外,每年都有新作品问世。”
从2001年开始,福瑟开始受到挪威国家奖学金(2021年税前46.1万挪威克朗)资助,李澍波指出,“这意味着国家发工资,他只管创作。挪威政府还在奥斯陆为他提供了一座住宅,因此他不需要考虑生计,也不需要考虑市场。他曾经长时间酗酒,用酒精帮助自己产生灵感,但是后来遭遇休克就戒酒了。现在他戒酒也有一段时间了。福瑟不太在意和外界的交流,但是他作品的地位早就非常巩固了。”

在挪威,也存在着一些语言导致的刻板印象。人们认为东挪威的人比较油滑、现代,西挪威的人更为淳朴,但是李澍波提到,实际上西挪威也有很多成功商人,卑尔根是汉萨同盟(12-17世纪之间欧洲北部各个城市形成的商业政治联盟)成员,至今也是重要的欧洲商贸口岸。整体来说,东挪威更世俗一些,西挪威的地方性和宗教色彩更强,作家、艺术家有比较强烈的本土情结。挪威政府非常扶持用新挪威语出版的书籍和剧作,还有专门上演新挪威语戏剧的剧场。“挪威将之作为本土文化的支柱来扶持,福瑟在这方面是领军人物。”
李澍波正在翻译的小说《三部曲》篇幅不是很长,她在采访中介绍道,《三部曲》写的是19世纪西挪威峡湾的一对年轻人,女主角在地主家做女佣,男主角是小提琴手,他们来到了大城市。第一部曲讲的是怀孕的女主角即将生产,想要找一个可以住的地方,但在当时的卑尔根,人们认为他们不是正经人,他们在雨里走了一天,到处被拒绝,在反复的行动中展开自己的记忆和体验。在平淡的过程中,忽然就发生了直接挑战人性的事件,男主角杀了好几个人,但读者并不觉得突兀。李澍波说,“福瑟的语言看起来很简单,但是非常现代主义。他的小说写作非常像实验戏剧,会把一句话翻来覆去地说,但每次说展示的情感和内容都不一样。”
在翻译过程中,她愈发感受到《三部曲》与挪威另外一位诺奖作家克努特·汉姆生(Knut Hamsun)的《饥饿》之间的血脉延续。《饥饿》背景在奥斯陆,一个饥饿的“边缘人”在外面转悠了一整天,想要弄点吃的。“《饥饿》讲述的是文艺青年的饥饿,《三部曲》讲述的是底层人的‘饥饿’,主人公是没有固定收入的人,连工人阶级、农民都算不上,因为挪威农民也是挺有钱的,得有块地才能当农民。两部作品的主人公都处于社会的边缘。”
李澍波此前曾翻译过卡尔·奥韦·克瑙斯高《我的奋斗5》和《我的奋斗6》,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李澍波也谈到了克瑙斯高与福瑟的关联——二人是师生关系,克瑙斯高在卑尔根就读的写作学校,就是福瑟等人开办的;克瑙斯高是南挪威人,用挪威语写作,对福瑟的评价很高。
喻荣军:福瑟写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可沟通
(喻荣军,作家,国家一级编剧。上海市戏剧家协会第八届理事会副主席,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艺术总监。)
福瑟在欧洲享有“新易卜生”、“新品特”或“新贝克特”的名号,他的剧作曾被搬上中国的话剧舞台。2010年,福瑟最早也最知名的作品之一《有人将至》在北京首演;2013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排演了《名字》,并于2014年上海当代戏剧节推出约恩·福瑟戏剧展,邀请外国剧团赴华演出《一个夏日》《有人将至》《死亡变奏曲》等五部作品。
2019年,上话导演王魏创排了《一个夏日》,这个剧名来自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我可否将你比作一个夏日》。该剧讲述了一对住在北方寂静萧瑟海边的普通夫妻的故事:一个平凡的秋日,女人意识到她的丈夫阿瑟不会再回来;多年后的一个夏日,垂垂老矣的女人依然住在海边的那幢房子里,望着窗外的大海,丈夫离去的原因似乎成为了一个永远的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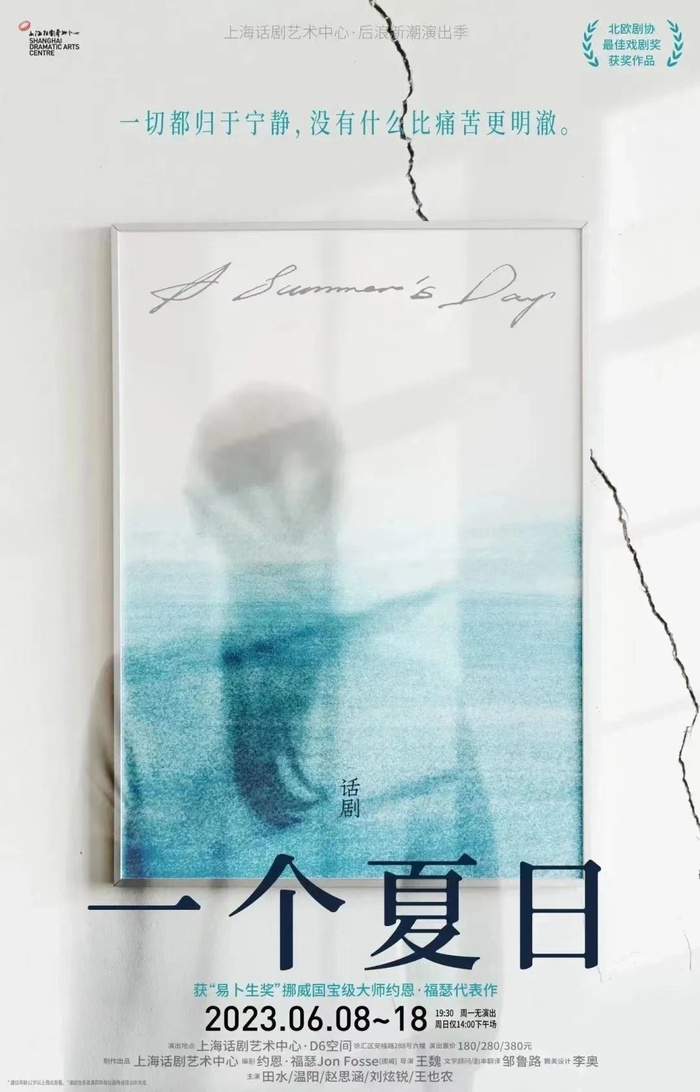
2017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艺术总监喻荣军在斯洛伐克戏剧节见过福瑟,与他相谈甚欢。在他的印象中,福瑟是个“非常谦和”甚至有些“社恐”的人。他曾邀请福瑟来中国,但因疫情阻隔未能如愿。得知福瑟获得诺奖的消息,他表示很为对方感到开心,“我们已经关注他很多年了,觉得应该把他介绍给我们的观众,因为他是非常独特的一位剧作家。他会得奖,在我们的预料之中,也在我们的意料之外。”
十多年前,福瑟的经纪人向喻荣军介绍称,这是挪威继易卜生之后又一位戏剧大家,喻荣军看了《有人将至》等作品后被深深打动。在他看来,福瑟的作品既符合中国人对北欧的感受——“阴冷潮湿的冬天,海岸边,人与人之间那种不是那么热乎的关系,如果把这个定性为北欧的话,那他的戏肯定具有北欧的这种特点”——又具有一种普适性的当代性,“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不可沟通、疏离和冷静的状态,他写得非常入骨,有时候甚至是比较残酷的。我觉得他的作品都有一点品特的风格,对当代人的生活状态又写得特别冷静客观。他会让我们的观众从一个比较客观的视野去打量社会,这个角度非常独特。”
今年夏天,《一个夏日》再次在上话演出。喻荣军表示,在上话的版本中,主创团队的创作主旨是尽量让观众能够感受到福瑟在他的戏剧世界中创造的散文式的、客观的、小清新的氛围感。导演王魏注意到,过去四年使得观众对“孤独”、“隔阂”、“疏离”有了更直接更切肤的感受。有2019年的观众时隔两年留下评论:“今天突然想起这部话剧,想起那个男人在峡湾里孤独的样子,我想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孤独,我也想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孤独。”

喻荣军也提到,向中国观众介绍福瑟的作品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他的作品戏剧性比较弱,娱乐性不是很强,“不是大众的戏,是比较小众的戏”。但从观众对《一个夏日》的反馈来看,他发现观众越来越能够领会福瑟的创作旨趣,“它所反映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福瑟)创造的一个属于他的世界,让现在的观众也很有感触。尤其是经过了疫情三年,大家对这方面的感受可能更深。”
作为国内唯一一家长期关注福瑟作品的剧院,上话将继续探讨创排福瑟作品的可能性,比如《秋之梦》。喻荣军表示,“在未来有可能的话我们还会有更多的推介,让更多的观众了解这一位剧作家,他的作品能反映当代社会的特点。虽然现在还没有具体计划,但我还是希望我们接下来能排演更多他的作品,因为他拿了奖,可能更多的观众会关注他。”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