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界面新闻编辑 | 徐鲁青 黄月
一直以来,海派文化都以万花筒的形象呈现在大众视野里,在经济政治的巨大变革中,折射出社会生活变迁的五光十色。内涵丰富的海派文化正是随着上海作为摩登都市的发展而形成的。
自1843年开埠以后,上海成为了一个五方杂处的文化熔炉,画报、报纸、杂志等大众媒介纷纷出现,为上海市民提供了解各方面新闻消息的渠道,也通过图像构建了一座摩登都市的想象。
在新书《摩登图释》中,复旦大学特聘讲座教授陈建华通过分析上海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的画报,试图呈现出上海近代都市生活的不同面向。从月份牌到电影海报,从画报到杂志封面,摩登都市在媒介中的呈现往往和女性身体联系在一起。丰腴的,时尚的,情欲的,健康的……女性的身体成为现代性在大众媒介中的独特表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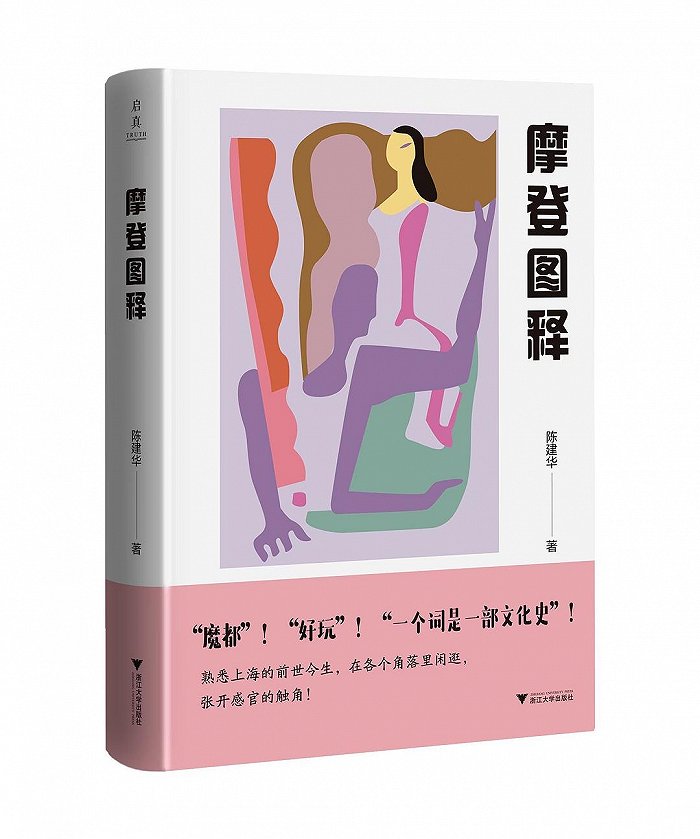
陈建华
启真馆·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3-10
妓女:规训与反叛
“摩登”在中国语境中本来指代佛经中的摩登伽女,意为古印度摩登伽的淫女。近代,“modern”经由日本传入中国,却意外地因为发音相似成为了“摩登”的新含义。同为“modern”的汉语释义,“摩登”的使用率远远比不上“现代”,却距离大众和都市本身更近。

或许受到本意的影响,近代“摩登女”的内涵比“新女性”更为激进和具体。陈建华认为“摩登女”更具有“外国趣味”、“暴露主义”和“性的解放主义”等特征,在外观上袒胸凸臀,更为西化,身体更为自然健美,身着美艳装扮,在男女交往上更为开放自由,更具自主性。
妓女在传统社会中被视为引诱正人君子离经叛道的危险因素,不被主流文化认可,但却又无时无刻不受主流文化的规训。在近代,她们仍然面临这种困境,但大众媒介已经揭示出了她们身上的某种反叛精神。《今代妇女》杂志里有两幅女性“交腿”图,文字解说“交腿坐法不宜于大庭广众之中”,作为男性欲望的投射对象,“交腿”是不雅的。但在女性立场上重新审视,这恰恰是女性自适自信的主体性的一种彰显。

陈建华指出,交腿姿势对于妓女来说不足为奇。“富春楼”是近代上海有名的“花国大王”,常常登上新闻。《紫罗兰》杂志中,“富春楼”不仅交腿,还一手托腮,一手搭在椅子的扶手上。传统观念无法容纳这种随意,因此将她视为社会另类而不屑一顾。
但这种蔑视何尝不是双向的呢?《太平洋画报》上的"富春楼"甚至直接斜身靠在贵妃榻上,远比直立更具观赏性,神态和手势也更为舒展。陈建华认为,妓女利用资本与技术作了一场又一场“可观性”呈现,拓展了社会空间的中间地带。在作为被凝视的客体的同时,她们主动成为反抗凝视的主体。

传统文明和前卫思潮的强烈碰撞不仅出现在闺房之中,更表现在公共空间之内。妓女乘马车炫耀奇装异服,在大马路上招摇过市,这种景象被大众媒介捕捉并广而告之。美国波士顿大学现代语言与比较文学系教授叶凯蒂在《上海·爱:名妓、知识分子与娱乐文化(1850-1910)》一书中将其称为“上海公众面前最绚丽的风景”或“新的都会性格”,而这正是以女性在公共领域的自由行动为前提的。这类图像让我们对于“妇女解放”的渊源追溯更进一步,历史叙事也因此有了更广阔的阐释空间。
杨贵妃:西方审美的东方美人
杨贵妃是传统文化中的四大美女之一,似乎与“新文化”、“摩登”背道而驰,但却在孔学被口诛笔伐的时候受到了格外的青睐。明代士大夫的杨妃出浴图本用于私下观赏,在近代,它们经由媒介大量复制而流传于消费市场。郑曼陀、王美沅、刘既漂和王仲年等民国画家也以“杨妃出浴”为主题进行了大量创作。《长恨歌》的诗句被《申报》等报刊化用,故事情节被用来创作连环画。鲁迅在1921年甚至有创作《杨贵妃》剧本的计划。这都与“摩登女”的媒介呈现有着密切关系。
杨玉环身材矮胖,双脚也不够小巧,在明清的审美标准中称不上美女。而唐代因胡人变革的风尚,和近代传入中国的西方审美竟殊途同归。陈建华在书中写道:“在1914年的《眉语》杂志里有一幅题为‘西方杨妃’的出浴图,似乎只有杨贵妃才具备中西交融的条件,而西施或其他美女就没有这种可能。”大众对于“摩登女”已形成独特的集体想象,杨玉环脱离传统审美标准的身体异质,经由媒介呈现给大众。

对于几千年来一直受到礼教约束的中国人来说,接受“裸体”观念和其公开呈现都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大量此类图像频繁出现,大众也逐渐接触了“裸体”背后的西方价值观念:文艺作品所代表的人的重要价值和人类文明的成就。裸体不再等于卑俗的欲望,而与高尚纯洁的意涵有关。
尽管如此,从“贵妃出浴”到“海水浴”、“裸体”,这些词语受到男性窥视欲望的推动,借助图像的力量,诉诸视觉感官,刺激大众的消费欲望,推动了许多纸媒与视觉制作的产业链。
身处情欲和消费漩涡中心的女性身体,逐渐成为日常文化消费的主流,进而作为“摩登”的标记被大众熟知。当然,它们的文化价值也不可忽略。“时尚”、“时装”、“摩登”等词语作为日常惯用语而推进西化的同时,还不断向大众输入女体体育健美、艺术审美等观念,开启了都市日常启蒙的现代性之旅,也符合女性走向解放的要求。这不仅是时尚的变迁,对于城市或民族来说也是一种现代化进步的象征性标志。
丝厂女工:摩登都市中的边缘群体
无论是穿着时装的妓女,还是暴露身体的杨玉环,她们都因欲望的投射而受到特别的关注。“丝厂女工”并未含有多少情欲色彩,但仍然被大众媒介包罗其中,因而也成为陈建华重构上海文化历史叙事的“边缘元素”。
陈建华在书中说:“在一个多世纪之前的画报里所反映的主要是繁华的十里洋场,灯红酒绿,光怪陆离,无奇不有,更多聚焦于当红妓女、名门闺秀或西方美人,却也使我们看到大墙底下的缫丝女工——被压榨被侮辱的一群人,看到她们的痛苦、无奈、觉悟与抗争。”
上海最早成为通商口岸,外国资本主义最先在这片土地扎根,因而上海也最早地出现了工人群体。传统农村经济的松动瓦解给了许多年轻女性进入摩登都市做工的机会。丝厂女工就这样融入了社会变革的巨大洪流之中。
1884年《点石斋画报》的《乃见狂且》图中题词记录,一群女工放工后被无赖们评头论足、调戏羞辱。题词本应谴责流氓对缫丝女工的欺凌,但因为画面左边是日本茶楼“荟艳楼”,租界上有很多日妓,于是题词转而感叹:“遂使礼教之邦,等诸化外乎。”意思是中国向来是礼仪之邦,自从租界出现,就变成“化外”——野蛮之地了。

题词的转向反映出一种反殖民的民族主义倾向——租界不应该存在,但原本社会结构中就存在的性别不平等也被掩盖在了民族主义的宏大叙事之下。在民族矛盾的尖锐时刻,这种忽视可以理解;但今天再次回望,或许应该看到内部矛盾是与民族矛盾共存并相互纠缠勾连的。

这些丝厂女工“为了糊口而进丝厂,不得已抛头露面”。除了来自陈旧社会观念的束缚,还要遭受流氓骚扰、买办欺压、匪人抢劫、老板欠薪等等。多重权力结构的作用下,她们受到了极度的压迫,却也因此迸发出了巨大的力量。她们“放工后,三三两两,结伴归家”,互相照顾;她们抱团一起教训流氓;她们结成“女党”,“三百余人拥至公共公廊”,追讨薪资……
这些女工在大众媒介中的“可观性”远远比不上妓女和杨玉环,似乎也与“时尚”、“时髦”等词毫无关系,但却构成了摩登都市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景观。她们率先成为职业女性,并独立出现在各类公共场合,甚至拥有先进的革命觉悟,深度参与了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方方面面。

参考资料:
李公明:陈建华的“摩登图释”与……亟待重述的现代史叙事,2023年10月12日。
(文中图片均来自《摩登图释》一书)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