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繁花》成为2024年开年第一部“爆了”的电视剧,并不让人意外,早在2014年(金宇澄小说《繁花》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前一年)王家卫有意向购买《繁花》版权、拍摄“沪语美剧”的消息传出起,这位上海出生的中国香港地区导演将如何拍摄其职业生涯的第一部电视剧就引发了种种猜测。2017年,王家卫开始了《繁花》的影视化工作。2020年8月,电视剧《繁花》官宣启动。2023年12月底,《繁花》正式播出。
自2021年《繁花》首个片花流出,该剧就面临着“是否尊重原著”的争议。胡歌饰演的阿宝衣冠楚楚,举起酒杯邪魅一笑的镜头,很难让人不联想到2013年的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衣香鬓影、觥筹交错的财富景观也使人疑惑,这到底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还是九十年代的上海。
电视剧目前已近尾声,播出之初的“背离原著”非议渐渐平息。许多观众一边吐槽一边被剧情勾着往下追,渐渐咂摸出剧版《繁花》的独有叙事魅力。如果我们抛开原著小说,将剧版《繁花》看作“同人作品”或“番外”,可能反而能看出“原创剧情”中的意味深长之处。《繁花》接续了2023年《平原上的摩西》《漫长的季节》等高口碑影视作品生发出的“九十年代怀旧风”,不同之处在于,《繁花》以上海为背景讲述九十年代,正如剧中漫溢的金色光晕所暗示的,它所呈现的,是这复杂十年的另一个黄金色的面向。
重塑上海城市叙事
作为剧版《繁花》的旁白,阿宝揭示了男主角和改革开放亲历者的双重身份:邓小平南巡讲话加快了中国股份制改革的步伐,以100点为起点,上证指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逼近1000点。阿宝抓住机会,在股市中获得了第一桶金,成为和平饭店的常客“宝总”。阿宝离开“1993上海和平之夜”派对,在和平饭店门口被一辆出租车撞倒,拉开了故事的序幕。

和平饭店在原著小说中无甚存在感,却是剧版《繁花》中反复出现的地点,某种程度上来说,剧集主创是了解和平饭店在当时上海人心目中的地位的。恰是在1992年,建于1929年的和平饭店获得中国首家世界最著名饭店称号,再次成为上海年轻人趋之若鹜的时髦去处。作家陈丹燕在《上海的风花雪月》中这样写:“也是只有上海孩子才能有的心情:对欧化的、富裕的生活深深的迷醉。”除了和平饭店,《繁花》镜头还屡屡掠过波光粼粼的黄浦江、外滩巍峨富丽的西式办公大楼和百货公司林立的南京路。

这些地点长久以来被视作上海的象征。历史学家连玲玲指出,从1843年开埠到租界废除的一百年间,外滩原本是上海航运的起始点,沿路以码头栈房、仓库、洋行等功能建筑为主,后来成为银行、保险公司、高级旅馆和办公大楼的所在地;南京路原本只是连接外滩和跑马场的通道,后来吸引了诸多商店和娱乐场所进驻,其中最著名的是先施、永安、大新、新新“四大百货公司”,演变成“上海第一商业街”。在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卢汉超看来,“上海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巍峨的商业性建筑作为其主要标志的大城市。”早在1930年代,上海就已经是世界第五大城市、中国最大的港口和通商口岸,有着“东方巴黎”的美称。
在摄影集《上海1842-2010,一座伟大城市的肖像》中,编著者刘香成和凯伦·史密斯(Karen Smith)指出,虽然上海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被淹没在共和国的整体性格中,但在最近几十年的时间里,这座城市在1949年以前的许多形象特征又重新浮现,比如享乐主义和遍地的机会与财富。学者李欧梵注意到,随着政府在九十年代做出开发浦东、把上海打造成全球化国际大都市的战略决策,“旧上海”的繁华也成为了服务于这一目标的一种文化资源。1996年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出版,在文坛掀起怀旧风,程乃珊、陈丹燕、孙树芬、陈子善等人都出版过讲述“旧上海”故事的作品。

[美]刘香成 [英]凯伦·史密斯 主编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0-05
对“旧上海”的追忆是文艺界的潮流,也是城市转型期的人心所向。卢汉超在九十年代的上海注意到,很多老上海人倾向于把上海正在进行的狂热经济改革和热火朝天的建设看作是传统的恢复,接受他采访的一个上海人甚至感叹,“忘记过去的60年——九十年代与三十年代接轨了。”
如果我们了解到这一点,就会发现剧版《繁花》中游本昌饰演的爷叔角色是多么耐人寻味。爷叔是指导阿宝生意经的老前辈。上门寻访拜师的阿宝获得了他的信任,二人搭档做生意。爷叔对开公司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在和平饭店租下一间长租房。走进千挑万选的房间,爷叔未经介绍就对房间格局了若指掌,阿宝好奇,他淡淡地回了一句,“以前这是我的长包房。”租好房间,爷叔又教阿宝穿衣,请裁缝上门定制西装,第一个要求就是“一定要英纺、纯羊毛的”,“夏天(穿)派立斯、凡立丁,冬天(穿)法兰绒、轧别丁。”当阿宝第一次穿戴整齐,出现在爷叔面前时,爷叔不禁眼中泛泪,仿佛看到了年轻的自己。我们不难想象,他在解放前属于上海的富裕阶层,后来被划为“买办资本家”成为革命打击的对象。这个角色象征着九十年代上海的传统回归——爷叔在商界的运筹帷幄和对奢侈消费的见多识广,不过是重复了他曾熟悉的一切。

一同回归的还有上海独树一帜的城市性格。“在近代上海,城市化、现代化和西化三者盘根错节,”卢汉超在《霓虹灯下》中写道,“作为中国新思想和变革最主要的起源地,上海本身就是现代化的产物。最后,由于它是中国最主要的通商口岸,与西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上海的城市化和现代化又包含了一定程度上的西化。”卢汉超指出,上海是一座在西方商业精神和活力的刺激驱动下发展起来的城市,这种商业精神和活力对中国来说是新奇的;“上海人”的气质精髓,也是由商业造就的——“精明”差不多成为“上海人”的同义词,但它并不仅仅只是意味着“小气”或“市侩”,“相反,它意味着一种风格或出于对生活勇敢果断的想象,用中国的一句成语来形容,就是敢于为长期利益而‘掷金如土’。”
然而,也正是由于上海人在盲目排外和崇洋媚外两者之间采取的世故立场,上海一直有着“西化桥头堡”的刻板标签,与此同时,传统儒家观念将城市商业文化视为一种堕落,“道德沦丧之地”于是成为上海城市形象的暗面。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对城市商业文化的疑虑一直影响着中国作家的城市书写。《繁花》原著令人津津乐道的烟火气实际上有着明显的年代划分:六七十年代固然残酷冷峻,却因作者对时代风物事无巨细的描摹而透出柔光;九十年代的画风则变得声色犬马,光怪陆离。2020年出版的小说《南货店》同样讲述一个江南城镇数十年变迁的故事,作者张忌对时代划分也采取了类似的处理方式,特别是用女性角色来映衬时代差别——在物质匮乏的革命年代,女人是命运的祭品;到了商品经济改革的年代,(进城的)女人是欲望勃发的“蛇蝎美人”。
剧版《繁花》略去了原著小说的多数鸡零狗碎、男女情事,将故事主线聚焦于阿宝的创业与成长,特别以重塑阿宝人设的方式为上海“正名”。在剧中,阿宝呈现出一个有情有义、不忘本的商人形象,他与三个女性角色(李李、汪小姐、玲子)的关系与其说是体现男主风流倜傥,不如说是衬托他的仁义和对弱者的怜惜;他是黄河路各家豪华饭店的座上宾,但最落胃的依然是一碗泡饭。有意思的是,汪小姐(唐嫣 饰)这个角色也改头换面,从原著中一个偷情怀孕又为了生子假结婚的奇情角色转变为剧中“泼辣、天真、耿直的机关单位小姑娘”、中国第一代女性白领的代表。

作为一个城市书写文本,剧版《繁花》强调了“城市是把握经济机遇的象征”,它暗合了改革开放时代我们对现代化和与之齐头并进的城市化寄予的厚望。人类学家王爱华(Aihwa Ong)在《成为全球城市:亚洲实验与全球化的艺术》(Worlding Cities: Asian Experiments and the Art of Being Global)一书中指出,新兴国家的城市已经承载了财富、权力、声望等国家野心,成为国家解决现代生活和国家利益问题的重要干预场所。正如剧版《繁花》旁白/阿宝的意气风发之语所言,社会发展的热望被凝结于上海——这座最有国际化潜力的中国城市——之上:
“1988年的上海,投入黄浦江上的浪头,滔滔向前。改革十年,印证了发展才是硬道理。市场经济改变了每个人的活法,勤奋是这片土地的底色。每个人都在为社会的进步添砖加瓦,成为市场的铺路石。”
上海版本的“向前看,别回头”
剧版《繁花》大量启用上海演员、推出沪语版本令许多观众津津乐道,在语言层面,电视剧力求还原上海的原真性——沪语正是“上海人”最重要的身份标识。卢汉超指出,上海话形成于19-20世纪之交,到民国初期逐渐成型,上海话可能是中国最年轻的方言。民国时期,原先带有松江或浦东口音的上海方言渐渐成了“乡下话”,“城里人”——住在外国租界及周边地区的中心城区的居民——说的是另一种“上海话”。1949年以后,严格的户籍制度让上海的外地人口数量大为减少,但也由此产生了至少两代出生在上海、说着纯正上海话的人。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因为这座在近代吸引和容纳了全国各地移民的城市一度切断其移民根基,语言层面的“上海性”才被确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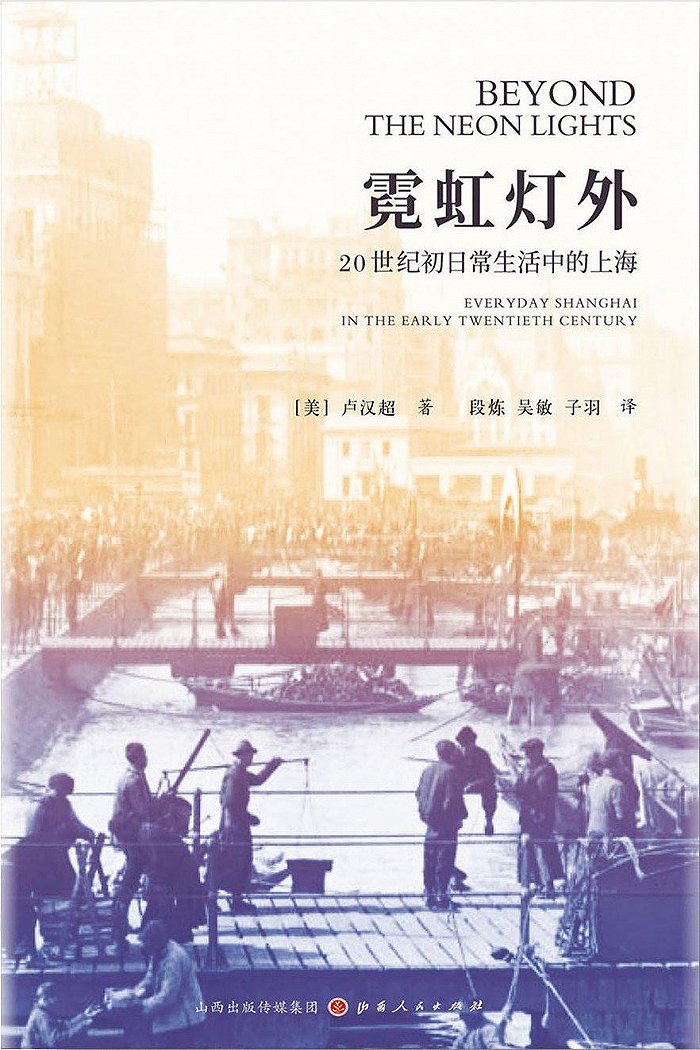
[美] 卢汉超 著 段炼 等译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8-9
或许也在不经意间,上海话成为剧版《繁花》的一个隐喻——符合这座城市特定叙事的人与事是筛选的结果。原著小说中的三个男主角只保留了阿宝,六七十年代这条线被从两个时代的交叉叙述中去除。剧版阿宝的资本家家庭背景被隐去,对其青葱往事的描述仅追溯到1978年,还是工厂工人的阿宝与公交车售票员雪芝(杜鹃 饰)的初恋。七十年代末正是政治逐渐从中国人日常生活中退居幕后、人们开始在私人生活中享有越来越多自主权的时段,大家开始在公共场合“谈恋爱”,比如1978年,刘香成在上海人民公园拍到了一对在老人严肃注视下坐在长凳上聊天的情侣。因此,阿宝与雪芝一起吃火锅、乘公交,是符合时代语境且适合用镜头语言描述的“纯爱”桥段。
另外几处闲笔淡淡触及阿宝的前史。玲子从日本回到上海,阿宝去玲子家拜访,上楼时看到一位男老师正在教孩子谈钢琴,不禁停下脚步若有所思。在这个镜头之前,字幕已提示观众钢琴在原著中的线索:“蓓蒂的钢琴,苍黑颜色,一匹懂事的高头黑马,稳重,沧桑,旧缎子一样的暗光。”阿宝帮玲子处理天花板漏水问题,爬上屋脊更换瓦片。玲子半调笑半试探地问,是否和女朋友在屋顶上看过风景,她人在上海吗。阿宝浅笑回答,“变成一条金鱼,游走了。”

落日阳光将石库门的屋脊和阿宝的背影镀上金边,此时旁白告诉观众,阿宝小时候喜欢和蓓蒂一起爬屋顶,眼里是半个卢湾区,蓓蒂是他的邻居,喜欢弹钢琴,那样的午后是他永远的童年记忆。“时光如水,把人和事带走,这些年被带走的,又何止蓓蒂一个。”电视剧用这句台词交代了阿宝的前史,它被抽离了时代阵痛,仅余一个个体对成长过程中朋友离散的一丝无可奈何。
根据生命历程理论(life-course theory),一代人青春后期的人格形成期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会塑造一代人的意识,那么应该来说,我们不能清晰地看到剧版阿宝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如何塑造了他的价值观。他毫不迟疑地纵身跃入了改革开放的大潮,无比顺滑地接受了新的时代逻辑——对一个奋进的人来说,过去不仅不重要,而且需要被抛却。
在剧中,同样被抛却的,还有原著小说的平民视角。金宇澄2014年接受采访时表示,《繁花》得到读者广泛关注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在内容上选取了‘非主流的视角’来重新发现‘平民城市生活的模糊区域’”,这正是剧版《繁花》与原著小说最显著的背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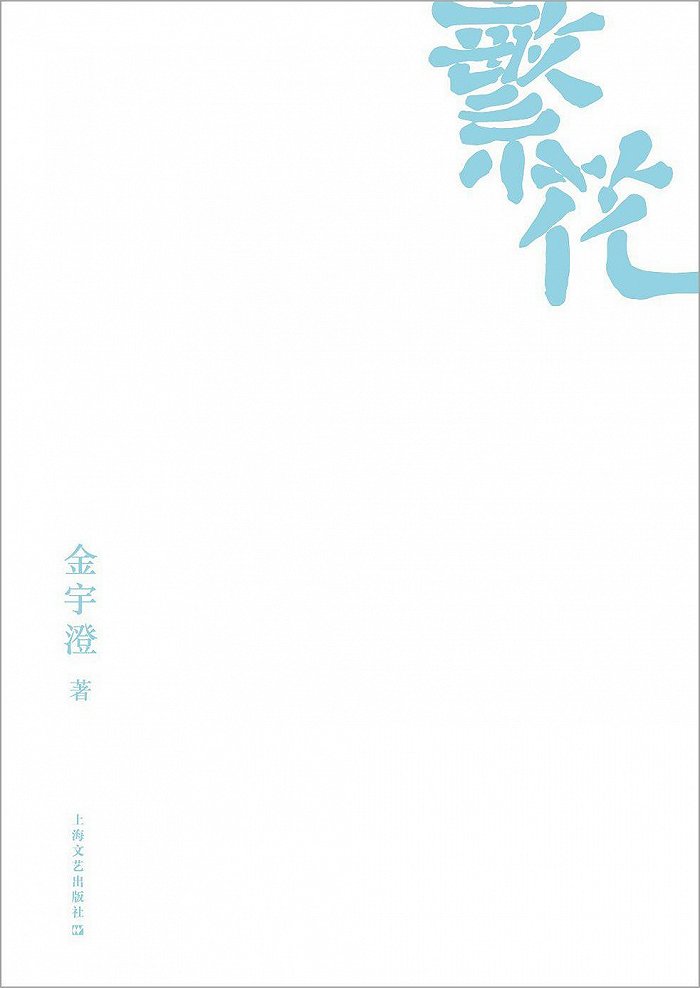
金宇澄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3-7
从挥金如土的阿宝、海鲜大户陶陶到满手金戒指“黄货压邪”的玲子、豪华饭店老板娘李李,剧中的主要角色都不是普通的市井之辈(即使是“夜东京”中的常客葛老师和菱红也是衣食无忧的人),剧中对城市景观的呈现也完全剔除了“下只角”。鉴于电视剧删去了(军人干部家庭出身的)沪生和(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小毛这两个主角,由他们的故事线蔓延出的更多元维度的上海生活图景也因此难以在电视剧中呈现。根据微博用户@文物医院的考证,《新民晚报》1990年12月公布了上海市的人均月收入——逾168元。这与剧版《繁花》对财富的呈现形成了鲜明对比:剧中人物动辄掏出一沓沓的百元现金,即使去南京路抢购“三羊牌”T恤衫的消费者也如卡通片人物般挥舞着钞票。
剧中戏份最多的“小市民”阶层人物或许是黄河路上的烟纸店老板,但他是一个纯粹的工具人角色——为剧中主要角色提供情报,为剧外观众解说剧情——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原创角色本人的故事线。在一个讲述上海大时代的故事里,普通人是否就是精英群体的旁观者和崇拜者?在经济高速增长期被摩天大楼的阴影和都市精英的光环遮蔽的,被时代抛下、努力追赶日渐遥远的梦想,或与逆境顽抗的小人物的人生,是否值得同样的注视?

因此,同样是描摹九十年代的热播电视剧,《繁花》与《漫长的季节》形成了一组有趣的对照:作为一个典型的东北故事,《漫长的季节》通过讲述经历集体主义、计划经济的终结和重工业凋敝之下的失意者、小人物的故事,让观众产生共鸣,因为我们如今和局中人一样面临迷茫与失落;《繁花》中的上海则被描述为抓住机遇的改革红利区,唤起观众对九十年代光明一面的怀恋,正如剧中旁白所说:
“走在1993年的南京路上,你会感到那是一个会飞起来的年代。我们庆幸生逢其时,与时代紧紧相连。一切尚未定义,一切皆有可能。”
这是上海版本的“向前看,别回头”。在《漫长的季节》中,火车司机王响在真相大白后呼喊着“向前看,别回头”,提醒我们既然过去的创伤已是定局,不如好好把握现在。在《繁花》中,阿宝也一直在“向前看”,他没有创伤,他从不回头。
(本文图片均来自豆瓣)
参考资料:
【美】卢汉超.《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山西人民出版社.2018.
连玲玲.《打造消费天堂:百货公司与近代上海城市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
金宇澄.《繁花》.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
【美】刘香成 【英】凯伦·史密斯.《上海1842-2010,一座伟大城市的肖像》.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
陈丹燕.《上海的风花雪月》.作家出版社.2008.
Ong, A. (2011). Introduction: Worlding Cities, or the Art of being Global. In Worlding Cities (eds A. Roy and A. Ong). https://doi.org/10.1002/9781444346800.ch
《<繁花>爆了:大家到底在寻找哪一个“上海”?》,三联生活周刊
https://mp.weixin.qq.com/s/iYjqvcRdgOQPsFSJQhOnJw
《向前看,别回头 | 2023年度流行作品与社会心态盘点》,界面文化
《内敛、奢靡与伪装:中国人如何在镜头前表达爱情?》,界面文化
《<繁花>将登话剧舞台 王家卫有意购买版权拍“美剧”》,文汇读书周报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