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心量是能够扩充的,读史就能不断积贮内心的资粮。历史学家王汎森在新书《历史是扩充心量之学》中提出,一个心量广阔充实的人,立身应事,志量视野都比较宽大;如果一个人心量过于狭窄,即使天资非常高,深度广度都有限,只能靠着一些小聪明(street smart)来应事。
心量这个词从佛经的“心量广大”而来,后由宋明理学的承袭和解释,发生了变化。理学家以心量大小来区别圣人与凡人。在他们的设想中,内心世界如同是一个很大的空间,需要用格物穷理的功夫把它填满、扩充开来。王汎森则借用了这个概念,讲述历史教养能够培育人的心量。
人的内心世界也是一个潜在无限大的空间,要用知识、经验去充填,它才会撑开,否则它会皱缩成一条窄缝。历史能够帮助让人们经历过去的事,并体会到生命的深度。这对人们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没有深度的生活属于贫穷的生活——它仅仅是从某一刻到另一刻(from moment to moment)的。另一方面,历史的教养也教人面对真正的现实,个人的现实世界因为可以纳入别人的事实而得到扩大,不再会任意主观投射自己的想法。此外,读史还能塑造人们的理性能力,使人们对事情的来龙去脉,乃至相续的因果关系有深切的把握。

王汎森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4-5
历史的情绪与人格
扩充心量的前提在于承认人的有限理性。在之前的讲演录合集《执拗的低音》中,王汎森已经提出,历史研究中后见之明式的解释倾向太强。与此相关的是,历史学家常常推测历史中的人物处于“完美理性”之中。他借用诺奖经济学得主赫伯特·西蒙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概念来阐明,历史行动者往往是在不确定、不完美的理性下走向未知的,他们的行为或抉择都并非穷尽(maximize)所有可能后的选项,或是充分了解所有可能的结局之后才做出的。相反,人们经常在时间仓促、情况模糊的情况下,凭借一点经验、知觉还有理性做抉择,而且这种抉择往往夹杂浓厚的情绪与偏见。

此外,历史学家考量历史人物时也应当区别热情的认知与冷静的认知,不应当忽略人们在判断事物时,情绪和武断性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我们常误以为历史行动者的主观预期效用中是全知的方式,而忽略了被情绪、热情所影响的部分。”
历史与个人心量想法的提出,亦与王汎森对20世纪历史研究的趋势判断有关:20世纪以来,史学流派基本上都倾向去人格化,或不再关心胸襟、器识、格局的培养。这源自于近代知识专业化进程,即学科知识与伦理、价值和生活层次等方面分离。在其影响之下,专业史学的进步与人生拉得越来越远,历史也变成了好像没有用的学科。
可是,历史果真与人生无关吗?他在序言中强调,现代专业史家应当思考这些被丢掉的老课题,包括历史对人格的培养、对价值和方向的引导等,对于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也当重新重视。在历史转型时期,人的作用尤为凸显,性格与心量的影响更不能忽略,“社会虽然有结构、经济、政治、潮流等因素,这就像个大水库,可是还得要有人打开水龙头,”王汎森写道。
王汎森将历史学的发展置于中国历史的撰写谱系中。清朝史学家章学诚就曾抱怨,中国历史上的正史写人物太为“格套”所拘束。所谓“格套”,恰与司马迁《史记》的千人千面列传写法相反。在《执拗的低音》里,王汎森引用刘咸炘的观点讲道,司马迁、班固之后有一个发展趋势是,史学的识见日益局狭,侧重朝政,而对群体民风不够注意,譬如刘氏认为游侠为华夏民风之一大端,学者多不注意,“班书以后,绝无《游侠》《货殖传》。”如此说来,要了解一个时代的历史,必须注重稗史杂记,才能显现出一个时代的士习与民风,《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这些书比正史更足以见民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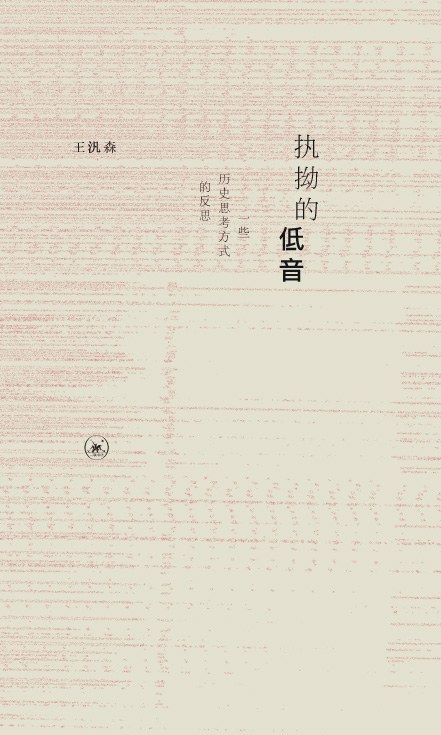
王汎森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0-1
理解历史中的“风”
把握无数事实知识仅仅是“记住”,把握历史的风势才是“撰述”。为了撰述历史,史学家当善于“观风”。不是将事情一件件拆开来看,而是能够将无数事实知识前后关系综合。历史的任务之一正在于察势观风。中国人喜欢谈风,诗经中也有“风”。可是风是什么?风是看不见摸不着,但令人们都深受熏习的力量。每一件事中都有风,小到装饰风格的变化、交朋友的风格,大到一个时代的风气——譬如北朝末年报应之说流行,源自南北朝的唐人节义不重、明中叶才士傲诞之气等等。
偶发的风势会塑造历史的变化,王汎森举例说,在历史上,往往有少数几个现实地位不高的人,靠着几篇文章或是几次演讲,而与某种政治社会环境中群众的关注耦合,一圈圈扩大而形成一股风,甚至形成风卷残云之势。许多影响历史的关键思想,最初并不明显,重要性也未被估计。正因为历史的关键时刻往往是微妙的、突然的,身处其中的人如果心量不足,就没办法以全副力量去加以处理。
不过值得补充的是,他也指出,某个时刻吸引人们跟着盘旋而起的风,不一定有智慧、合逻辑,也未必经得起严谨的知识验证,而是一些能弥补人们空虚、渴望的东西。或是因不景气、低收入、灾荒,或对精英政治彻底失望,其中有许多从后人的眼光看来恐怕是荒唐无稽的,可是当时人却不会觉察,用胡适的话说就是,“虽有智者,亦逃不出。”
理解了历史中的“风”,也应当看到“现在”包裹着属于不同时期的、不同性质的历史元素。他引用英国历史学家柯林伍德的“encapsulate”(封装)的概念,阐述为何现在不足以解释现在,“许多人都沉浸在一时一地的事情时,历史思考强调人们应当具有长程的眼光。”因为有些元素在过去已经存在,只是被包括在发展中,但从未消失。就像凯尔特人的艺术风格在长期消失后,仍能在19、20世纪突然复活一样。因此,历史也具有解放的功能,王汎森举例说,如果人们不知道心与物的分割其实是近一两百年才从西方发展而来的,就会把心与物的对立当成人的本质来讨论。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