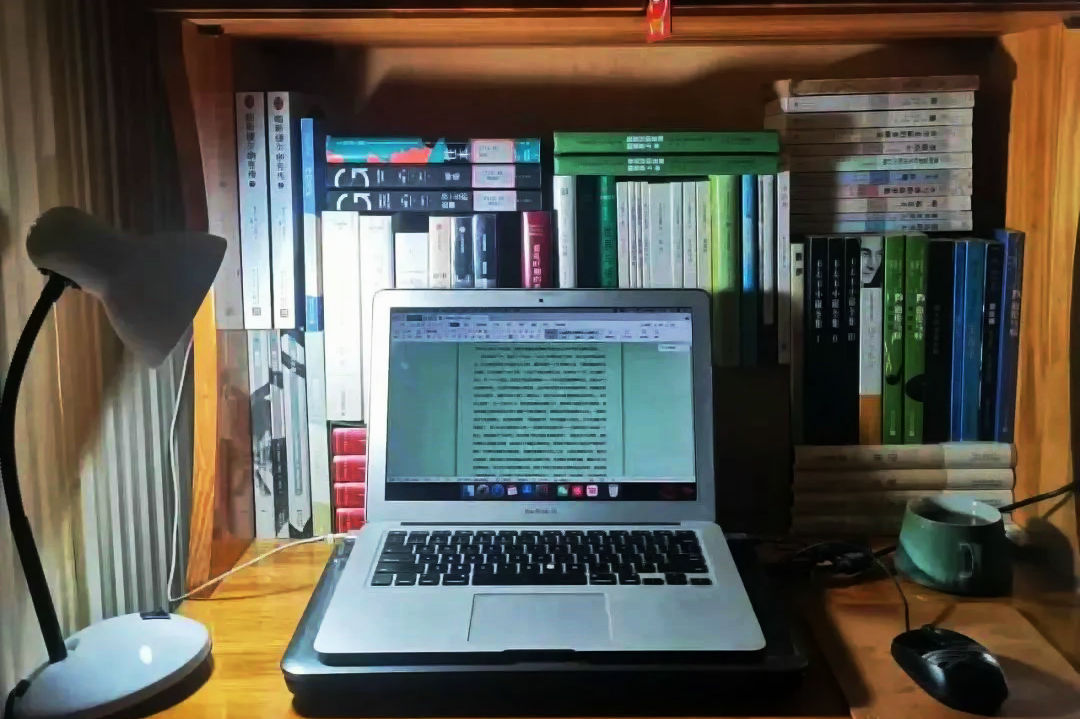文 | 胡安焉
编者按:在《我在北京送快递》热销之后,一些媒体把胡安焉当作“素人写作”的代表,尤其关注他的打工人身份。但这种标签过于片面,其实,他的写作经历至少可以追溯到2009年。在打工、开店的间歇,胡安焉持续创作,在黑蓝文学等平台发表过许多作品。在近日出版的新书《生活在低处》中,胡安焉回顾了童年和原生家庭对他性格形成的影响,以及走上写作之路的坎坷与精神世界的平和与自足。在自序中他说,“从来没有人用‘优秀’来形容过我,也没有人真正关心我的内心世界。”
胡安焉对美国作家卡佛说过的一句话记忆深刻:“作家要有为普通的事物,比如为落日或一只旧鞋子感到惊讶的禀赋”。而“普通的事物”也是他写作的耕耘之地。以下摘自该书第二章“我为什么写作”。
志向
我可以清楚地说出自己开始写作的日期,起码可以准确到月份,那是在二〇〇九年十月。但是我无法记起自己最初萌生写作这个念头的时刻。这就像大多数人都知道自己的生日,但很少有人知道父母是在哪一天创造了自己一样。不过我在梳理自己的记忆时,发现有一些不那么确定的时刻,它们或许不是唯一和决定性的,但肯定曾对我后来的写作产生过重要的推动作用。
比如我回溯到二〇〇四年,当时我和几个朋友离开广州,一起搬到了北京通州。我们对外宣称是为了创作漫画,我们也确实画了一些漫画,但和总体花费的时间相比,我们的产出少得可怜。因为我们几乎不怎么画画,多数时候只是在到处闲逛和聊天而已。此外对于合作画出来的漫画,我们的感觉也不太一样。因为我只是负责撰写脚本,对画画并不很擅长和喜欢,所以借助朋友的手实现自己的想法,我心里是满意的。
但我的一个朋友却觉得我的脚本写得太详细,使他作画时缺少自由度,因此也就没有了乐趣,他喜欢有一些发挥的空间,而不是充当我的作画工具。另一个朋友则没有那么在乎自己的空间和自由度,但他认为我写的故事太感伤,而那种感伤不像是属于一个年轻人的。实际上他连年轻人的感伤都不喜欢,更不要说我那种不年轻的感伤了。我对他的意见很认同,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但我只能想出那种感伤的故事。顺带一提,当年我二十五岁。就是在这个时期,有一天我们又在外面闲逛,路过一个食杂批发市场时,其中一个朋友没头没尾地对我说了一句:“我觉得你更适合写作。”
老实说,我不清楚他为什么这么说,但我当时没有追问。有人向我提建议时,我习惯点头说好,而不是问为什么。此外和朋友在一起,我喜欢充当听众,而不是表达观点。因此我常常交到喜欢表达的朋友,而不是和我一样沉默寡言的朋友,否则相处起来就会很尴尬。后来我常常回想,当年在朋友眼里,我有展露出什么写作上的才华吗?我觉得并没有,因为当年我根本没写过任何称得上作品的东西。要不就是我的谈吐比较温文尔雅?这倒是有可能,尽管这只是我给人的一种错觉。因为我顶多只能算是性格温和,但谈不上什么文雅。和同龄人相比,我情绪比较平稳,几乎从不激动,此外我很少不加修饰地表达内心真实的想法,这些特点都很容易让我的朋友误以为我是个有修养的人,但这显然还不足以被看成是某种写作上的天赋。所以当时朋友随口说的一句话,或许仅仅是看到我在画画上起点太低、悟性太差,觉得我还不如另辟蹊径算了——这就是我最后对那句话的理解。
不过这对我来说并不成为一个打击,我身上好像从来没有可被称为志向的东西。我确实曾想过做成一些事情,但那些想法既不强烈也不持久,显然无法称之为志向。如果说我真的不适合画漫画,那我就不画好了。我没有那种坚持己见,克服自身的落后和不足,去证明别人对我的看法是错误的动力。相反我倒经常理性地察觉到,我并不总比别人看得更准,尤其是在看待自己时。当然,我也可以画了但不拿给别人看,那样我就不必在乎自己画得好不好这个问题了。可是不给别人看我就没有画漫画的动力,我觉得自己并不喜欢画画,甚至也不能说是喜欢写作,起码不像我的有些朋友那么喜欢。我之所以去尝试除了面对面交流以外的一切表达形式,只是为了表达有些我在面对面交流时无法表达的内容。因此我的创作必须有读者,我也愿意取悦读者,我甚至愿意取悦任何人,或许只对那些特别坏或对我特别不友善的人例外。这才是我的本性。
我的朋友对我说我更适合写作的那一刻,或许不是一个对我后来写作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时刻。因为我在听到那句话之后,又足足过了五年才真正动笔。而在这之前我早已放弃了画漫画。当然我不否认,我确实是一个迟钝的人,经常在事情发生时听不懂别人想表达什么,而到了事后才省悟其中的含义——可那也不至于要花五年才理解一句这么简单的话。不过这句话应该还是触动了我,或者给了我某种自信——自信向来是我极其缺乏的东西——令我朝写作的方向靠拢了一点。这有点像一枚钉子得经过反复的敲打,而不是被一锤就砸进墙里去。
演员
另外一件对我写作产生过推动作用的事情,大约发生在二〇〇四年底,我离开北京前不久。严格来说,在那之前我和朋友就已经离开北京了。当时我们为了节省开支,从北京通州搬到了廊坊的燕郊。但燕郊和通州离得很近,我们从原来在通州的居所去往燕郊,甚至要比回北京市区更便捷,所以搬到燕郊并没有使我们觉得自己离开了北京。但是燕郊到底是个比北京落后得多的地方,那里不像北京,到处有鳞次栉比的建筑和琳琅满目的商品——起码当年还没有——却有大片大片的玉米地和干枯的河床。换言之,在燕郊人们的消费选择很少,而且主要是一些中低层次的选择。
我们住处附近唯一的一家医院,光看建筑外观很容易让人对它信心不足;而一旦你走进医院里面,剩余的那点侥幸心理也将荡然无存。不过,我从头到尾都没去过那家医院,甚至都没设想过自己可能走进那家医院。那时我还年轻,身体很少出问题,而像感冒之类的小病我会自己买药吃,所以没什么机会进医院里看病。当时我和朋友都没有工作,我们没有收入,但我一点也不担心。我们的日子过得既逍遥又拮据,在最窘迫的时候,每天只能自己动手煎饼子吃——幸好我们还有一袋面粉——连买菜的钱都没有了。但就算是这样,我也丝毫没有紧张。因为在千里之外,我还有一个家和父母,我知道他们不可能看着我饿死而不管——虽然他们强烈反对我到北京。
事情发生的那天,忘记是为了什么,我独自从外面返回住处。路上我买了两只光饼,拿在手里边走边吃。在路过上面提到的那家医院时,有两个农村妇女突然拦住了我。在她们拦下我之前,我完全没有注意到她们,因此多少有些愕然。我记得她们头上缠着毛巾,那种打扮即使在当年的燕郊也不多见,因此我不难推断,她们应该来自附近的农村。我对燕郊附近的农村了解不多,只是有一次,我坐930 路跨城公交去三河市,途中看到了大片大片的农田,不过除了玉米秆以外,我认不出绝大多数农作物。
我以为她们是要向我问路,我已经准备好回答不知道,因为我才搬到燕郊没多久,很多地方都没去过,而且去过的地方我也说不清楚,我很怕自己说错了误导别人。可是她们并不是来向我问路的。其中一个妇女对我说——原话我已记不得了,不过她的意图很简单,不必逐字还原也能复述出来:她想要我手上的一只光饼,我还没有咬过的那一只。
虽然我不记得她当时的措辞,但我记得她的语气和表情。相比于她说的话,她的语气和表情给我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假如要用一个词来形容,我觉得可以用“坦然”。就像这个请求她已反复提出了无数遍,其中假如原本还包含了什么感情和意味,那也早就挥发殆尽了。或是我本来就该在那个时刻出现在那里,等着她们来向我要一只饼。而她们果然来了,不过是履行自己的职责,接下来就轮到我了——这里面没有丝毫偶然的成分,她们并不冒昧而我也无须意外。这就是命运。或者说,命运常常给人这种感觉:就像我们并不是我们自己,而只是在扮演我们的一群演员。
在我对眼前的情形做出反应之前,那个妇女又接着说道,她的男人送到医院里了。她没有解释更多,就像这句话已经足够说明情况。我自然也没有追问,因为那句话确实已经足够——事实上她不说都行,她不说的话我心里还好过一点,而且同样会把手里的饼奉上,仅仅因为我不喜欢拒绝人。假如她的男人年龄和她差不多,那也不过是个四十几岁的中年人。我总不能问她:“假如你连买一只饼的钱都没有,那你的男人躺在医院里又有什么用?”
我当即就把手里的饼给了她,她接过后掰成两半,边转身走开,边和身边的同伴分着吃了。她们都没有向我说谢谢,要不就是她们从没接受过这种教育,毕竟看样子,她们平常根本不会主动和陌生人说话;要不就是和她们正在承受的事情相比,向人道谢这种礼貌上的讲究显得太过浅薄和造作,以至于不合时宜。相反倒是我想向她们道歉,尽管我不清楚自己做错了什么,但我感觉有那种冲动——作为一个相对而言幸运的人,为她们的处境和所遭遇的一切道歉。
不过话又说回来,她们遭遇的不幸实在太常见,即使相比我贫乏的过往,它也不算一件特别深刻或重大的事件。不说那些和我关系没那么亲近的人,就拿我的父亲来说,在我十岁的那一年,他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开胸手术。为了修补那次手术带来的后果,他又接连接受了两台四级的大手术。在第三次手术之前,医院让我母亲在病危通知书上签了名。主刀医生对我们说,要做好病人不能出手术室的心理准备。他省略了状语“活着”,显然是为了照顾我们的感受。如果说十岁的我还小,不懂得事情的严重性,因此受到的冲击不大,那么在我二十七岁那年,父亲又再次在我面前中风倒地——这次是我亲手打 120 叫来了救护车。
和大多数人一样,我当然更关心自己的父亲,而不是一个连面都没见过的陌生人。同时基于理性我也认识到:世界上有那么多医院,每个医院里有那么多病人,这些病人又都有各自的亲戚和朋友,我只是没有机会碰见他们,但他们遭受的痛苦和不幸并不比我碰见过的那些更轻。可是尽管如此,父亲和这个世界上千千万万不幸的人带给我的感受,都无法取代那个农村妇女和她躺在医院里的男人带给我的感受。当我父亲躺在医院里时,我确实感受到一种尖利的难过,以及深刻的恐惧和无助。就程度而言,这不是后者带给我的感受可以匹比的。但是父亲的不幸带给我的感受,似乎在成分和来由上都有迹可循,它是一种因为性质单一而较为容易理解的感受。哪怕是它的尖利和深刻,似乎也是一种较为容易理解的尖利和深刻。
可那个农村妇女向我讨要一只饼时,我的感觉就没有那么容易解析了。不过,我绝不是指当时自己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或者大为震撼之类的。不是那样,完全没有那种戏剧化的冲击和震撼。事实上,在经历了那件事之后的一天,我过得和之前一天一样;在经历了那件事情之后的一周,我过得也和之前一周一样。我的生活和我本人都没有立刻发生什么变化。故此这件事肯定不是以某种直接和显性的方式影响了我。甚至我都说不清楚它影响了我什么,但影响肯定存在——可能是改变了我对生活的看法,或者改变了我感知生活的方式,或者只是把我意识中混沌的部分变得更加混沌。
如今回过头看,我认识到一个人的经历不仅是他遇到的事情本身,而且应该包括在事情发生时,他的处境和状态等方方面面的因素。非此我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些明明很重要的事情,对我精神施加的影响却微乎其微;而有些分量不重或者莫名其妙的经历,却令我在很多年后仍感觉到其中的意味深长。我还想起了一件事:那天我独自路过那家医院,很可能是在从银行返回住处的路上。当年我和朋友们总是结伴外出、一起行动,只有去银行我会独自一人,而我去银行是为了取父母汇给我的钱。尽管我父母反对我留在北京,但当我向他们求助时,他们仍然立刻把钱汇给了我。那段日子里我好像总共跟他们要过两三次钱,总数是两三千,这笔钱我后来没有还。而遇到农村妇女的那一次,如果我真的是从银行取钱回来的话,那肯定就是最后一次了,因为在那之后不久我就离开了北京。
“疯女人”
第三件我认为对自己写作产生过推动作用的事情,发生在二〇〇九年的某一天——确切一点说,是那年的一到八月里的某一天。当时我和一个合伙人在南宁的一家商场里经营着两个女装门店。到了那年的八月底,我退出生意,然后离开南宁,至今再没有回去看过。在这个女装生意的最后时期,尤其是在我决定退出但人还没走的那几个月里,我买了一些小说放在店里,空下来时就拿出来读。那个商场每天从早上九点经营到晚上九点半,但除了节假日以外,平常直到下午三四点才有顾客来逛,所以我每天都有好几个小时的空闲时间。如今我记得自己当时买的那些小说,其中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卡佛,还有塞林格,其余的我就记不起来了。以我今天的眼光看,当年我买书很随意,基本上书店的陈列架推荐什么我就买什么,而我好像还以为自己花了心思挑选。
那段日子的阅读确实给了我很多触动,当年我认为是那些作品打动了我,但今天回过头才看清楚,打动我的其实是我的生活,而不是那些作品——那些作品只是触发了我对生活的感动而已。我还发现自己不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和我认识或遇到的大多数人相比,我都更不容易高兴、难过、生气或兴奋,这或许是由于我习惯了压抑自己的感受。我想假如不是我的讨好型人格在作祟,我会变得对人非常冷淡——虽然现在已经有不少人说我太冷淡。这种冷淡是由于在很多社交场景里,我无法和那些感情远比我丰富的多数人共情。有时我甚至怀疑别人是在演戏,也就是我不相信他们真的会为一些在我看来很无聊的事情激动。
不过,我承认他们没有那么做的动机,反倒是我经常在演戏,我的动机是想要迎合别人。然而当我接二连三地遭遇不顺心的事情,或者陷在糟糕的生活里无法挣脱时,我发现自己的感受力会随之变得更敏锐。或许这是不幸对我的馈赠吧——尽管一提到不幸我就脸红,因为我并没有遭遇过什么特别的不幸;而一般程度的不幸,我想每个人都有过。但我不习惯也不喜欢向人倾吐,我极少告诉别人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尤其是那些负面的感受。或许因为这个缘故,我体内的负面感受很难挥发掉,而这使我在阅读时变得更容易被感动。于是在南宁的商场里,我凑齐了这两点必需的因素:生意上丑陋的竞争和冲突给了我糟糕的生活,而空闲的时间给了我书。前面提到的那件后来对我写作产生过推动作用的事情,就发生在这个时期,发生在我的女装店里。
那天我一个人在看店,有个女顾客走了进来。她看起来很紧张,甚至有些害怕,脚步迟迟疑疑,但又竭力保持镇静,像一只夜晚出来觅食的啮齿类动物,任何风吹草动都会促使她立刻逃跑,逃回自己安全但暗无天日的洞穴里——这个女人有精神问题,这点不仅我知道,周围所有店主都知道。她可能就住在附近,所以经常来逛我们商场,但逛进我的店里还是头一回。每次她来,周围的店主就在她身后互相打眼色、捂着嘴窃笑。假如她走进了谁的店,其他人就一脸坏笑地看热闹。背地里大家都叫她“疯女人”,但她不是那种带有攻击性的疯子,她的“疯”主要体现在胡乱搭配的衣着、奇怪多变的表情,以及走路时不自然的姿势。她和人说话时也和一般人表现不一样,不过在那之前我还没有和她说过话。她逛进我店的那天,手臂上还挂着一只明黄色的提包,那只提包因为体积很大也显得有些怪异。不过我想假如换一个人来提,可能也没有多么怪。
我当然明白精神失常和正常之间,并不是一种像黑和白那样的关系,而是一种像深灰和浅灰那样的关系;我也明白没有一条确凿无疑的界线可以彻底地划分这两者。我看着她一件一件地翻看我货架上的衣服,同时意识到周围的店主已经把注意力集中到我的店里来了。我还知道那些注意力并没包含多少善意——我和周围店主的关系很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然后那个女人问我,能不能试穿一条牛仔短裤。我告诉她可以。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她很亲切,而且很熟悉,尽管在此之前我还没有和她说过话,甚至没有认真地打量过她。我想部分原因可能是,我对周围这时加诸她身上的恶意很熟悉。
我看着她把短裤从带夹衣架上取下来,可她并没有走进试衣间,而是直接在店面里,把两条腿分别伸进了裤管里。然后她提起裤子,把短裙撩起,对着镜子照了起来。我记得自己惊呆了。反应过来后,我尴尬地告诉她,旁边有试衣间。可要不就是她认为我不可能在和她说话,要不就是我的声音小得只有自己能听见,总之她没有任何反应,甚至都没转头看我一眼。因为她丝毫不感到难堪,难堪就转移到了我身上。不过我的难堪才刚刚开始,因为就在我的目光关注下,她又接着往腿上套第二条短裤了。我眼睁睁看着她想把它套在第一条短裤的外面——那根本就办不到——在两条短裤之上,还有她自己穿来的一条短裙。
我就像闯了祸似的站在旁边,没有勇气再提醒她有试衣间。她显然不知道试衣间有什么用,或许也理解不了自己当着我的面撩起短裙有什么不妥;我也不认为自己有能力帮助她建立这些认识。事实上我发现连和她说话都很困难,这不是她能不能理解我的问题,而是她好像完全无视我的存在。她在进店问了我一句能不能试穿后,就仿佛我从她的世界里消失了,接下来她的一举一动完全可以用旁若无人来形容。
就在我手足无措时,我再次震惊地看到,她取下第三条短裤,正准备往自己腿上套,而前面的两条短裤还挂在大腿上。她这么做完全没有意义,可是说这个有什么用呢?她可能从一开始就不明白为什么要试穿,只是有人曾教过她这么做,她就把这当成某种必需的仪式。突然之间我觉得心里很难受,我自己也说不清楚这种难过的成分。可是让一个顾客在我面前套上三条牛仔短裤这样的事情实在太荒唐,于是我几乎是下意识地伸出手,按在她的一只手上,我想告诉她:别这样。可她直到这时才察觉我在旁边似的,突然抬起头看向我,四目对接,她的表情里包含了惊恐和委屈,就像一个被自己信任的人伤害了的孩子。她的年龄虽然不太好准确判断,但肯定是在三十到四十之间,我从来没有在这个年龄的人脸上看到过这种表情。与此同时,我的眼睛也湿了,眼泪随时要夺眶而出……从她的脸上,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自己,她就是另一个我——惊慌,恐惧,孤独,委屈,被人不怀好意地围观,腿上还挂着三条牛仔短裤——只不过我还有力气遮掩,她却只能就这么袒露出来……我缩回了手。
最后她买下一条短裤,我默默看着她拉开那只明黄色的大提包,里面空空荡荡,底部散落着一些纸币。她一张一张地拣出来,先捋平整,再叠成一沓,然后递给我。她数出来的金额是对的,这说明她可以分辨纸币的面值。但不知道为什么,她脸上仍然挂着一副惶恐的表情。或许她不是在害怕什么,而是害怕本身已经固化在她的精神里。我想假如我脱掉自己的面具,我的表情大概不会比她的“正常”到哪里去。
如果说我从这件事情里得到了什么启发,那大概就是由此更加看清了自己:在深灰和浅灰之间,我离这个女人要比离大多数人近得多。此外,这段经历和五年前我在燕郊遇到那两个病属的经历一样,其中都包含了一种否定性的启示,令我意识到自己当时的生活偏离了正轨,过得毫无意义。事实上在这两件事情发生后不久,我就分别离开了北京和南宁。然而有意义的生活应该追求些什么?对此我并没有一个现成的答案。或许,写作会是一个选择。
失控
第四件对我后来写作产生过推动作用的事情,严格来说更像是一个隐喻。这件事发生在二〇〇九年底,也就是遇到“疯女人”后的几个月,当时我刚离开南宁,回到广州还没几天。一个中午,我走在一条马路上,马路对面突然拐来一辆电动车,逆行朝我冲了过来,直到车轮擦到我了才刹停。我被吓了一大跳,不过并没有受伤,那是一辆搭客的“摩的”,但车上只有骑手一人,他是为了赶在绿灯的最后几秒冲过马路,所以才开得那么急。可是他显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不对,因为他不但没有向我道歉,反倒质问了我一句:“你为什么走得这么急?”听到他这么说,我瞬间情绪失控了,那是我第一次在公共场所失控,我反问他为什么逆行,他避而不答,于是我用拳头砸了他的肩膀一下——不过那只是象征性的,并不是能打伤人的一拳。
他看到我暴怒的样子,有点愣住了,虽然仍在反驳,但声音很小,语气也收敛了。就在这时,旁边站出来一个男青年,挡在了那个骑手身前。他当时说了些什么,今天我已不能一字一句地回忆起来,大意是说那个骑手属于弱势群体,挣钱很不容易,我不该欺负他。而我好像反问了他假如骑手蹭到的不是我,而是一个孕妇,那该怎么办。我和他就这么拌了几句嘴,最后他说,你要打架就和我打。不过当时我们站在一个公交站旁边,有不少人在那里等车,其中多数是老年人。我们吵架的时候,他们就在旁边围观,当男青年说到打架时,几个老人马上站了出来,把我们俩分开。老人们对我们说,年轻人不要为了一点小事就冲动。虽然我很生气,但老年人的话确实有道理。
这次小小的冲突,是我生平第一次在大街上情绪失控。在此之前,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一面,也不相信自己会在大街上朝人大吼大叫。由于我暴露出连自己都不知道的一面,这触发了我的反思。继而我认识到,从南宁回来的我,已经不是一个完好无损的我。曾经我的精神被一层厚厚的外壳包裹住,尽管因此变得反应迟钝、感知麻木,但同时也不容易受到刺激或伤害。可是这层外壳在南宁已经磨损并破裂,令我失去了保护,变得敏感和脆弱,同时又易怒和歇斯底里。过去我不在乎的一些事情,如今却变得非常在乎;而另外一些我从前在乎的事情,这时却变得不再在乎了。
此时,我看着大街上洪洪的人流,很清楚自己已不想融入其中。可是孤独地在漫无目的中摸索,我又害怕被那虚无的深渊吞噬。无论是什么,我希望有一件事情,是我可以投入其中,同时又不必为此和我厌恶的现实打交道的。这一年我刚好三十岁。
我很清楚自己的写作,从最初就怀有一种逃避的动机。比如说,躲到想象和虚构中,而不是活在现实生活里。我可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去上班也不交际,因为我还要写作——这或许不是个很好的理由,但毕竟算是个理由,而且不妨碍别人什么。这也称不上是一个好的出发点:为了逃避而投入写作。但我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我就像个溺水的人,能捞到什么算什么。再说,哪里有那么多好的出发点啊?我出生到这个世界上,本身就不是个好的出发点,那么凭什么我的写作会有一个好的出发点?不过,这确实是一个我必须克服的问题:不是关于出发点,而是关于一种端正的心态。
或许直到今天,我都没能完全克服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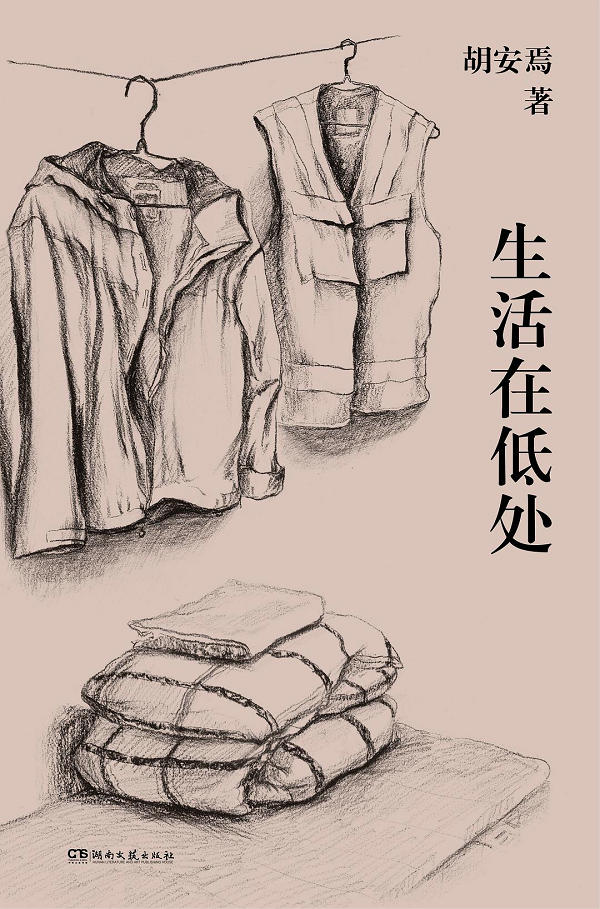
——完——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