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在2018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尼日利亚小说家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被授予品特奖,该奖项旨在奖励那些在作品展现了“生活和社会的真相”的写作者。她在获奖演讲中说:“有时候政治必须被当做政治来讨论。今天没有比这更正确和更紧迫的事实——我们必须知道真相是什么,我们必须把谎言称作谎言。”
对于真相和谎言之间的界线与转化,第三帝国的历史或许为我们呈现得最为全面和深刻。毕竟纳粹领袖约瑟夫·戈培尔就曾说过,将谎言重复成真理是纳粹主义的核心。法西斯主义的核心是欺骗吗?说谎者相信自己撒的谎吗?他们能够识别虚假吗?还是在纳粹的知识与信仰体系内,谎言已经作为真相说服了他们呢?这是宣传达到的效果呢,还是神话发挥的作用呢?个人信仰转变成政治认同是如何发生的呢?阿根廷历史学家费德里科·芬切尔斯坦在《法西斯谎言简史》一书中试图探索和探讨的正是这些问题。
撒谎和政治一样古老,法西斯得势的历史也即谎言掌权的历史。正如阿迪契所言,“今天没有比这更正确和更紧迫的事实——我们必须知道真相是什么,我们必须把谎言称作谎言。”
《为什么法西斯主义者相信他们的谎言即是真相?》(节选)
撰文 | [阿根廷]费德里科·芬切尔斯坦
翻译 | 张见微

有些人说得有鼻子有眼,却没有一句真话,气得我照着他们的脸就是一拳。证人们尝到了我的厉害,又编出一套谎话。我不相信,但不敢置之不理。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最著名的法西斯主义宣传家、纳粹领袖约瑟夫·戈培尔说,将谎言重复成真理是纳粹主义的核心。这句话经常被误引,导致了一种法西斯主义形象的产生,好像法西斯分子充分意识到自己蓄意造假的程度。法西斯主义的核心是欺骗吗?说谎者相信自己撒的谎吗?他们能够识别虚假吗?当戈培尔说希特勒无所不知、“天命所归”时,他是否真的具备一种基于现实的知识概念?
这很复杂。事实上,戈培尔曾经伪造并发布过自己遇刺的消息,后来他把这一消息作为事实“刊登”在自己的日记中。这些日记并非写给公众看的,而是在他死后多年才出版。他还在其中一次次提到自己的演讲取得的“成功”,它们得到了他所控制的媒体的称颂。是戈培尔在自欺,还是他真的相信存在一种超越实证的真理形式?难道他想要编造一个新的现实吗?当然,从基于现实的角度看,编造谎言与信奉一种魔幻的真理观念毫无区别,都是在逃避真实。戈培尔分明是在通过发明另一种现实来欺骗自己,但他和大多数跨国的法西斯主义者都不这么认为。

对于戈培尔这样的法西斯主义者来说,知识是一个关乎信仰的问题,尤其是对法西斯主义领袖神话的深信。正如操纵或发明事实是法西斯主义的一个关键维度,对超越事实的真理的信仰也是其关键维度。法西斯主义者并不认为真理与宣传之间存在矛盾。
戈培尔将宣传定义为“一种艺术,不是怎样去说谎或歪曲,而是如何去倾听‘人民的灵魂’和‘用一个人能听懂的语言跟他讲话’”。正如历史学家理查德·埃文斯评论到的,“纳粹党人的行动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他们且只有他们,通过希特勒,对德国人的灵魂有了内在的认识和理解”。真理源自灵魂这种想法,是信奉无法证实的绝对确定性的结果。
每当阿道夫·希特勒要颠倒是非的时候,作为症候性的表现,他会谈论起大是大非。在他的理解中,与他的种族主义理论相悖的事实都是谎言。他的世界观建立在一个无需实证的真理概念之上。换句话说,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是真的东西(可证实的因果关系的结果),对他来说却有可能是假的。我们当中的大多数认为是谎言或捏造的事实,在他看来却是真相的高级形式。就像当今的民粹主义媒体所宣称的,希特勒将自己对真相的不诚实投射到他的敌人身上,从而颠覆了现实。他谎称说谎者是犹太人,而非他。他说起谎来就好像他代表了真理。他指责犹太人“大大地扭曲了真相”。但希特勒却将这一实际真相等同于他所信奉和宣扬的反犹太神话。
在利用谎言和诽谤方面,首屈一指的行家一直是犹太人;毕竟,他们整个的存在是建立在这个巨大的谎言之上,即他们是一个宗教群体,但实际上他们是一个种族——一个种族!人类最伟大的头脑之一(叔本华)已一针见血地戳破他们:他称他们为“谎言大师”;这个说法是颠扑不破的。任何认识不到或不愿相信这一点的人,将无法帮助真理在这个世界上取胜。
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不仅希特勒,阿根廷和世界各地的其他许多法西斯主义者都视反犹太神话为真理的体现——德国犹太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称之为“依照计划的神话”。法西斯主义者幻想出一个新的现实,然后去改变实存的现实。因此,他们重新划定了神话与现实之间的边界。神话在取代现实时所凭借的政策,旨在依照种族主义相信的谎言重塑世界。当反犹太主义的谎言声称犹太人天生肮脏且会传染,因此应该被杀掉,纳粹党人则在隔都(ghetto)和集中营里创造条件,让污秽和广泛传播的疾病变成现实。犹太囚犯在忍饥挨饿、受尽折磨、彻底沦为非人之后,变成了纳粹党人打算让他们成为的样子,也就可以被名正言顺地杀掉。法西斯主义者通过将隐喻变成现实的方法,追求与经验世界不相符的真相。法西斯的意识形态谎言没有丝毫真实之处,然而其追随者却想让它们足够真实。于是凡是他们亲眼所见的和不喜欢的,皆被设想为非真实。墨索里尼认为,法西斯主义的一个核心任务就是否认民主制度的谎言。他还将法西斯主义的真理与民主的“谎言”相对立。道成肉身原则是领袖(ilDuce)的这一神话式对立的核心。他相信一种超越民主常识的真理,因为它是先验的(transcendental)。他回忆道:“在我生命中的某个时刻,我曾冒着不被群众看好的风险,向他们宣布我所认为的新的真理、神圣的真理(laveritàsanta)。”

对墨索里尼来说,现实必须遵循神话的要求。如果人们一开始就不相信,事情就难办了;他们的怀疑也需要受到质疑。法西斯主义的神话框架植根于法西斯主义的民族神话。他宣称,“我们希望将[这一神话]全然变成现实”。神话可以改变现实,现实却不能妨碍神话。法西斯主义的这一神圣真理,同样是由法西斯的真理与敌人的虚伪本性之间的奇特界限所定义。敌人处在真理的对立面,有的只是谎言。在欧洲边境地区,人们陷入“对俄国神话的执迷”,对布尔什维主义着了魔,但墨索里尼认为这些与自己竞争的神话是虚假的,因为它们反对基于极端民族主义的绝对真理,当然也反对他的领袖神话。他说:“我们将其他一切置于[这一领袖神话]之下。”
在将神话进行现代化的过程中,法西斯主义者将神话从个人信仰问题转变成政治认同的主要形式。根据这一改写,真正的政治是古老而暴力的内在自我的投射,这种自我在被应用于政治时,克服了理性的诡计。如此一番操作,法西斯主义者便可以把一切符合其意识形态目标、假定和欲望的东西定义为真实。
法西斯主义的这一神话维度是反民主的。从历史上看,民主乃是建立在与谎言、错误的信念和信息相对立的真理的概念之上。与此相反,法西斯主义者提出了一种关于独裁统治的激进的真理观念。正如历史学家罗伯特·帕克斯顿解释的,对法西斯主义者来说,
“凡是允许新的法西斯主义者支配他人的,凡是让上帝的选民取胜的,都是真理。法西斯主义不依赖于其信条的正确,而是依赖于领袖与其人民的历史命运的神秘结合。这让人联想到浪漫主义者关于民族历史的繁荣、关于艺术或精神上的个体天才的观念,不过法西斯主义在其他方面否定浪漫主义对无拘无束的个人创造力的推崇。”
法西斯主义者将人民、国家和领袖这三者隐喻性的统一,建立在将神话视为真理的终极形式之上。但他们这样的做法不乏先例。真理与谎言在法西斯主义中的异乎寻常的地位,不过是真理与政治漫长的关系史中反复出现的一个方面。在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看来,政治史总是呈现出与真理的紧张,而法西斯主义对这种紧张的解决,意味着对政治的破坏。要界定法西斯主义,其中一点便是有组织地撒谎。只有领袖规定的事实(和谎言)才可以被接受为真相。

以宣扬另一种现实为名歪曲真相,是法西斯主义历史上常出现的现象。西班牙法西斯独裁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否认自己参与过对格尔尼卡的可怕轰炸,这是他最大的战争罪行之一,造成了上千人死亡。虽然法西斯政府的这次行动有据可查,但佛朗哥声称是“红军”“摧毁了格尔尼卡”,旨在散播有关他的“宣传”,抹黑他。在这么做的时候,佛朗哥把真相的概念揽在手中,声称说谎者并不是他,而是他的政敌。
同样,纳粹党人也没有区分可观察的事实与受意识形态驱使的“真相”。当“群众领袖攫取了让现实来配合其谎言的权力”时,极权主义独裁最激进的结果便出现了。几年后,在关于阿道夫·艾希曼的引发争议的研究中,阿伦特对这位大屠杀策划者的推理过程进行了重要的探究。艾希曼可谓“对事实本身极其蔑视”这一现象的缩影。阿伦特将艾希曼对谎言的认可等同于整个社会“对现实和事实的屏蔽,以完全相同的方式,以相同的自欺、谎言和愚蠢——它们如今已在艾希曼的头脑中根深蒂固”。
为什么法西斯主义者相信他们的谎言即是真相?正如许多反法西斯主义者彼时曾指出的,法西斯主义独裁的历史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被法西斯主义者推举为现实的神话性想象永远无法得到证实,因为它是基于全面控制过去和现在的幻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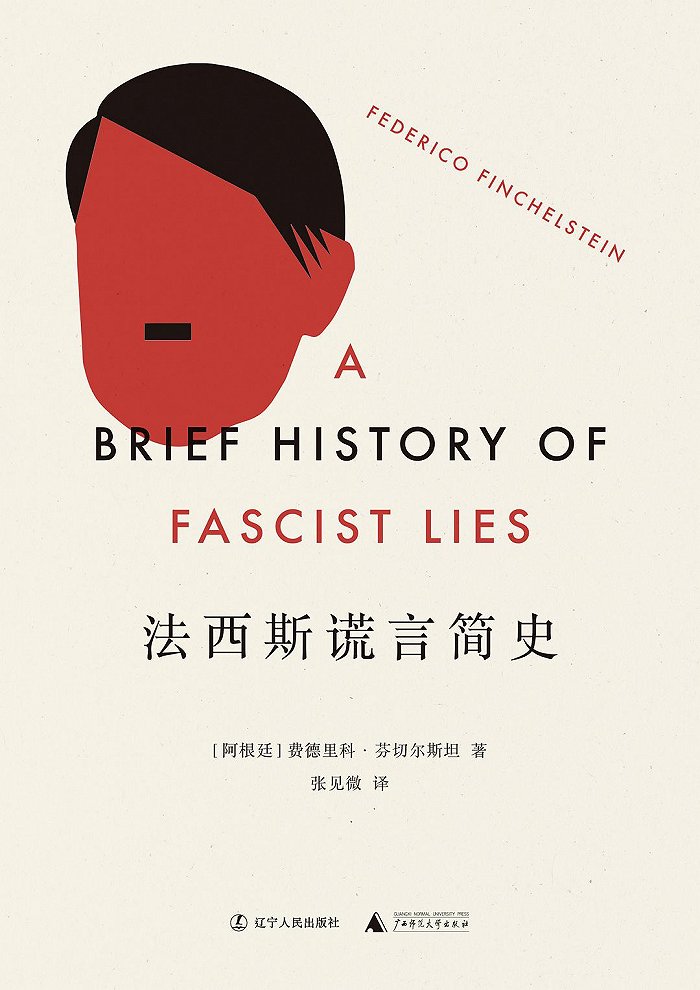
[阿根廷]费德里科·芬切尔斯坦 著 张见微 译
一頁丨辽宁人民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12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法西斯谎言简史》第一章,注释从略,较原文有删节,标题为编者自拟,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