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编辑 | 黄月
家长在生日蛋糕上插满课本让孩子大哭、“985硕士妈妈”嫌弃孩子是学渣,这类视频屡屡登上热搜,更不要提“双减”前被奇观化的海淀妈妈(总是妈妈,没有爸爸)和“双减”后周末脱不开身的家长。城市很多中产家庭里的父母和子女,似乎都在为教育焦虑和痛苦,而一些民间家庭的教育实践要么很少被主流话语关注,要么成为被凝视和同情的他者。
北京师范大学研究员安超在《拉扯大的孩子:民间养育学的文化家谱》一书中指出了民间教育实践被轻视的现状。在学院内部,大量教育学研究被布迪厄的阶层研究理论统领,强调家庭文化资本决定个体社会地位。阶层理论可以有力地解析和批判结构弊病,但单一的视角也可能带来对民间民众教育实践的贬低——民间教育既提供不了经济资本也没有文化资本,成为了需要被弥补、被解放的对象。同时,对民间教育的研究也缺乏主体性,民间父母在传统养育中的实践性知识被忽略了。

安超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年
安超从小在山东农村长大,后来读书升学并进入城市工作生活。在博士期间,她回到山东乡下老家生产,感受到早已体认的现代城市精细化育儿与乡村养育经验的巨大冲突,这也让她决心重新回望个人家族教育史,审视被现代科学育儿话语所轻视的“庶民教育”。庶民是区别于贵族的群体,除了养育孩子,还要为生计奔波,他们也不同于掌握了精细化育儿标准的城市中产阶级,而更多凭借直觉与经验进行养育实践。
反思当下结构性教育焦虑,拥有话语霸权的“科学育儿”和“精细育儿”是唯一“正确”的养育方式吗?我们是能否在缺少“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加持的庶民教育里看到更多温度与能量,并打开对城市养育方式的想象?在教育成为“家庭资源投入的无底洞”(社会学家渠敬东语),越来越多的女性退出职场、代际矛盾加剧之时,城市育儿是否可以借鉴庶民共养经验,超越原子化家庭,构建互助的养育共同体?
焦虑的母亲,疲惫的儿童
在《给无价的孩子定价》一书中,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社会学教授维维安娜·泽利泽(Viviana A. Zelizer)探讨了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儿童的社会价值观念转变:儿童从家庭中的劳动力转变为“经济上无用,情感上无价”的存在。这一针对美国社会的描述也极其契合中国几十年来儿童角色的巨大变迁,如今的孩子几乎不参与任何生产性劳动、成为家中所有人的情感寄托,同时也被期待在道德上无暇,家长严格地筛查动画片是否有阴暗的画面、不准孩子和成绩不好的“坏孩子”做朋友,不允许任何玷污孩子纯洁性的风险存在。安超认为,教育焦虑最根本的危机是儿童对成人的经济依附和成人对儿童的情感依附,“结果就是我们一边无微不至地照顾孩子,一边把他们禁锢在家庭、游乐场、电子产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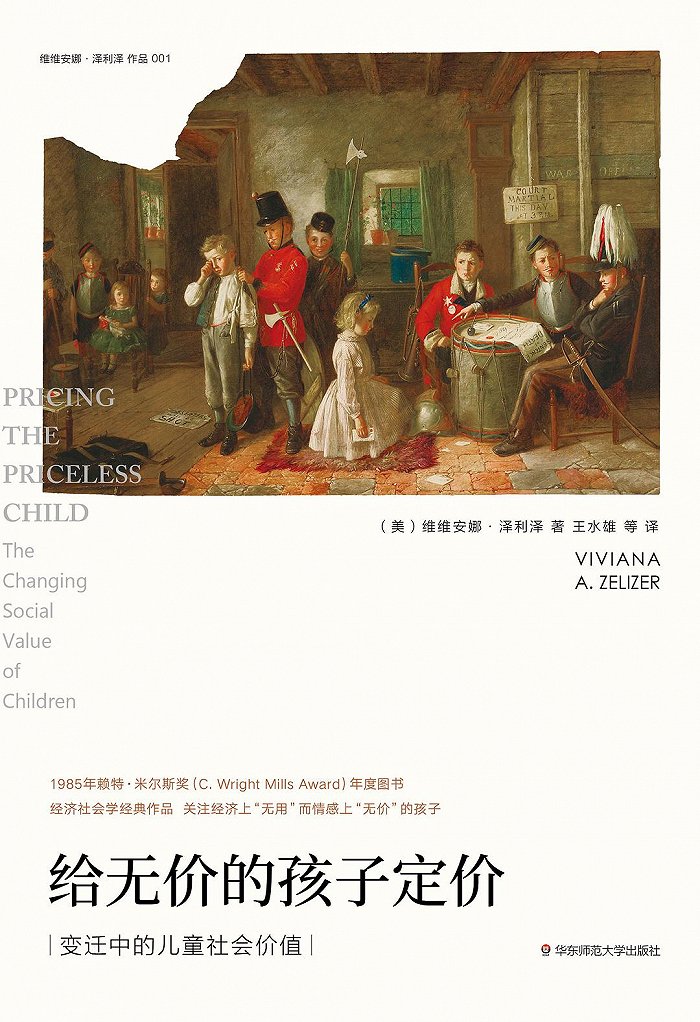
[美]维维安娜·泽利泽 著 王水雄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
对儿童的精细化养育要求也进一步加剧了性别不平等。在美国,“母爱至上”、“依附理论”、“童年决定论”等观念长期流行,日本占主流的观点是教育学者中内敏夫提出的以儿童和母亲为核心的“教育家族”。而在中国,母亲所承担的角色压力在近几十年里急剧增大。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教授金一虹指出,自1990年代起,中国掀起了“母教”潮流,宣扬好母亲应该勇于承担责任,为了孩子牺牲自我发展,这也让许多母亲在工作和育儿冲突时产生一种罪恶感,全职母亲的现象越来越多。苏州科技大学社会学副教授陶艳兰也分析了中国育儿杂志中的“母职”话语,她总结出这些话语建构的理想母亲形象:愿意花费高昂的教育经费、遵循育儿专家指导、一切以家庭和孩子为重等。安超在田野中观察到,如今,中国城市家庭中“严母、玩父、慈祖”代替了传统社会的“严父慈母”角色分工,母亲成为教育的总舵手和指挥者。安氏家族中有越来越多的母亲为了敦促孩子的学习,又不放心上一辈的教育方式,选择放弃自己的职业发展专门在家陪读。这也给了孩子巨大的心理压力,焦虑的母亲与疲惫的儿童共同构成了城市中产的教育困局。
教育焦虑中还充斥着大量“科学育儿”话语,例如“家庭教育要专业化”、“父母要培训上岗”。弗吉尼亚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莎朗·海斯(Sharon Hays)指出,科学育儿提倡的是一种以“儿童为中心、信赖专家指导、高情绪投入、劳力密集、高消费的育儿方式”。安超在对自己家族做田野调查的过程中也发现,城市新一代年轻父母往往不相信自然成就式养育,对于“专业机构”和“专业书籍”的热情非常高,家族中第一个女博士安德婧是科学育儿的代表,她花费了十万余元报了很多家庭教育班、父母课堂、家长学校等,还抽出自己几乎所有闲暇时间学习育儿知识。
然而,科学育儿并不总是正确,在界面文化此前关于中产育儿焦虑的采访中,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张聪指出,许多公共话语中的“育儿科学”其实更多是对某一理论的断章取义,学界本身就对如何正确育儿没有唯一的答案。兴起于西方国家中产家庭的科学育儿往往需要投入高时间与财力,给家庭造成了很大压力,安德婧在科学育儿的高标准之下,需要不断寻找心理医生来消解内心的焦虑和失落,同时她的孩子也感到不开心,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里,他始终觉得自己在学校的表现对不起母亲的付出。科学育儿的话语霸权也造成了对自然成就式养育和养育直觉的污名——完美妈妈适用于经济好的中上阶层,平民家长在科学育儿的话语之下变成不合格的家长,正常的妈妈沦为“失败的妈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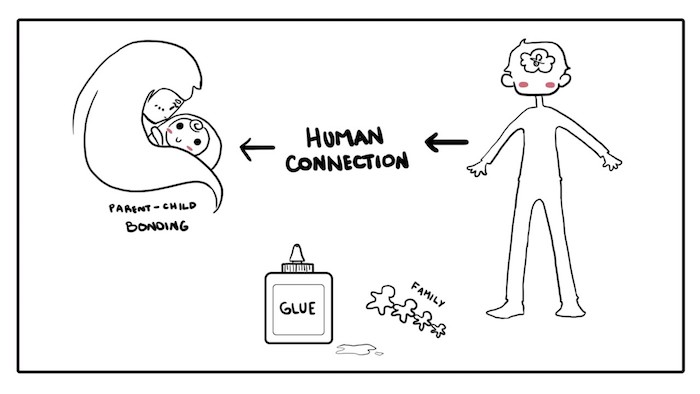
庶民教育里的“功德”、品行与同伴学习
在与安超的一场线上对谈中,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助理教授许晶认为,“现在大多数的育儿书籍都是强调核心家庭,以儿童为中心和本位。而实际上如果抛开我们熟悉的样式,去看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所谓‘科学育儿’背后是一套理性主义的权力和系统,如果参考人类学和民间教育学研究,全球不同文化里的民间育儿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作为通过读书升学进入大城市工作的乡下子弟,安超在自身家族教育史的田野调查里发现,从小受到的乡土社会庶民教育为自己留下了许多珍贵烙印,或可为如今城市教育症结提供新的可能。
和刻板印象里“小镇做题家” 、“读书改变命运”的功利性读书相悖,“回馈社会”经常在乡土民间社会作为劝勉读书的目的出现,这类具有公共性的读书目标已经很难在当下城市激烈的教育竞争里找到。在安超的观察里,庶民教育虽然在不同时期有程度不同的功利性,但也始终带有超越性和公共性。人们对学习的目的不仅是自利与物质的,老人认为孩子读书是为了“学好”,“好”是“走正道”、“对人有用”等,而非仅仅对自己的“实用”,“功德”在村里人的教育中是比“功名”更重要的事情。安超发现,这种“功德”意识在每代人身上都有所体现,村里出的读书人在经济独立后往往都会尽其所能为族人提供帮忙,完成经济回报和道德回馈。人们对读书怀着纯粹的精神向往,许多村民虽然没有机会读书,但会寻找一切机会搜罗有字的东西。没有上过学的老人也会一直保持将笔墨纸砚放在家中,写写画画。
与激烈的教育竞赛对“出人头地”的追求不同,安超注意到,庶民家庭里的孩子长大后不一定很有出息,但也很少会品行败坏,她归功于庶民教育中的“底线性教育”。底线性教育主要包括对勤劳、节制和体恤的强调,这些都是生计中重要的品质,比如“不劳作不得食”(勤劳)、“不眼馋、莫伸手”(自我节制),“报恩与回馈”。底线教育内化于日常的生活、礼仪、言教之中,不能保证孩子成年后可以出人头地,但也同时防止了他们坠入社会底层。出于生计考虑,民间还会强调自立性劳动,比如儿童自己料理生活、照顾自己的能力,强调公益性劳动,从小鼓励孩子获得劳动所得后回馈社会的重要性。
许多研究认为闲暇是贵族式教育的特点之一,同劳动相对立,而忙于生计的庶民阶层被视为少有闲暇和精神生活。但安超的田野调查发现,闲暇活动是庶民教育的重要部分,平民的闲暇往往和生计相结合。孩子们一边摘果子、割麦子,一边和同伴玩耍,虽然游戏常伴随着暴力和受伤,但儿童也在其中学会控制自己的攻击性,比如“打人不打脸”的规则,同时也在游戏里锻炼胆量、培养伙伴情谊。许晶在对谈中也提到,非洲采集部落的儿童很少单独玩耍,玩耍和生计、劳作往往结合在一起,童年的学习有传统上是非正式的,这些培养了孩子们很强的好奇心。在当下的中国,从研究到实践都非常强调亲子关系的教育,而相对忽略了同伴学习(Peer Learning)——在和同伴相处的过程中习得社会知识并培养自立能力——的重要性。

安超在《拉扯大的童年》一书中指出,平民生活中的世俗交谈(拉呱)也是闲暇生活的重要部分,老人下棋时,“人们一边东家长、李家短,这些话也全都落在孩子们耳朵里”,孩子也从中学到了成人世界的道德监督、审判、教化;村子里还常有流动的手艺人,到村里来干着剃头、补锅等活计时,孩子往往会围拢听他们谈村外新鲜的故事,丰富对世界的认知。在乡土社会里,儿童有很多参与公共闲暇活动的机会,比如集市庙会、节日祭祀。这些公共生活既与生计绑定,又充满人情味,让儿童学习到社会中的人情往来和买卖情谊,比如“买卖不成仁义在”、“聊着天临走时赛上两本菜,这次零钱没带下次再补上”。在红白喜事里,孩子也获得了最初的关于死亡、爱情和性的概念;丧葬仪式中“孩子们就跟在队伍后面看热闹,他们对‘死亡’懵懵懂懂,但并不恐惧,孩子们跟着大人完成整个仪式,可以慢慢消除对死亡的恐惧”。无论是通过同伴游戏获得非真实暴力的体验,还是与各式各样的人闲聊、参与公共生活,儿童都可以在这些活动中里习得日后的社会经验。相较之下,过度保护孩子、甚至将之与社会百态隔离开来的教养方式却可能适得其反,阻碍了儿童在社会参与中培养道德、开放心胸、发现同伴、与其他成年人相处并认识世界的可能。
城市育儿有可能超越原子化核心家庭吗?
安超观察到,城市养育行为越来越退守核心家庭,孩子也仿佛成为父母的私有财产。“管不得的宝贝疙瘩”说明家长对孩子的情感越来越私人化的同时,对他人的孩子也越来越缺乏公共之爱。安德婧的孩子在自述中提及,“我的母亲常说,妈妈为什么偏偏管你而不去管街上的路人呢?因为他们和我没有关系,我只关注我自己的孩子。这样的话表达了妈妈对我独一无二的关爱。”当大人斩断同公共社会的联系,这种“独一无二”的爱将孩子和家长都禁锢在狭小的空间里,既限制了父母与儿童的发展,也使得家庭内部承担着巨大的养育压力。泽利泽也指出了现代社会中儿童的神圣化现象,成人在资本世界中遭受冷漠的商业文化和异化的劳动后,将全部情感与心灵依赖转向孩子,儿童成为如同宗教的神圣性存在,家庭成为现代风险社会中的避风港,而不再是个体通往广阔世界的桥梁。
实际上,从人类历史来看,以原子化核心家庭为中心的养育模式是非常晚近的产物。农耕时期,中国平民的养育模式是亲缘共养,一个家庭的育儿既依靠家族支持和女性合作,也有同村人互相的关照,比如一家孩子缺奶时可以让另一家妈妈帮喂奶,比如一些条件困难的孩子“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紧密的熟人社会与亲人纽带诚然可能导致很多问题,比如生活私密性难以维持、个人边界被侵犯等。但这种互助共养模式无疑也有可取之处,既能减轻家长尤其是母亲的巨大压力,又得以不将养育局限于冲突剧烈的两代人之间。
如何使对儿童的爱超越私人家庭的边界,把儿童和成人重新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引向公共生活?许多地方正在努力尝试超越核心家庭的互助育儿模式。“四环游戏小组”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师生在北京四环农贸市场发起的互助组织,农贸市场的外来摊贩面临孩子在北京“入园难”问题,他们自身也因菜场工作繁忙无暇看护和陪伴幼儿。北师大的师生们借鉴了20世纪六十年代英国的“社区家庭自助育儿”,组织摊贩家长互助轮岗,组织读书会、出游、玩具制作,为菜场的孩子们提供基本的学前教育和社交环境,如今,游戏小组已经从大学生主导变成了摊贩间的自发互助,数百个流动儿童通过这样的方式得到了基本的学前教育。“双减”政策之后,上海五角场街道也出现了社区互助育儿组织。在假期里,要工作的父母既不愿意让孩子独自在家,也不想把教育全权托付给市场上昂贵的补习班。于是,家长们自发依靠专长组织课程,轮流讲课陪伴邻近的孩子们。“我的孩子”变成了“我们的孩子”,家庭养育变成了小范围的公共生活,互助组织也创造出超越核心家庭的多元复杂的社群连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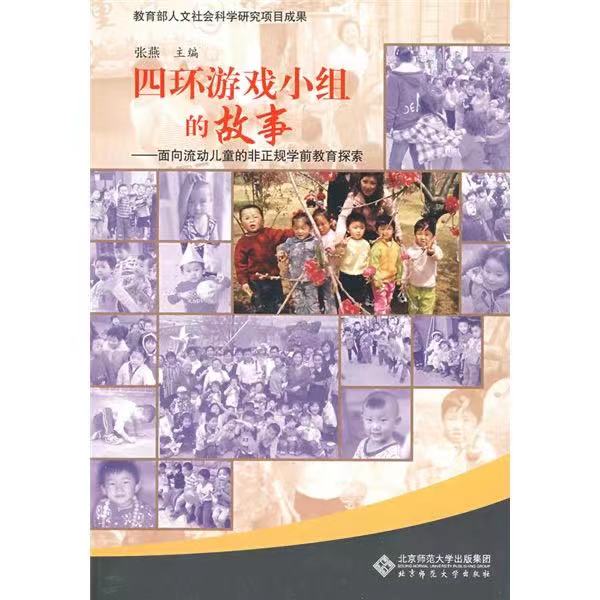
张燕 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年
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学院副教授李洁在《重新发现儿童|“鸡娃”背后:从“外包”课外生活到社区互助育儿》一文中说,“从历史的长度来看,养儿育女完全落到家庭只是近来的事,抚育带有公共属性,且不仅仅局限于对于儿童和家人的照顾,还包括营造社会共同体,维系共享的意义纽带、情感和价值等其它不同性质的劳动。”安超认为,当今的城市家庭可以借鉴庶民教育的共养经验,建立具备边界感的互助养育共同体,让教育超越私有制家庭。政府也应建立适合人际互动的公共场所,比如社区花园和城市公园这类更自由的、非组织化的人群交流场所,而不是让城市被商业中心的房地产绿地占领。同时社会也应对边缘的、由人们自发所形成的教育尝试更加宽容,让父母和孩子有机会从单一的教育想象中解放出来。
参考文献:
群学书院 安超《拉扯大的孩子》沙龙讨论纪要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3899996/
维维安娜·泽利泽 .《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变迁中的儿童社会价值》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科学育儿”可以纾解城市中产的育儿焦虑吗?》, 界面文化/article/2189905.html
《重新发现儿童|“鸡娃”背后:从“外包”课外生活到社区互助育儿》,澎湃思想市场https://mp.weixin.qq.com/s/TTdpVAnPDjeTl4k5J7sBww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