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编辑 | 黄月
流调,全称为流行病学调查。“流调信息”一般包含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简单的勾勒,虽然没有起承转合的情节,但已能够勾勒出一个人的基本生活样貌。2021年沈阳新冠疫情期间的一次流调为我们呈现了一位爱吃鸡架的大爷的生活,他每天下两次馆子,吃的是鸡架、炖肉和抻面,有网友调侃他把流调记录变成了沈阳美食攻略。无独有偶,广州一位75岁阿婆的流调也涉及多家酒家、餐厅和茶点轩,不是在饮茶就是在去饮茶的路上,网友纷纷评论“太粤了”。
也有一些流调让我们意识到生活的艰辛,比如去年一名34岁海淀爸爸的流调关键词是“中年、考研、蜗居、通勤3小时、带娃、出差”。流调虽然只记录了一个人几天内的动向,却好像成为了其个体人生的切片标本,被放在舆论的放大镜下反复观看、讨论和分析。在新冠大流行的年代,流调成为了一份独特、显形且不能忽视的文本。当我们在讨论流调的时候,我们关心的究竟是什么?

在注意力有限时代看见他者
互联网不仅是多种技术的综合体,也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媒介,我们的注意力被无数的信息争夺。在《顿悟的时刻》一书里,作家张悦然认为,社会新闻里充斥着人间悲剧。“人类悲悯的天性使我们能够去同情所有受苦的人。但是我们不是神,我们的同情不能均分,我们总是同情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多。”人们会把自己的感情放在一部分人的身上,而没有选择另一部分,这是为什么?她认为,可能由于境遇相似,也可能是因为他们身上揭示的情感正是我们的情感暗面。
人们倾向于把感情寄托在那些让我们联想到自己处境的人身上,弗洛伊德将这种倾向称为“细微差异的自我迷恋”。在社科领域,人们可能会用身份政治来解释这个问题。在《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可的渴求》一书里,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身份政治的存在源于社会对个人尊严的忽视,诸多群体感到自己的身份没有得到足够的认可与尊重,但身份政治的兴起也导致了具有差异的群体和群体之间的诉求逐渐缺少公约数,因此福山觉得这是一条让社会变得更加碎片化的不归路。

然而,因为病毒,情况发生了变化。在《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一书中,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民安从SARS的经历中看到,虽然传染病让人们的身体彼此隔离,但是这种空间隔离却让人们前所未有的相互连接。“单个原子般的身体惊人地织成了一种同质感,”一个紧张的焦点将人们紧紧统摄在一起。

汪民安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 2022-1-1
在这种情况下,流调的信息重要性倍增。信息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产生巨大的防治效益,也是最为经济的防疫手段。汪民安认为:
“信息在抵达个体的同时还造就和决定了个体,它使个体产生实际的防治和自我诊断行为,信息的这种威力同防治性的政府权力、医学救治权力相比毫不逊色。这三者成为‘防疫工程的三位一体’。”
在人人都想获得流调信息以了解情况、判断风险的时候,陌生人的生活也变得和我们息息相关。病毒不仅打破了民族国家界限,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种族与性别的区分,让不同阶层的人士都感受到了公共卫生的不稳定性。在这种情况下,遥远且陌生的个体患病及隔离经验也成为了更多人的普遍关切,既是判断自身感染风险的一种渠道,也反映了某种“同呼吸,共命运”的感受。我们不得不把注意力投向了平时关注范围之外的个体,无论阶层、民族与性别,流调为我们了解他人、了解不同的生存境遇提供了机会。
是窥视别人也是发现城市
今天都市的特征是邂逅、碎片式经历和疏离感,血缘和地缘关系被陌生人的关系取代。陌生人社会既让我们获得自由和释放个性的机会,也造成了更多隔绝与孤独——我们自己的生存经验有限,视野中的生活形态也不够丰富。在城市化与互联网双重力量筑起的孤独社会里,加拿大社会评论家哈尔·涅兹维奇认为今天的流行文化(pop culture)实际上正是一种“偷窥文化”(peep culture)。一部分人喜欢在网络上展示自己生活的细节,其他人则以观看这些内容为乐趣;有的人喜欢窥视,有的人喜欢被窥视。参与真人秀、直播生活、发布微博等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暴露自己,以此维持“自我”,而观看直播、真人秀、浏览他人的社交网络动态则满足了另一部人“偷窥”的欲望,这是我们时代的社会集体偷窥。

对他人怀有强烈好奇心可以说是人之本能。弗洛伊德把人的好奇心和“窥视”欲望当作性本能的一种,受力比多驱动。拉康也有“想象的凝视”一说,他看到,自我理想是以他者目光看自己时得以凝定的形象。“自我”不是用自己的目光看世界,而是用外部的眼光看自己,自我的本质就是他人,“我只能从某一点去看,但在我的存在中,我却在四面八方被看。”所以,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谁都难说自己没有窥视的潜意识存在。
阅读流调并非简单地窥视他人的生活,也为我们彰显了看到更多生活面向和城市肌理的可能性。如汪民安所言,虽然说我们都生活在现代城市里,其实人们只能固定地在工厂、学校、商场、住宅这几个地点穿梭,“城市空间看上去是开阔的,无限延伸的,充满着机会和富于秘密的,但是群众无可奈何地只能在烟囱、厂房和住宅确立的坐标中自我定位。尽管他们置身于城市,但他们对城市的秘密一无所知。”流调里的人去过我们熟悉的地方,也把脚步印在那些我们从未抵达之处,我们去往的场所是固定而受限的、是出于有限的需求与视野的,是被身份和关系划定的,却在流调中经由他人生活工作的地点窥探到了一座城市的丰富性和巨大秘密。

本雅明曾借用巴黎诗人波德莱尔创造出“都市漫游者”的形象,这种漫游者是都市文明的产物。地理学家、思想家大卫·哈维在《巴黎城记: 现代性之都的诞生》里谈到,这样的都市漫游者“是一个立志于揭开城市和社会关系谜团的人”。流调中在不同地点之间辗转生活的新冠“中枪”者们,也仿佛都市漫游者一般带领着我们开启了一个又一个场景。
场景中是不加粉饰的生活
虽然流调的本意只是传染病防控,找出“时空轨迹交集”,但是阅读流调为大众提供的信息远不止于此。
在著作《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中,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把个体和群体在他人面前努力产生并维护理想印象的过程比作一种戏剧表演。他看到,人性化的自我可能只是被反复无常的情绪和变幻莫测的精力驱使的动物,可是作为一个社会角色,在观众面前表演时却必须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按照这种理论,社会就是剧院,个体进行表演,以引导和控制他人对自己的印象——用时下流行的词语来说,就是“印象管理”。不过,流调不允许我们通过日常表演来美化和彰显自己的形象,呈现出某种恰如其分的表演。即便有表演的欲望,我们也不知道何时何地的生活内容会进入流调,不知道自己需要在何时何地如何进行表演。一方面,病毒的紧急性、残酷性压制了表演,另一方面,无人能够预知和防备非表演状态下的自己进入流调。

与此相比,流调提供的是一种不加粉饰的零度写作,这里只有时间、空间和你自己。无怪乎一些网友已经开始担忧如果自己感染了新冠,流调写出来会是怎么样——“要是公布流调,我的行程也太辛酸了”,“为了不公布流调我会好好注意的”……
流调中的场景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叙事,一个人的途经之地和对应行为叠加,仿佛一个因有待补齐而更引人遐想的剧本。“场景所在的地方是能够表达你感觉到的氛围、情感、情绪,以及你认同的气氛的区域。”在《场景 : 空间品质如何塑造社会生活》一书中,作者多伦多大学社会学副教授丹尼尔·亚伦·西尔和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特里·尼科尔斯·克拉克这样写道。场景让人们产生共鸣,可以从场景的叠加中辨认出一个陌生人的工作和家庭情况、消费能力甚至饮食偏好和业余爱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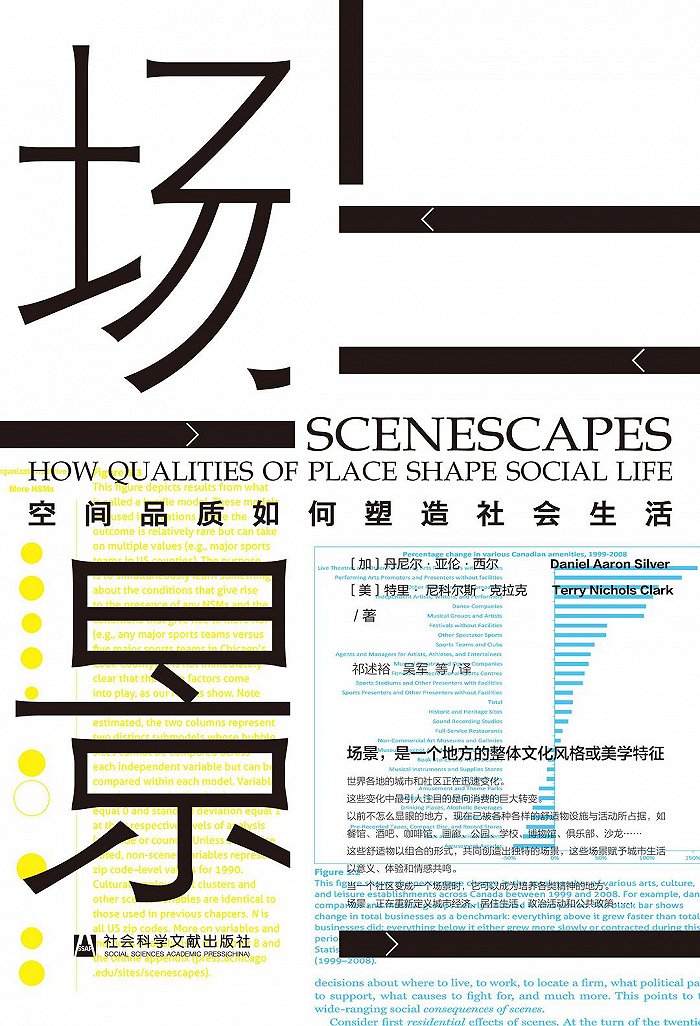
【加】丹尼尔·亚伦·西尔 / 【美】特里·尼科尔斯·克拉克 祁述裕 吴军 译
方寸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1
所有的公共空间都并不仅仅是空间而已,流调里的每个人都进入过不止一个场景,这些所有空间彼此相关,每个场景都“说”了很多,有相似之处,也是前后连贯的、不断叠加的、互相补充的。我们去过的场景彼此相连,勾勒出我们真实的生存状态,“我到底是谁”的答案因此呼之欲出。
参考资料:
《顿悟的时刻》张悦然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0
《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汪民安 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 2022-1-1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欧文·戈夫曼 著 冯钢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5-16
《场景:空间品质如何塑造社会生活》【加】丹尼尔·亚伦·西尔【美】特里·尼科尔斯·克拉克 祁述裕 吴军 译 方寸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1
漫展上的制服与偷窥:是女生有伤风化,还是男性偷拍有错?https://m.jiemian.com/article/4757691.html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