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编辑 | 黄月
公元前300年,托勒密一世在亚历山大城建立了一座大图书馆,野心勃勃的埃及国王企图将世界上所有的书尽数收进这座图书馆。从那时起,图书收藏者和图书管理员就一直沿袭这个梦想,它也成为了现代版本图书馆的核心理念——现代版本图书馆有权获得在本国出版的每一本书。
图书馆不仅是书籍的汇聚之所,也是思想的汇聚之所。几乎从图书馆诞生伊始,谁有权利进入图书馆、哪些书能够在图书馆保留下来就成为事关图书馆存亡的重要问题。不同的时代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其决定因素包括战争动乱、政治博弈、信仰分歧、翻译失误、保存不当、知识迭代等等,就这样,图书馆的历史也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交织在了一起。在这个世界读书日,界面文化(ID: Booksandfun)挑选了五本图书馆主题书籍,与各位读者分享这一世界上最古老的公共场所的内部运作机制,以及它罕为人知的动人往事。
《巴黎图书馆》

[美]珍妮特·斯凯斯琳·查尔斯 著 张文跃 译
光尘·中信出版社 2021-10
用一句话概括《巴黎图书馆》:这是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长篇小说,讲述的是一群勇敢的图书管理员,在二战期间和战后的巴黎,如何在纳粹的重重限制、监视和匿名举报下坚持运营一家图书馆的故事。2010年,美国作家珍妮特·斯凯斯林·查尔斯在巴黎亚美利加图书馆担任项目经理,结识了两位对这座图书馆历史了若指掌的同事,从他们那里得知了这座图书馆在二战期间如何坚持维持开放,为前线士兵和不被允许进馆的犹太读者送书的往事。查尔斯被这个充满了勇气、坚韧和泪水的故事深深打动,她花了数年时间研究图书馆档案、采访当事人,创作了这部作品。在作者手记的最后一段话里,她点明了这部小说的意义:
“一位朋友说,在阅读以二战为背景的故事时人们会扪心自问,如果重新回到那个时代,你会怎么做。我认为一个更好的问题是,把视角移到现在,问问自己现在能做些什么,让每个人都能去图书馆,都拥有学习的权利。我们还要问自己,该怎样给人们尊严,该怎样保持自己的怜悯之心。”

由于本书的主角之一是一位图书管理员,我们得以通过她的视角了解到图书馆内部运作的一些行业知识,比如图书馆藏书的编码是根据杜威十进制图书分类法得出的——这一分类系统由美国图书馆专家杜威在1873年创立,用十个类别,根据不同主题归纳整理图书馆藏书。所有事物都能从这一分类系统中找到对应的数字,比如“636.8”是“猫”、“636.7”是“狗”。与此同时,作者也借图书馆工作者之口道出了一些对图书馆和阅读意义最深情的叙述,比如这句: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肺脏,书籍就是人们呼吸的新鲜空气。它让我们的心脏持续跳动,让我们的头脑充满想象,让我们永葆希望之光。有了这座图书馆,读者才能了解外面的信息,才能聚在一起从社群中汲取力量。”
《亲爱的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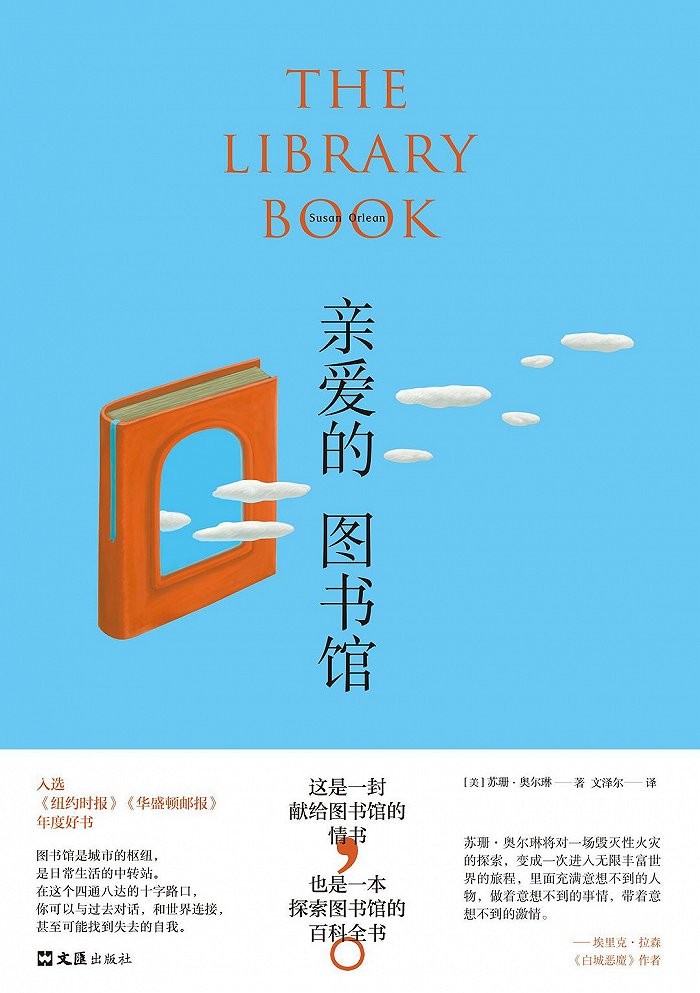
[美]苏珊·奥尔琳 著 文泽尔 译
新经典文化 | 文汇出版社 2021-5
在这部纪实作品中,故事从1986年洛杉矶中央图书馆的一起纵火悬案展开:1986年4月29日太平洋时区上午10点左右,该图书馆突然起火,大火连续烧了七个小时,火势之大让洛杉矶全市消防员倾巢而出。一共有40万册图书在大火中被烧毁,另外还有70万册图书被烟或水严重损坏,这是美国历史上损失最大的公共图书馆事故。
纵火人是谁?洛杉矶中央图书馆对当地居民来说具有怎样的意义?作者苏珊·奥尔琳铺陈了三条线索——洛杉矶城市史、图书馆的历史和嫌犯的个人史——每一条都引人入胜,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亦令人动容,比如美国公共图书馆系统的完善还见证了美国女性主义的发展,嫌犯的最终命运和80年代艾滋病在洛杉矶的爆发息息相关。
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深入图书馆平静表面后的庞大复杂体系,了解到优质的公共图书馆能如何提升市民的文化生活。得益于管理人员的远见和努力,洛杉矶公共图书馆系统早在1933年就已经是全美流通书籍数量最多的图书馆,当时洛杉矶是美国第五大城市。图书馆的咨询服务从1930年代起就成为最受读者欢迎的服务项目,他们向馆员提出的问题千奇百怪(比如“罗密欧具体长什么样”、“1929年美国的产奶总量”或“眼睛虹膜上是否能感知不朽”),在一个没有谷歌的时代,图书馆咨询台或许是人们在学校之外能依赖的最重要信息窗口。公共图书馆的作用还不止于出借藏书和回答读者问题,它还是无家可归者的社区中心,这里允许他们使用电脑和网络、阅读和闲逛,除非他们有任何过分的举止。
而在不远的未来,图书馆或许将成为信息与知识的交换中心。作者援引美国的数据指出,虽然图书馆堪称历史最悠久、最老派的公共场所之一,但它在30岁以下的人群中却越来越受欢迎。尽管年轻人是在一个充斥着网络信息和电子书的时代长大的,但约2/3的年轻人认为,图书馆里有些重要资料是互联网上找不到的,而且图书馆为习惯远程办公的年轻人提供了最早出现且完全免费的共享办公空间。
《亲爱的图书馆》会是一部阅读爱好者都会喜欢的作品,因为作者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对书籍的热爱能引起所有爱书之人的共鸣,“世界上所有的谬误,似乎都被图书馆那简单到不言而喻的承诺所征服:这是我的故事,请对我说;我在这里,请告诉我你的故事。”
《廷巴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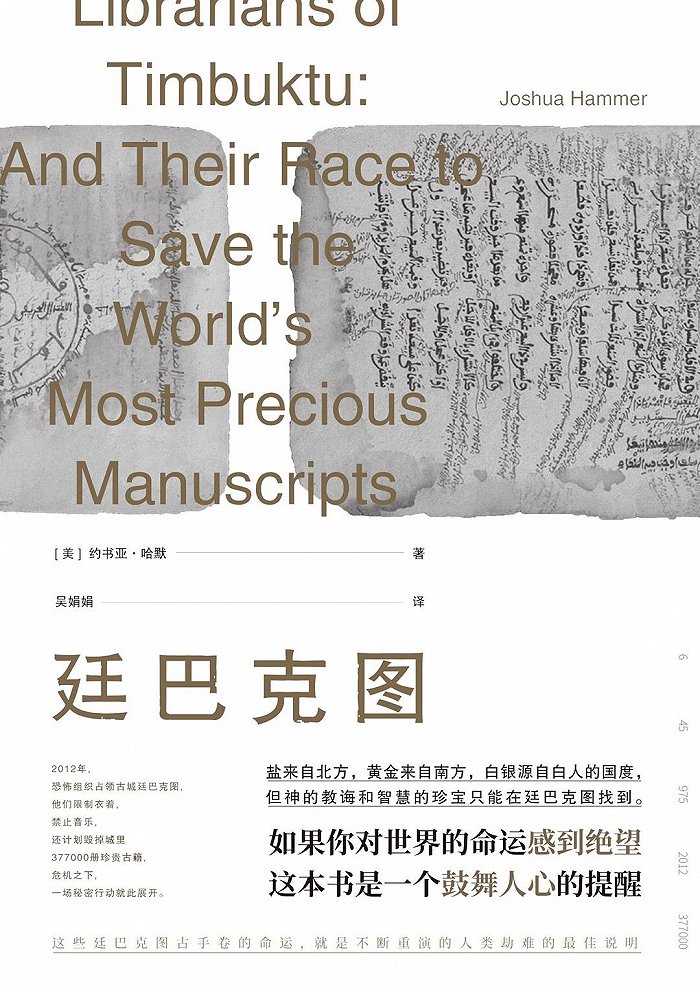
[美]约书亚·哈默 著 吴娟娟 译
新经典文化 | 文汇出版社 2020-1
廷巴克图(Timbuktu)始建于公元11世纪,是西非马里历史最悠久的古城,现通行的名称为通布图(Tombouctou)。中世纪最伟大的伊斯兰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14世纪上半叶就到访过廷巴克图,16世纪,另一位伊斯兰旅行家哈桑·穆罕默德·瓦赞·扎亚提也在自己的游记中提及廷巴克图。他们都注意到了以廷巴克图为中心的盛极一时的手稿创作与书籍收藏文化——当欧洲仍在黑暗的中世纪时,知识与理性的火苗就已在撒哈拉以南的地区熊熊燃起。1591年,摩洛哥征服廷巴克图,手稿创作与书籍收藏的文化被迫转为地下活动,但18世纪时又得以兴盛繁荣,只是在法国长达70年的殖民统治下再次销声匿迹。
1964年,即马里脱离法国殖民统治的第四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在廷巴克图建立一个收藏中心兼研究院,恢复该地区宝贵的文化遗产,并向世人证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亦曾是重要的知识中心。教科文组织委任德高望重的当地知识分子满玛·海达拉主持研究工作,之后他的孙子阿卜杜勒·卡迪尔·海达拉继承了这一使命,收集和研究散落各处的珍贵手稿。
焚毁书籍、破坏收藏机构是所有战争手段中最具有象征意义的:它消灭的不是人的肉体,而是人的精神以及文化存续。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廷巴克图对书籍破坏和文脉中断并不陌生——伊斯兰文化向来具有两股针锋相对的意识形态,一股开放包容,另一股僵化暴力。2012年,廷巴克图再一次面临威胁。“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占领了马里北部地区,宣誓要对任何挑战“纯粹伊斯兰社会”愿景的人与物发起圣战,其中就包括廷巴克图收藏的精美手稿(内容包括逻辑学、占星学、医学、音乐与诗歌)。
为了拯救这批珍贵的古手稿收藏免遭“圣战分子”的破坏,海达拉再次踏上冒险之旅,穿越马里的沙漠,将它们从恐怖组织的眼皮子地下偷运出廷巴克图,成功拯救了这批价值连城的文物。书中对这段经历的描述堪称惊心动魄。这个真实事件亦在提醒我们,尽管狭隘、不宽容和思想镇压总在历史的阴暗处伺机而动,但人类对文明、理性和自由的追求是永远无法磨灭的。
《火种:人类文明的最初成果如何在七个城市之间传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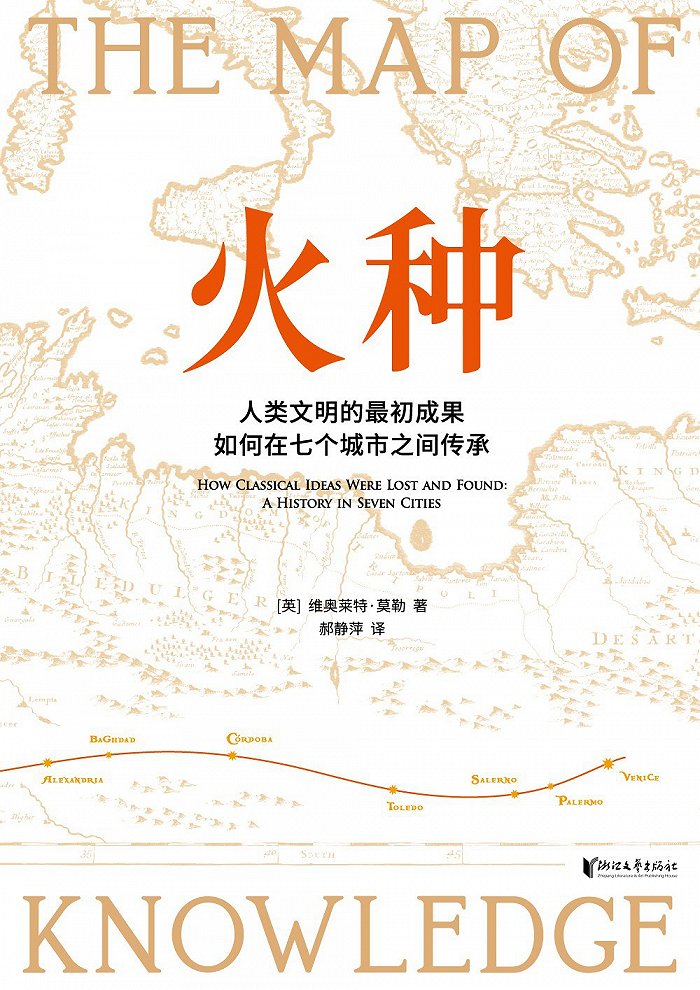
[英]维奥莱特·莫勒 著 郝静萍 译
果麦文化 |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1-1
在本书中,作者维奥莱特·莫勒关注西方科学史中的三部巨作——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以及古罗马名医盖伦的医学作品集——是如何跨越时间长河流传到今日的。在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知识接力中,七座城市(亚历山大城、巴格达、科尔多瓦、托莱多、萨勒诺、巴勒莫、威尼斯)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些城市几十代人的抄写、翻译、传播、接力下,创作于遥远古代的作品从战乱、政治博弈、信仰分歧、翻译失误、保存不当造成的重重困难中存活到了印刷术发明的时代,从此发扬光大,推动了现代科学的诞生。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科学的发展离不开伊斯兰文明的贡献,阿拔斯王朝早期的三位哈里发对此厥功至伟:阿拔斯王朝的第二位统治者曼苏尔(al-Mansur,714-775年)定都巴格达,鼓励和资助学术研究(该城处于水路和陆路贸易网络中心的优越地理位置毫无疑问也有助于跨文化交流);他的孙子哈伦·拉希德(Harun al-Rashid,763-809年)同样也是学术研究的热情支持者;哈伦的儿子马蒙(al-Ma’mun,786-833年)则是所有阿拔斯王朝的统治者中对科学兴趣最浓厚的哈里发,他重建了父亲的智慧宫,推动巴格达成为当时最重要的知识中心,智慧宫图书馆到9世纪中叶已是世界上藏书量最大的图书馆。
那是伊斯兰文明的黄金时代。宗教教义还未给穆斯林的思想套上保守排外的枷锁,相反,科学与信仰和谐发展,“对宗教真理的追求不仅促进了在广泛的哲学层面的理性探寻,而且要求回应具体的实际的需求。”知识从四面八方以各种语言流入巴格达,而巴格达人来者不拒,即使是那些遭遇拜占庭当局迫害的异端基督徒,亦能在这座城市里继续教授和研究希腊神学、哲学、医学和天文学。曼苏尔曾亲自写信给拜占庭皇帝,请求对方提供书籍。拜占庭立刻送来了一箱科学书籍,其中就包括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学者们将其翻译成阿拉伯语,并进一步拓展了数学研究。莫勒指出,中世纪阿拉伯科学广泛涉猎天文学、占星学、哲学、数学和地理学,在她看来,这些古巴格达学者在文艺复兴几个世纪前就预示了它的到来。
《消失的图书馆》

叶锦鸿 著
启真馆·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1-12
在《消失的图书馆》中,作者叶锦鸿介绍了多座湮没在历史中的图书馆,其中包括二战期间被焚毁的商务印书馆旗下东方图书馆,这也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史上的一个大灾难。1897年,商务印书馆创办于上海,早年出版图书质量不佳销路有限,陷入亏本经营的境地。为了提高图书出版质量,为编辑提供图书资料,商务印书馆于1904年设立编译所图书资料室,开始广泛收集国内藏家散出的古籍善本,以及日本、欧美各国新书。1909年,图书资料室被命名为“涵芬楼”,取“善本书香,知识芬芳”之意,同年,商务印书馆成立专门的图书馆部门,并聘请版本目录学大师缪荃孙的弟子孙毓修管理。由于收藏丰富,且为编辑人员提供了良好的阅读学习环境,“涵芬楼”名扬当时的中国出版界。1916年,茅盾进入商务印书馆,他的理由是:“在此不为利不为名,只贪图涵芬楼藏书丰富,中外古今齐全,借此可读点书而已。”
1922年,商务印书馆成立图书馆委员会,以14万元购入出版社大楼马路对面的空地,建造了一座五层高的西洋式建筑,定名东方图书馆。1924年,位于宝山路的东方图书馆建成,是当时上海华界最高的建筑,也是当时上海的重要文化地标。至1926年5月2日东方图书馆正式对社会公众开放,馆藏已颇具规模,包括古籍4万册、地方志2641种(共2.5万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全套“本版图书”、15世纪以前的西洋古籍以及多套完整的中外期刊等。
1932年1月29日上午,日军轰炸机突袭上海,向商务印书馆所在区域连续投弹,将印刷厂、编译所、东方图书馆等设施全数炸毁,曾享有“亚洲第一图书馆”美誉的东方图书馆毁于一旦。叶锦泓指出,“一·二八”事变期间,日军锁定了上海的四个轰炸目标,除了上海自来水厂、上海发电厂和中国银行以外,就是作为“中国文化大本营”的商务印书馆。日本海军将领盐泽幸一曾表示,“炸毁闸北几条街都不打紧,不出多长时间他们就会重建,只有炸毁了商务印书馆,他们才会万劫不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日军轰炸商务印书馆和轰炸其他地方不一样,使用的是燃烧弹,轰炸次日还有日本人拿着火把来继续焚烧,有记载称纸灰在上海上空飘落数日不散。
1941年12月8日,日军占领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第二日就又对商务印书馆等五家书局进行地毯式搜查,凡是出现“苏联”“日本”“国难”等词语的书籍,无论具体内容为何,一律抄没。商务印书馆再遭重创,多达462万册图书被日本当局没收。1953年,商务印书馆将涵芬楼仅存的“烬余”善本和东方图书馆藏书全部捐献给了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后来这批图书被收藏于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