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编辑 | 黄月
两次世界大战、纳粹独裁、大屠杀、柏林墙建起而后倒塌……20世纪初出生的一代的德国人,生来被抛于历史漩涡的中心,他们在玫瑰色滤镜里回忆第二帝国与魏玛共和国,在纳粹控制的教育体系中度过青春期,并随之卷入了残酷的二战。柏林墙横贯于他们的中老年岁月,西德的公民全身心维系私人生活,东德的居民则继续在萧条经济与极权统治里挣扎。
在这一代德国人中,有作家君特·格拉斯、思想家哈贝马斯和卢曼,也有美国历史学家康拉德·雅劳施(Konrad H. Jarausch)在《破碎的生活:普通德国人经历的20世纪》里记录的七十多个普通人,他们是教师、医生、士兵、农民,在相信“历史终结”的暮年里写下自己的一生,“时间像狂野而汹涌的海浪一样扫过我们,摧毁了一切。”雅各比娜·维托拉在回忆往昔时写,她战时因躲避东部入侵的苏联红军西逃,那一场大逃亡中,约有100万德国平民丧生。
普通德国人如何在当年被卷入纳粹暴行,又是如何在铁幕倒塌后书写自己的经历的?《破碎的生活》中文版出版之际,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通过邮件采访了作者康拉德·H·雅劳施,他认为,通过研究被大历史图景掩盖的民间记忆与个体叙述,我们可以看到,普通人如何既是政治压迫的受害者,又是独裁统治和战争的附庸。他也提到了第三帝国对年轻人的教育灌输、纳粹的厌女体制与高女性支持率,西德公民早期遁入的政治冷感。雅劳施认为,了解德国人的苦难不意味着为二战开脱,只有找到德国苦难与罪行之间的联系,才是正视过去的关键,而这些普通人的回忆正展现了私人生活是如何同邪恶体制共谋,又如何最终被其反噬与倾轧的。

从学校教育到青年团:纳粹如何改造青年?
雅劳施在《破碎的生活》中发现,青年人更容易卷入国家社会主义的宣传中,纳粹党一直把德国青少年作为宣传的重点对象,希特勒认为,“谁拥有青年人,谁就拥有未来。”人们察觉到纳粹执政后学校课程内容的变化,赫尔曼·德布斯在回忆录中写:“元首、民族和祖国等概念每天都被呈现在我们面前,”以便确认“希特勒及其支持者永不犯错的形象”。席尔默回忆道:“历史课变得党派化,几乎不知不觉地引入了纳粹意识形态。”学校里支持纳粹却没有能力的员工被提拔为校长,一些持有异议的老师遭到监视和审查,甚至被解雇。也有些老师会偷偷向学生传递自己的理念,比如黑尔默的自传提到,高中老师会“中立但有趣地提供官方版本之外的其他视角”,引导学生思考,还有人不遵从官方要求的“希特勒万岁”问好方式,而用“日安”代替。然而,绝大部分老师都不会公然反对纳粹意识形态。在晚年,这一代人普遍认为,“学校的教育并没有提供任何区分人道和不人道行为的标准。”

与此同时,“希特勒青年团” 与“德国少女联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青年加入。青年团成员会一起参加露营、徒步等团体活动,特尔记得,徒步穿越祖国的不同地区和在篝火旁唱歌,创造了“一种与我们民族早已逝去的老一辈人真正交融的感觉”,莫斯曼喜欢团队中“爱国朗诵、唱民歌和行军的乐趣”。青年团将年轻人神化为“德国未来的保证者”,比如彼得斯回忆,加入少女联盟让她从家庭与学校独立了出来,她对自己肩负的使命——“建设将持续千年的崭新的第三帝国,并承担责任”——感到振奋。 没有一个魏玛青年“知道或可能知道战争意味着什么”,在学校和希特勒青年团的思想灌输中,曾经残酷的一战被描绘成了英勇的斗争。还有一些年轻人遁入非政治性的追求中,只要当局不打扰他们的私人生活,他们就愿意服从纳粹的意识形态要求。
人们的回忆录中还记下了同上一辈的政见冲突,父辈往往对纳粹政权抱持更警惕的态度,赫尔穆特·拉什多夫回忆,他并没有意识到纳粹党的问题,但他的父亲预言:“希特勒掌权后会有战争。”本诺·舍夫斯基回忆道,在收到阿姨送的青年团制服时,“我妈妈对此非常愤怒,把这些东西藏进了箱子”,他的父母只允许他最低限度地参与青年团的活动。汉斯·席尔默禁止自己的儿子去希特勒青年团,但他的儿子并不能理解:“其他男孩也穿着这些衣服,却没有任何问题。”霍斯特的母亲对纳粹颇为不安,但他认为:“纳粹掌权是好事。他们帮助德国恢复了其应有的伟大。他们是我的国家的领导者。”当霍斯特听说一位朋友和父亲被关进了集中营时,他说:“他们是帝国的敌人,必须使其变得无害。”全面控制的教育灌输让越来越多年轻人对纳粹深信不疑,一切正如希特勒在1933年所预言的那样:“当一个反对者说,‘我不会站到你那一边的,’我平静地说,‘你的孩子已经属于我们了……你会死去的。但你的后代现在站在一个新的阵营里。不久之后他们除了这个新组织之外什么也不会知道。’”
残酷战时:被杀害的男性与被侮辱的女性
雅劳施发现,二战经历“构成了大多数人生活描述的中心”,战争对男性与女性的意义截然不同。如果总结人们在自传中提到的战争事件,对男性是“服兵役”、“中断他们的事业和浪漫关系”以及“爱国意义的战火的考验”;而对女性来说,回忆大多关乎“家庭、亲人和朋友”,在战争时期,女性更关注自己家庭的基本生存情况,政治很少出现,通常被视作外来的入侵。
男性主动参军服役一方面受到同龄人压力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被看作男子气概的证明——他们“不想落后于无数同龄人,特别是那些认识和交好的人”。罗伯特·诺伊迈尔担心:“在这场战争结束后,我会被称为‘开小差的’,人们会指着我说‘那是个懦夫’。”这一时期 ,一种凶残的“尚武男性”形象被发明宣传,取代了平民版的男子气概。

随着战事升级,军队逐渐丧失人性。罗伯特·诺伊迈尔描述,当一个受伤的俄国俘虏走在他坦克前面时,“他被履带绊了一下,被卷到底下压扁。 我们从他身上碾过,这让我恶心。”除了战死的士兵,越来越多的平民被杀害,残酷的无差别杀戮以报复敌人的名义被合理化,赫尔穆特·拉什多夫回忆 :“我旁边的一位同伴举起枪,向一群平民开火。”他的同伴认为:“这有什么,他们只是俄国人。”有士兵写道,他看到两具护士的尸体,“她们被割掉了乳房,生殖器也被破坏。”而作为报复,他的部队“包围了一个村庄,开始用曳光弹和燃烧弹射击”。村子里的老人、女人、孩子都跑了出来,“我们将他们成批扫倒在地,直到再也没有人动弹。”
很多研究都忽略了二战时期的女性叙事,或认为女性只是第三帝国的受害者。雅劳施反对这类观点,他指出:“妇女在纳粹独裁统治中发挥了积极得多的作用。虽然在纳粹成员中比例偏低,但她们为该党提供了几乎一半的选票。”对希特勒的崇拜不仅关乎领袖伟人式的追随,还带有情欲的成分,“许多女性的书写都流露出对一个同是父亲、情人和救世主的希特勒的狂热追捧。”罗瑞·瓦尔布如此回忆见到希特勒的一刻:“他站在车里,举着右臂,他是如此严肃,如此强壮,如此伟大……这是我14岁生命中最美丽、最感人、最有力量的时刻。”安内利泽·胡贝尔说“所有人都向他伸出了手”,而元首突然越过其他人的头顶,向她伸出了手:“他的眼睛对我施加了可怕的力量,我不由自主地把我的手伸向他。”

吊诡的是,第三帝国时期的女性权益出现了巨大倒退,按雅劳施的话来说,“纳粹建立的体制是厌女的。”为减少经济萧条时期男性的失业,纳粹推动女性回归家庭,这极大逆转了魏玛共和国时期争取的女性职业进步。纳粹还致力于打造母性崇拜,宣传女性的任务是创造一个真正的“民族共同体”。在“生命之泉”计划中,种族纯洁的女性被安排怀上雅利安男性的孩子,并宣扬成“给元首一个孩子”,这一计划制造了数万个婴儿。战争结束时,他们中有很多无人认领,沦为孤儿。
战争中,女性在后方经历着无差别炮火袭击,被安排到军工厂顶替男性空缺,还遭遇了大规模性暴力。在战争中德国女性想出一些办法躲避强奸,比如“穿得像个男孩”,用灰烬弄脏自己的脸,在身上涂抹鲜血,让自己失去吸引力。乌尔苏拉·贝伦伯在回忆录中写,一个蒙古人走进房间,把她推到了一个满是垃圾和油的车库里,“他用自动手枪指着我的头,把衣服从我身上扯了下来。我感到痛苦、厌恶和恐惧,与男人的第一次接触就遭遇了暴行。我月经来得很多,腿上都是血。”事后,她“一个人躺在那里,只有一个想法和愿望,就是能够去死”。一名受害者回忆,当无法抵抗时,“我干脆让它发生在我身上”,告诉自己“这不是你自己,这只是身体,可怜的身体!你离得很远,很远”。强奸过后,这些女性需要寻找土方和堕胎医生防止怀孕,还要面对自己伴侣的责怪,这让侮辱雪上加霜。

在受害者与行罪者之间:人们如何回望破碎的生活
在这些日记中,人们面对过去的态度往往徘徊反复:“一边是将自己标榜为受害者来脱罪,一边是自我批判式地承认对罪行负责,在两者间摇摆不定。”一种常见态度是后悔自己“善意”的爱国情绪被纳粹利用,海因里希·布施曼写:“保卫祖国的诚实的民族感情被滥用了。”许多人积极参与二战并非是忠于希特勒,而是为了“善良的德国免受残暴的布尔什维克军队的侵扰”。马丁·西格认为,“当时我们通常只是在回应无法阻止的外部力量。”即使是一些纳粹的反对者,在那时也认为应该履行“爱国职责”。然而这类观点背后的预设是国家高于一切,无论战争正义与否,年轻人为国参军都是无可指责的。雅劳施发现,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许多老兵自传中都出现了对此的反思。布施曼回忆:“当我意识到这场我自愿参加的战争不是防御战,而是征服战时,我的情感在1942年发生了改变,从志愿者变成了战争和希特勒政权的反对者。”
另一些人则反感普通人对德国罪行负有责任的说法,他们认为,错误的是纳粹领导层。年轻的退伍军人格哈特·塔姆将不幸归咎于“罪犯、纳粹党头目、刽子手和集中营管理者”,而自己的行为是在“延迟、拯救和阻止毁灭”德国。“我们只是在做自己的工作”、“我们都被纳粹误导了”、“遭到了元首的背叛”这些说法常常出现,更顽固的民族主义者则认为,一战胜利方应该对此负责:“我们不是罪犯,而是针对德国人民和帝国的大清洗的受害者,那是我们的对手根据强加的凡尔赛和约发起的。”
无知是另一个常见理由,威尔·泽尔曼—埃格贝特称:“大多数德国人对数以百万计的人被罪恶地谋杀一无所知。”东德工程师阿尔贝特·莱特霍尔德写道:“我没有意识到任何个人罪责……集中营的存在是已知的,但从不清楚它们的数量和其中非人道残忍的程度。”
反思的文字也在回忆录中出现,虽然只来自于少数人,但这些笔触仍令人动容。迪特尔·舍恩哈尔斯是曾经相信“德国会胜利”的士兵,战后他移民瑞典,成为了大学教授,他在课堂上告诉学生们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让他们警惕年轻时的理想主义被不负责任的煽动者滥用。在日记里他写道:“要竭尽所能地避免另一场战争,不仅是核冲突,而是战争。”回顾自己一生破碎的生活,他用了“永远不再允许”这一表达,并在短语后认真地写下:“独裁、战争与大屠杀。”

专访康拉德·H.雅劳施:找到德国苦难与罪行之间的联系,才是正视德国过去的关键
界面文化:是什么促使你去研究普通德国人如何经历20世纪的?
康拉德·H.雅劳施:我写作《破碎的生命》是为了挖掘普通德国人如何讲述他们20世纪的经历,这些民间回忆(Popular Memory)往往与官方记忆文化和学术历史不一致,从普通德国人身上可以窥见他们在这些经历中的反思过程,正是这些创造了1945年后的德国民主政治。
界面文化:个人叙述的生活史总是不同于宏观的历史描绘。你也在书中提到,个体叙述可以赋予历史更多的“人性维度”,你研究的这些普通人自传揭示了哪些被大历史误解或忽视了的图景?
康拉德·H.雅劳施:许多历史研究都是关于国家、社会、经济、意识形态的,而他们如何对历史中个体产生影响则没有受到足够多的关注。从这些自传里可以看到,普通人既是独裁统治和战争的附庸,又是政治压迫和大屠杀的受害者。探索“人性维度”(Human Dimension)意味着比传统的历史叙事更认真地对待这种矛盾的关系。
界面文化:我们的记忆不可避免是被更广阔的社会文化所塑造的,你也强调人们的写下的这些“记忆”不等于当时“真正发生了什么”。你在书中是如何处理人们的记忆与“历史”之间的裂痕的?我看到书中对人们自传文字的评论与批评似乎并不多。
康拉德·H.雅劳施:在书中,我试图探索实际事件和人们回忆之间的张力。由于许多学者已经很好地重构了实际发生的事,我转而关注事件是如何被记住的,以及普通人从他们的经历中得出了什么结论。这不是一个记忆与事实两者择一的事情,而是关于实际发生的事如何与过去的记忆互相关联的问题,因为后者会影响对未来的决定。我看到人们的自传往往带有悔意,对于第三帝国,他们也常常自我批评。
界面文化:你选择的传记材料都来自1920年代出生的德国人,他们从祖辈那里获得了对第二帝国与魏玛共和国的印象,青年时代在纳粹统治与二战中度过,后来还经历了东西德的分裂与统一。为何你将这代人的一生形容为“破碎”?与其他世代相比,他们有什么特点?
康拉德·H.雅劳施:说1920年出生的普通德国人的生活是破碎的,是因为一战、大萧条、独裁统治和种族灭绝破坏了他们从童年到成年的和平,人们同时成为了施害者和受害者。直到1945年后的冷战,大多数德国人才回归所谓“正常”的生活,他们上学、开始工作、组建家庭等。魏玛出生的这一代人是参与国家社会主义最多的一代,同时他们受独裁统治的影响也最大——男人作为士兵在前线被杀害,家庭主妇在家中轰炸时丧命。

界面文化:《破碎的生活》前言部分提到,这本书试图探索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普通德国人支持纳粹政权,最后这个问题是如何被回答的?
康拉德·H.雅劳施:《破碎的生活》通过观察希特勒青年一代来解释第三帝国为何如此受欢迎。这些年轻人比任何其他年龄组都更热情地接受国家社会主义。他们的父母或许已经建立了其他的信念,但年轻人更容易卷入国家社会主义的宣传中,这些宣传声称能为德国提供更美好的未来。正是这个年龄段的人最热情地接受了国家社会主义,因为他们相信希特勒的承诺。
界面文化:在这本书中,你也非常关注女性在战时的苦难。当时为什么有这么多女性支持纳粹,即使纳粹如你在书中所说建立了一个厌女的制度?
康拉德·H.雅劳施:纳粹确实是厌女的,所以回想起来,有这么多女性支持第三帝国是很令人惊讶的。相当多的人对纳粹宣传的家庭生活和母性的保守榜样感到满意。关于这些女性的遭遇,她们虽然没有在前线战斗,但她们在工厂工作,在家中遭受无差别的轰炸,再加之残酷的逃亡和驱逐——这些是二战期间妇女遭受的主要苦难。
界面文化:在人们的回忆录中,关于德国联邦共和国成立的部分并不多。你在书中也写道,那时的西德人“如果政治不发挥作用,人们会很高兴,这样他们就可以追求自己的事业和私人生活”。在你看来,这背后是什么原因在起作用?
康拉德·H.雅劳施:许多德国人因他们的政治参与而遭罪。他们震惊于魏玛帝国时期统治者的无能,失望于魏玛共和国的混乱,最终幻灭于对第三帝国的毁灭。结果是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形成了一种“没有我”(Without Me)的态度,他们专注于恢复私人生活,而不是建立第二个德国民主国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联邦共和国的积极表现最终使这些不关心政治的人相信,民主是一种比独裁统治更好的政治制度。

界面文化:在你选取的材料中,工人阶级的自传只有10%,你认为这会影响到可靠性吗,特别是涉及到东德的部分?
康拉德·H.雅劳施:工人阶级的人往往不写作,因为他们忙于日常生活的挣扎,因此不可能找到相同数量的此类作者。那些成为知识分子和工作人员的人最初相信东德这个工人和农民的国家,但当反法西斯政府转变成东德执政党的独裁政权时,他们的幻想破灭了。在西方,许多工人最初持怀疑态度,投票支持社民党和一些德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认为联邦共和国比东德更繁荣、更自由。
界面文化:你提到这本书想重新发现人们面对结构性转变时的主体性。然而,似乎大多数人在写回忆录时认为,他们在第三帝国时期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我们只是在做我们的工作”或“我们都被纳粹误导了”。你怎么看待人们在历史事件中的主体性?我想这个问题也同普通德国人应该为第三帝国罪行担负什么样的责任相关。
康拉德·H.雅劳施:事实上,支持国家社会主义的一个流行借口就是声称自己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虽然这种理由让许多人推卸了他们的责任,但少数人也意识到这是不够的,他们进行了严肃的反省,这同官方的记忆文化以及大多数自我批评的学术态度相符合。正是这种自我反省,最终将德国的记忆文化转向了一个批判性的方向。
界面文化:一些观点认为,聚焦德国人的受害经历可能会导向对二战罪行的开脱,后来新纳粹主义的兴起也借用了类似的策略,你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康拉德·H.雅劳施:从表面上思考德国人的受难确实会有这样的风险,因为他们强化了歉意同情的视角。但忽视这些发生过的经历无济于事,重要的是思考德国人为何遭受苦难——答案清楚地指向纳粹独裁和大屠杀。找到德国苦难与罪行之间的联系,才是正视德国过去的关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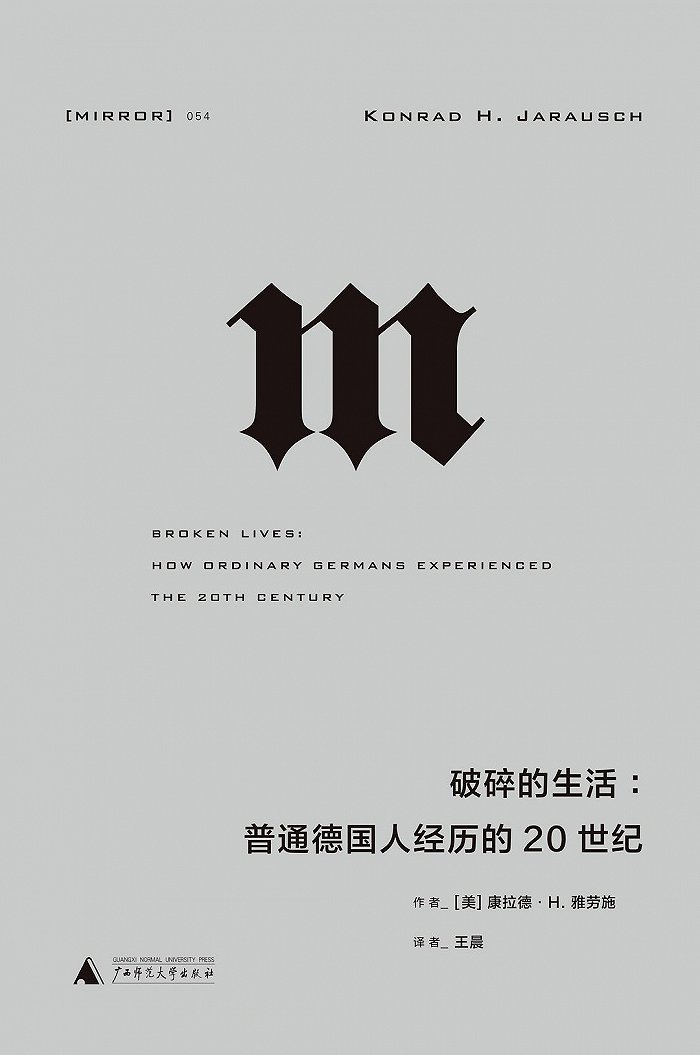
[美]康拉德·H.雅劳施 著 王晨 译
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
(内文图片均由出版方理想国提供与授权)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