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编辑 | 黄月
正德十二至十三年(1517-1518),王阳明因平定动乱而在南康县获得生祀。推动这座生祠建立的是当地四位耆老,他们关心的不是这位伟大哲学家的心学思想,而是他卓越的军事领导才能如何庇护一方百姓的生计。他们如此赞颂王阳明:
“俾我民安我父母,保有我孙子,利我桑麻谷粟,士卒业于校,工食力,商贾货殖于道罔虞。”

所谓“生祠”,最早可追溯到汉代,大多是因为祠主关心民生疾苦而在其生前设立与供奉。至明代,生祠成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政治文化现象。对明史稍有了解的人对生祠的第一印象,或许是大宦官魏忠贤的党羽为讨好他而在全国各地为其立生祠,但实际上,明代生祠并不仅仅只是阉党恶贯满盈的证据,而是在明朝专制集权的土壤中,生发出的一套极具在地性的政治模式:地方官受命于皇帝,并由平民决定其价值,平民借此表达政治观点,争取自身利益。
因此,生祠在一定程度上是明代平民获得政治话语权的工具——在地方官频繁调任的情况下,平民借由为心中好官立碑立祠、赞颂祠主的做法呼吁继任者维系(脆弱的)德政,帮助抵抗朝廷的苛政。而从地方官的角度来说,他们能通过施行德政收获民心与声望(生祠标志着民心与声望的顶点),进而积累政治资本。以生祠为纽带建立起的官员-平民利益体,在调和中央与地方政策的矛盾——中国政治史的恒久问题之一——过程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在《小天命:生祠与明代政治》一书中,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教授、明史学者施珊珊(Sarah Schneewind)首次将生祠置于明代的政治和信仰之间进行研究,她通过大量碑刻记录、地方方志和文人文集,考察了生祠制度背后的矛盾与张力。在接受界面文化(ID: Booksandfun)采访时,施珊珊指出,明代生祠制度的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种由士大夫到升斗小民各阶层人士形成的社会共识缔结而成的制度,这一社会共识重新发现了理学经典《大学》中的思想:“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施珊珊认为,生祠制度很大程度上来说呼应了明史学者宋怡明(Michael Szonyi)在《被统治的艺术》中提出的观点——无论政治力量施加的结构性压迫多么强烈,普通人总是能够保有自己的判断,既冷静又机智地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民意,正如明代为官者所承认和强调的,一直是衡量德政的重要(如果不是唯一)尺度。


01 作为一种民意象征,生祠对明代官员有很强的吸引力
界面文化:生祠在帝制中国是一个悠久深远的现象,它最早出现于汉代,在宋代数量显著增多。除了为宦官魏忠贤树立生祠这段臭名昭著的历史之外,在明代的背景之中研究生祠有何特殊的价值?
施珊珊:我做生祠研究,是因为它揭示了在明代这样一个专制且高度官僚化的时期,地方人民发表政治言论、采取行动的可能性。同样我也关注魏忠贤和他的东林党对手如何围绕生祠明争暗斗,因为生祠代表着民心所向。这种象征物竞争源自一个直白的事实:建生祠是地方受教育阶层讨好一位官员的方式,当这位官员升迁后,他就有可能反哺地方,一个互惠的赞助关系就成立了。因此,围绕生祠发展出来的习俗定规越过了法律的规定——它们试图消解真诚祝贺与贪污奉承之间的张力。一旦这些习俗定规确立下来,它们就被精心阐释为一种新观念。
首先,生祠话语(关于生祠和其他类似荣誉的阐释)特别关注平民的情感,以此“确保”建生祠的正确与真挚。这种对平民和情感的关注预示了(16世纪早期至中期)王阳明学派关于各阶层人民内在道德能力的论断。其次,东林党和阉党在16世纪晚期采用并发展了生祠理论,以之宣扬他们各自对德政的不同主张。再者,包括生祠在内的地方荣誉机制为的正是抵抗官员频繁调任的异化逻辑,当地人将优秀的州县官奉为“君”,这一实践启发了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提出“寓封建于郡县之中”的观点。通过将官员的合法性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之上,明代的生祠实践实际上是在一个新的语境内提出了旧观点,并因此修正了(传统中国政治)思想。明代生祠值得研究的原因正在于它们充满了矛盾与张力。
界面文化:生祠体现了明人怎样的思考方式?
施珊珊:第一,它们提出了一些宗教观念方面的有趣问题。明人的宇宙观认为万物皆有“感应”。政治与信仰——个人与公共领域的罪恶与美德——是密不可分的,它们通过因果报应、天人感应和各路神鬼相连。亡者的魂灵能在这个感应宇宙中起到作用,比如回应祷告、降下奇迹。那么生者的魂灵又如何呢?是的,明人相信它们也能起作用!当在江西广昌任职二十余载的江浩获生祠祭祀时,何乔新在为之撰写的生祠记中预测,
“岁时必谒焉,饮食必祝焉,水旱疫痨必祷焉。事有不平者,必号于庭而诉焉。”
第二,生祠在东亚有两千年的历史。一些唐、宋、元代的生祠到明代仍享有奉祀,而一些明代生祠一直留存到清代甚至今天。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出一个观点,元代的生祠试验影响了明代的生祠思想与实践,正如元代政治塑造了明代平民主义以及明代治理理念的许多其他方面,包括元皇庆二年(1313)理学课程被纳入科考系统、社学和职业世袭制税目。元代法律不再要求建生祠、树去思碑需要取得国家许可,到了明代,这种自由发展为一种主张,即当地人(包括平民百姓)有权利根据州县官和其他官员的表现决定谁值得被纪念。
第三,生祠反映了声誉在个人、家族和公共事务中的作用。生祠是地方荣誉体系的一部分,它代表了一个地方社区与国家的关系。这一荣誉体系其实是一套将来去匆匆的官员与当地建立长久联系的策略,包括极尽夸张之能事的惜别、命名实践、颂歌与去思碑、保留衣冠、一些诗意的或含有历史典故的比喻,以及人人皆知但常常被误解的“父母官”隐喻。历史学家萧公权认为这些荣誉是腐败士绅讨好官员,以获得特别优待的手段。昆曲《牡丹亭》就嘲讽了生祠等做法。但明人在不同场合嘲讽一切事物,而如果所有给予官员的荣誉都是虚伪的,那人们也就没有了嘲讽的理由,更不要说积极追求、操作、怀疑和考验它们了。职业官僚很清楚,他们既有可能获得地方荣誉与道德尊严,也有可能遭受贬损与鄙视;他们的家庭、同代人和后辈官员将评说其功过;中央政府则将决定其升迁与贬谪,以及他们的身后名。如果不理解这一广泛且人人皆知的现象,我们就不能理解这个帝国的治理者们的动机与选择。
另外,生祠代表了(儒家)核心价值观念。宗祠事关儒家孝道价值观,但身为研究宗祠的后人,我们其实并不知晓父慈子孝是否真的存在。作为一个仪式性场所,生祠表达的是另一种儒家核心价值观:君主与官员应当以民生为重,尊重民意,而臣民也应当有所回报。正如一位作者所写,“生祠应当源自人民对执政清明、德行无双的官员真诚的爱戴与钦佩。”明人知道,树立生祠既有真诚的目的,也有动机不纯的目的,正如任何核心价值观的遵循都有一定的虚伪存在。研究它们,能够拓展我们对明人能想什么、能做什么的理解——也就是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中国文化的界限在何处。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明确表示研究目的是超越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那么这本书如何增进了我们对明代政治、社会、文化与宗教的理解?
施珊珊:作为现代人,我们倾向于认为政治是政治,宗教是宗教。在明代,启蒙运动还未发生,科学还未被发现,宗教和政治在许多方面是彼此缠绕的。以生祠为例,它既是人们表彰一位深受认可的官员的方式,也是人们祭拜他的场所。一些明代文本中“德”与“灵”是可彼此替换使用的。但与此同时,这并不意味着明人把人类活动与童话故事混为一谈。在任何一个具体事例中,他们会说,“那个人的厄运是人为的”或“那个人的厄运难以解释,可能是邪灵作祟或因果报应”。这意味着历史学家应更谨慎地对待“政治”机构与“宗教”机构的标签化。
我们在做历史研究时需要警惕的另外一组二元对立是好人与坏人。在现实生活中,没有谁100%的好,也没有谁100%坏。明人知道这一点,他们愿意供奉一位治理水平高的官员,即使他有一些品格缺陷。魏忠贤不是100%的坏——也许70%的坏吧——有一些官员与他合作;而东林党也不是100%的好,一些宫廷宦官与他们合作密谋推翻所谓的“阉党”。双方都希望获得生祠的荣耀,因为它代表着平民百姓的认可,即使对双方来说更重要的其实是争取皇帝的支持。所以我们不能称一方是“君主主义者”另一方是“平民主义者”,这些二元区分其实并不反映现实情况。
另外一组二元对立是合法与非法。根据明代法律,一位官员只有在离任后才能获得生祠,但高级别的官员,甚至是礼部尚书本人,都在碑刻中公开表示过为在任者建生祠表明民众的衷心爱戴,因此是完全合理的。

[美]施珊珊 著 邵长财 译
万有引力 |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2-2
界面文化:党争双方都利用生祠来声张“合法性”这一点非常有趣。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当时的党派政治促进了生祠实践?
施珊珊:我不这么看。魏党和东林党人都不过是利用生祠的悠久传统而已,正如之前所言,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明初、元、宋、唐甚至是汉。双方都觊觎生祠,是因为生祠显示了民众支持,继而象征着一个人超越党派主张的无上美德。比如说,第八章中写到的泰州同知王思旻,在旱灾侵袭15世纪中期的泰州时,他为了引起一位勘灾大臣的注意,跳入江中为民请死。王思旻为此获得的声望(包括一座生祠,后来他的孙子还拜访过)显然是当时的官员与士人都艳羡不已的。即使我们不相信关于这些人的每一个感人故事,我们也需要承认这些故事本身代表了当时士人向往的一种处世之道。
02 普通人具有自主思考、自主决定何为最佳利益的能力
界面文化:生祠在明代“平民主义”(populism)的背景下发展壮大。如今“populism”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甚至在很多情况下贬义的词语。所以明代的平民主义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施珊珊:许多学者已经对明代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充分研究,书中使用“明代的平民主义”指的对它们的一种整体性概括。它包括通过经商和科举实现社会向上流动;包括晚明的慈善团体——韩德玲(Joanna Handlin Smith)对此有深入研究——虽然由士绅领导,但不仅吸纳平民,而且模仿平民的组织形式。王阳明学说主张,无论出身如何人人皆可成圣,这也是明代平民主义的一部分。许多明代出版物针对的是大众读者,因为当时识字率有所提升,很多人开始可以读一点书了。明代的国教也吸取了民间宗教的一些元素。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明代平民主义”的历史事实。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提出的最重要的观点之一是,平民百姓通过生祠向州县官施压,要求对方考虑当地利益。我们是不是可以借用詹姆斯·斯科特的观点,称之为明代版本的“弱者的武器”?
施珊珊:我不同意你的观点。生祠和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是不同的,因为生祠已经被体制化了。生祠不仅为百姓所用,也为政治精英所用,他们都通过生祠向他们欣赏的官员表达认可,或向他们厌恶的官员表达异议。鉴于生祠是有石刻的建筑物,它们是当地人民表达政治观点的体制化方式,这意味着他们以此举为后世的历史学家留下档案记录。它们和“弱者的武器”的不同在于,它们是完全合法的、有正当性的、被明代法律和社会实践认可的——它们不是抵抗精英权力的手段。
界面文化:平民百姓积极使用“父母”的隐喻试图唤起官员的良知,而我们通常认为这种观点是统治阶级为了强调臣民的顺从心理向他们灌输的。
施珊珊:没错。研究发现,“父母官”的措辞更多集中于草根阶层的文本中,在那之后它才被国家和政治精英征用。而且,作为一种隐喻,“父母”在各种各样的明代史料中出现,它既指父母有责任照顾子女,也指子女有责任孝顺父母。在生祠的语境内,这一隐喻通常是指一位深受欢迎的当地官员“爱民如子”。
界面文化:那么,我们要如何理解明代普通人的“主体性”呢?
施珊珊: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普通人绝对具有自主思考、自主决定何为最佳利益的能力。虽然大多数平民没有接受过多少教育,甚至很多人根本目不识丁,这也不意味着他们就比社会精英愚蠢、比政府官员狭隘。就明史而言,我们无法找到证据证明强大的中央政府能为人民做出所有决定。
日本历史学家长部和雄提出过一个观点,他认为生祀反映了人们对德政六个方面的肯定。第一个方面是移风易俗(教化),也就是弘扬儒学和儒家礼仪,大兴科举,以对抗佛教与道教的影响力。但事实上我发现,如果一个官员只做这些事——试图给民众洗脑,改变他们的想法与信仰——他几乎是不可能获得生祀的。反之,民众为这样的官员建立生祠:他们有能力保护民众不受有组织的暴力侵害,并且认识到那些土匪盗贼通常也是走投无路的绝望之人,减免赋税徭役,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比如为促进贸易修建桥梁)但不铺张浪费,公正司法且不滥用刑罚,通过各种手段改善民生(无论是施舍穷人、促进商业与生产,还是成功祈雨)。我在第二章《父母之官》中详细介绍了这一方面的情况。
第二,虽然精英阶层总是侃侃而谈自己如何肩负引领万民的责任,他们也认为州县官的优劣是交由普通人评判的,他们无法被糊弄。值得注意的是,《大明律》既没有规定生祠必须由平民建立,也没有阻止士大夫自己建生祠。但是,明人意识到士大夫可能会利用生祠奉承官员以谋求晋升机会。为了防止此类腐败,把民意作为生祠之基础就成为了一种社会而非法律要求。明代的士大夫确实常常撰文批评百姓愚昧,容易被方士蒙蔽欺骗,但历史学家也应该注意到明代叙事中的另一面向——在这一方面,明人的想法和美国哲学家的想法更接近,他们都认为普通人意志坚定,拥有良知。
其实,中国传统思想中有一个脉络甚至走得更远。民众不仅被认为是领导者是否胜任的最佳评判者,而且最好的领导者还应当是那些听从民意的人。理学经典《大学》援引《诗经》:“乐只君子,民之父母。”对这句话的解释是:“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
第三,如果我们只看民间信仰,会发现普通人积极主动地选择祭拜哪些神灵,遵循哪些仪式,即使那些他们真心敬服的官员(因为他们推行减免税赋、改善民生等政策)强烈反对,他们也依然故我。在一篇有待发表的文章里,我写到了一些虽抨击当地民间信仰仍获得生祀的官员案例。当官员下令拆毁那些官方眼中的淫祠,当地人会重建它们,这也不妨碍他们生祀那位官员。
宋怡明的《被统治的艺术》比我的研究更有力地说明了非精英群体如何既冷静又机智地维护自己的利益,鲁大维(David Robinson)对中国北方地区土匪的研究也揭示了,普通人能出于自己的目的调适他们与国家的关系。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历史学家的研究也发现,普通人就和精英一样,能以各种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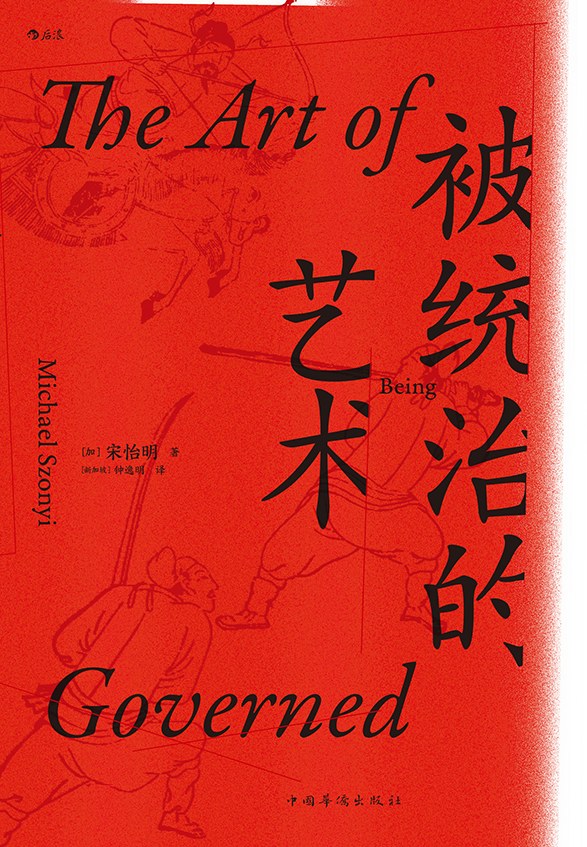
[加]宋怡明 著 钟逸明 译
后浪 |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9-12
界面文化:在多大程度上我们能说,生祠这一普通人表达政治立场的合法渠道被精英-士大夫体制化,“民意”被他们重新阐释,为己所用?
施珊珊:我得说这是一种落后的想法。生祠是各阶层人士一同建立完善的机制,然后东林党等超级精英利用了这一业已存在的形式。历史学家应该意识到,虽然精英主导了历史记录,但他们难以主导明代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需要认真理解史料,但也要明白文本的言外之意。比如说,我在第五章《从奉承到参与》中记录了东昌知府陈儒在洪灾中救助了武城百姓,其中一项举措是向朝廷征得许可,用当年拨发府库的一笔资金替代了武城当年的税赋。多年以后,“田夫野老”坚持要为陈儒建生祠,尽管陈本人、当地官员和士绅试图阻止。他们终于获得了一位官员的支持,礼部侍郎王道后来撰文表扬了这些普通人违背那些精英士大夫的意愿。在他看来,这些不从的百姓真诚地为建立生祠努力,反映了天道,并能促进政治宇宙的感应与平稳运行。
03 民意与官员的良知能为专制权力踩下刹车
界面文化:什么是“小天命”?这是明代官员积极实践的意识形态,还是某种不成文的政治规则?
施珊珊:“小天命”不是一个明代出现的术语,而是一个我根据史料总结出来的模式。我认为明代的官员和平民也看出了这一点,只不过并没有明确地用语言去定义它。它指的是上天能够像回应皇帝的德政一样,回应一位州县官的德政。皇帝如果有智者辅佐(这是科举的意义所在),关心百姓的生计与安全,而且本人品行端正(包括积极履行礼仪义务),就能获得上天的肯定。当皇帝施行德政,上天会降下祥瑞,反之就会降下灾祸以示惩戒。民心也是预示之一种,失去民心是灾难的前兆。
对于州县官来说也是如此,虽然他的管辖范围更有限。我们都知道方孝孺,他的父亲方克勤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他因为太过端方正直不易相处。方克勤主政济宁时曾违背中央的要求,因为他认为该政策虽然满足了朝廷的军事需求,但伤害了济宁百姓的利益。上天因为他的德政两次降下吉雨,并数次回应他的祷告为百姓带来丰收。百姓中流传的一首歌谣赞颂他为百姓免除徭役,使五谷丰收,是当之无愧的民之父母。这个例子让我开始思考“小天命”的问题。
界面文化:通过明代的种种生祠实践,我们也能看到当地利益并不总是与朝廷利益一致。一个获得生祀的好官员通常是那些能够维护辖地百姓利益,帮助他们抵挡中央政府税赋劳役要求的人。当地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张力是中国历史上的长久问题。和其他朝代相比,明代的此种权力冲突是怎么样的?
施珊珊:这要分两方面来谈。一方面,一些明代官员希望为民服务而非简单地为国尽忠。相比更早的朝代,明代官员更有可能与家族内的非精英群体保持紧密联系,或者他们本身就是底层出身。众所周知,不少明代官员在皇帝犯错时直言不讳,而且他们当中的不少人——正如在任何政府当中一样——直接在自己的任期内施展抱负,践行理想。在另一方面,我的印象中清代对州县官的控制更加严密,不过这一点你可能需要向清史学者求证。他们确实需要担心程序合法性的问题,而且他们也没有多少空间能够在辖区内试验更灵活的税收等民生政策。
界面文化:书中还提到,地方士绅不甚乐意见到地方官与当地百姓建立直接的联系,因为这种同盟威胁到士绅在地方领域的道德权威和话语主导权,所以他们会在生祠实践中刻意打压普通人的重要性。
施珊珊:在一些情况下,特别是在晚明时期,一些士绅试图降低百姓的积极性,视之为一种威胁——这是不是很有趣?当然,如果它从来都不是一种威胁的话,他们也就不会担心了。但在其他的案例里,他们会刻意在文章中宣传一座本来主要由士人赞助的生祠其实得到了民众支持,甚至一座由儿子为了纪念父亲建立的生祠都被阐释为民意使然。这是因为,明人普遍认为百姓的支持保证了这位获得奉祀的官员的所作所为符合更广大的公共利益,而不仅仅是为了当地精英或一小群人。
界面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明代被认为是压迫性专制集权政治的一个典型历史案例。这是否是一种刻板印象?
施珊珊:谈论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对“专制集权”(autocracy)这个概念特别小心。它的定义是一个人掌握“绝对权力”的政治系统,但在具体历史语境内这依然不是十分明确。它指的是统治者能肆意杀人吗?明太祖确实是这样(任何一个统治者,即使是一个王朝的建立者,也不应该处死成千上万的人),但大明王朝为他的凶残付出了代价:他不仅未能将手中的权力平稳交接给自己的孙子建文帝——后者在一场惨重的内战中丢掉皇位、被太祖之子朱棣取而代之,而且让朝廷难以选拔出优秀的人才为国效力。直到15世纪中期在“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的辅佐下,明朝才从动荡中恢复过来站稳脚跟。
“专制集权”指的是明朝奠基者或其他政权奠基者能罔顾过往经验,从零开始创造一个全新的体制吗?明太祖没能做到这一点,许多政府机构是从元代借鉴而来的。“专制集权”指的是太祖能要求所有人都根据他的意志行事,或全盘接受他的观点吗?他不能,因为发现自己总是遭遇不从和抵制,他多次更改政策。
“专制集权”指的是统治者无需咨询他统领的官员的意见吗?事实上,所有的明代统治者都需要一些官员的支持,在明代大多数时间里,一项政策需要经过所有高级官员认真商讨,一致通过才能施行,尽管最终它是由皇帝签署批复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事情是这样进行的,我们不会刻意关注它们,因此那少数几个皇帝完全无视官员意见的戏剧性案例在历史图景中就显得尤为突出。但即使是那位与官员争斗不休,甚至当庭打死过官员的嘉靖帝,也没法在任何事情上随心所欲;万历帝也是如此,他的回应是拒绝与官员对话。
明代的儒家学说教导士人,无论为官还是为民,都要对天下百姓怀有强烈的责任感。李戴(1531-1607)就任兴化知县期间曾遇洪水肆虐,他向天祷告,表示愿意以自己的生命换取百姓的平安,因此得立祠奉祀。当然,明代是有不少懒惰或腐败的官员,但其他许多官员愿意为了自己相信的东西(包括为减轻民众的痛苦)对抗上司甚至对抗皇帝。即使他们为此仕途不顺,他们依然能获得百姓的奖赏(比如一座生祠),在同僚中获得好官声,并在死后继续得到供奉。那些有良知的官员能为专制权力踩下刹车。
在现代社会里,我们很容易对君主体制极尽嘲讽之能事,但我们需要认识到如下事实:明代的君主制一方面确保了可预测的皇位继承(它当然不完美——事实上至少一半的权力交接或多或少存在问题),但另一方面也给每一位皇帝造成压力,他们需要好好表现,才能顺利地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除了一个皇帝所要思考的原因之外,把后代送上皇位也是确保自己死后能够得到供奉的唯一途径。这让皇帝们总是强烈关注国家政体是否健康运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宦官独裁者从软弱的皇帝手中接过权力后往往更加暴戾、更加不可理喻。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