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编辑 | 黄月
喜,睡虎地十一号秦墓的主人,生在秦始皇时代,比秦始皇嬴政大三岁,死于始皇帝完成统一中国大业之后四年,是秦朝的基层小吏。他短短四十六年的生命,在历史长河里,不过是一个平凡而脆弱的瞬间。
两千多年后,历史学家鲁西奇用零落的材料,试图在那个遥远而陌生的时空里找到喜,理解他所处的世界。他回忆自己在寻找喜的过程里常感到淡淡的恐惧,一是害怕喜看到他的研究后觉得“这根本不是我的世界”,二是在深入材料后仍能体会到秦朝超越两千年时空的威胁感。“冻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我若之何?”这首先秦人民叹时代之苦的歌谣传唱了一代又一代,或许也曾经过喜之口。
鲁西奇埋头喜的相关材料十余年,将发现书写在了《喜:一个秦吏和他的世界》里。日前,历史学家罗新与鲁西奇围绕这本新书展开了一场对谈。罗新是鲁西奇的研究好友,在对谈中,他回忆了二人交往的缘起:他们曾共同参加同一个学术会议,罗新在会上倡导历史学界应该多关注底层与普通大众的视角,他发言结束后,鲁西奇才进门,并在后来的讲话里表达了几乎一模一样的观点。罗新听罢感动又振奋,二人一拍即合,决定组织一套小丛书,专门关注普通大众的历史。
历时数年,鲁西奇写出了《喜:一个秦吏和他的世界》一书,想象自己站在秦吏喜的位置,借他的眼睛审视巨大帝国的统治机器;罗新今年也将推出《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他利用墓志等史料勾勒了北魏宫女王钟儿跌宕起伏的一生,从她的视角呈现半个多世纪的北魏历史。

鲁西奇 著
理想国·北京日报出版社 2022-7
近年来,叙事化微观史写作热度颇高,鲁西奇否认《喜》采用的是这类写作方式。他坦言叙述不是自己的长处,书中聚焦的并非喜的个人生命史,而是借喜的眼睛观察他所处世界的结构,“我有明显的结构化倾向,这是我的长处,我的研究都是空间的、地理的……”在前言部分,鲁西奇强调历史学者的使命之一是“在历史中发现人”,他认为自己的入手点是国家,但这并不矛盾,因为“人都在国家里,只有弄清楚了一个国家,才有可能理解人的一生”。

鲁西奇说,他在书里想呈现的,是喜怎样从一个有血有肉的自然人,演变成为一个帝国统治体系的官僚符号。通过户籍制度、军功爵制、邻里的军事化编排等,秦朝将每一个黔首都固定在国家控制体系的特定位置上,使之从军应役、立功受爵、交纳租赋,在有必要或有利时举报同伍、同里的邻居,并在战场上形成生存共同体。
在《喜》的第一部分,鲁西奇主要关注喜作为人的自然性,包括身体特征、家庭与情感。第二三部分转向社会性与国家权力机构,以及人的自然性是如何被这些制度结构所冲淡的,“这些人的身份都是国家从外部强制赋予,每个人不得不沿着国家给定的路径去生活。我所描述的并不是喜作为一个人的一生,恰恰相反,它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喜的非人化的过程。”
相较于鲁西奇的《喜》专注时代性的社会结构书写,罗新的《漫长的余生》是一个更具叙事性的文本,围绕着主人公王钟儿的生命历程展开。王钟儿30岁之前是一个南朝官员家庭的太太,经历战争作为俘虏被抓到北方,成为了完全失去自由的宫女。王钟儿作为北魏宫女又生活了五十六年,最终活到86岁,所以罗新把她的故事命名“漫长的余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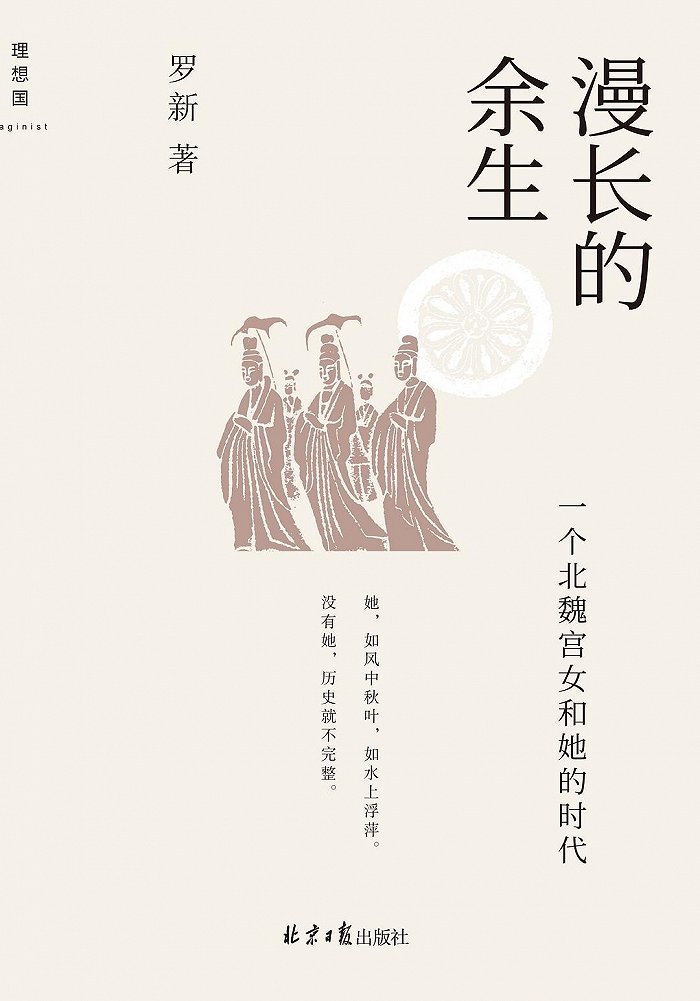
罗新 著
理想国·北京日报出版社 2022-7
十多年前,罗新读到王钟儿的墓志,一直想把这个故事写下来。他既希望大部分读者会觉得有意思,更担忧这一故事从历史学学科内部而言是否有意义,同行在读过之后能不能提出一些问题。罗新说,“我想,我是努力在让我感兴趣的历史故事和我希望完成的历史学科意义之间找到平衡。”
罗新认为,《喜》把这一平衡处理得很好,一方面它对史料的运用让人耳目一新,比如在对喜的家庭生活和男女关系的研究中,鲁西奇使用了大量《日书》的材料——《日书》是古人选择时日吉凶的参考书,记载一年中每一天是否适宜婚嫁生子、丧葬农作等各项活动。这类材料在秦简中很常见,但使用得特别且有说服力需要作者具备极深的功力。另一方面,《喜》的形式也让它不是无聊的读物。罗新指出,相比于文学和社科研究,很多人都忽略了形式对历史学的重要性,不同的内容、材料、问题适合的形式各有不同,“史学也是很在乎形式的,形式能够表现一个人的创造力。”

鲁西奇 著
新民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8
《喜》的另一个特点是关注秦朝普通人的生活,写秦朝却未写秦始皇,这在此前的秦史研究中十分少见。鲁西奇在前言中解释说,自己没有写秦始皇,是因为觉得世界基于每个人的存在才有意义,秦始皇和一个普通民众看到的世界是全然不同的。 “公元前三世纪下半叶的世界,不是秦始皇一个人的世界,而是无数人的世界……要将历史的‘世界’‘还原’为无数人的世界,而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些人的世界,”唯其如此,才能看到所谓盛世背后的复杂性。
罗新很认同呈现秦朝复杂历史的意义,“说到过去的秦朝,人们常常会想起浪漫的、英雄交响乐式的往昔,但实际上,往昔是具体丰富的,也有痛苦的地方。”他以书中常出现的名词“新地”/“旧地”、“新黔首”/“旧黔首”举例,它们出现的背景都是秦朝时期的征服战争,而“太多人把大一统的战争浪漫化了,却忽视了它有很可怕的、痛苦的那一面”。罗新也强调,今天的历史学家有责任呈现历史的多个面向,“历史是复杂的,我们接受单一面向历史教育的人,对现实只有单一的理解,我们作为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把复杂呈现出来 。”

罗新 著
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 2019-5
鲁西奇也指出,秦朝是一个身份制的时代,人们的不同身份决定了不同的生存轨迹和生活状态,“身份高的人可以享受荣华富贵,跟秦的官僚体系走得越近,所得到的名与利就越多;不自量力反秦的人,就可能被发配到巴蜀去。”这样的制度超越了作为个体的每一个普通人,并且长久地存在着。他常和朋友调侃,否认自己写的是“秦史”,因为类似的苛政并非只限于秦。“始皇帝无所不在、无时不在,虽然秦朝是一个短命王朝,但就秦制而言,二世三世至于万世的梦想是实现了的,这个做到的核心点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两个,一个是身份制,一个是层级制的官僚制。”在鲁西奇看来,这二者是制约中国历史2000年以来发展的最核心的两项制度。从这个角度来说,书中的全篇都写的是秦始皇,“你千万别说我没写秦始皇,你读这本书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到,始皇帝在里头,在每一个字里头,”鲁西奇说。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