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编辑 | 黄月
“这些雪糕就像藏在冰柜里的刺客,付钱的时候就刺你一刀。”这段时间,天价雪糕频频登上热搜,出现了一个新的网络词“雪糕刺客”,指的是那些看着普普通通却价格奇高的雪糕。夏日炎炎,走进街边食品店或便利店想买一支雪糕解暑的我们赫然发现,10元以上的雪糕已占据了雪糕市场的半壁江山,几十元一支的“网红”雪糕也并不罕见。
同类别的产品因品牌不同有价格高低之分,这早已是常识,高价雪糕更不是新鲜事。1996年,美国冰淇淋品牌哈根达斯在中国大陆开出了第一家专卖店,最便宜的冰淇淋单球要价25元,而当时全国职工平均月工资为539元。以“奢侈品”定位进军中国市场的哈根达斯,曾在一段时间里构成了我们对中产生活想象的一部分。安妮宝贝曾在首次出版于2000年的《八月未央》中,借小说女主角之口道出凝结在哈根达斯之上的对余裕生活的憧憬:
“出来的时候,看到哈根达斯的小店铺。我进去停留了很久,但里面的冰激凌太贵了,所以最后依然什么也没买。出来的时候拿了一份广告页,做得很精美,让人愉快。香草来自马达加斯加,咖啡来自巴西,草莓来自俄勒冈,巧克力来自比利时,坚果来自夏威夷……我一直在车上看着这份广告,我觉得它就像我的理想。”

近年来,随着“消费升级”和“新消费”潮流的兴起,不少中国本土冰淇淋品牌开始进入长期被外资品牌垄断的高端市场,带动了冰淇淋/雪糕单价的整体上升。但今年夏天,平价雪糕在线下零售渠道大规模消失,让我们开始质疑“雪糕刺客”现象背后某种心照不宣的消费逻辑:同一属性的产品,为何价格会有天壤之别?消费社会又是如何裹挟我们为不必要的高价买单的?
品牌的力量:以商品想象幸福

和雪糕相比,水或许是一个更极端地显露品牌力量的例子。水无色无味,虽然可能有味道和矿物质含量的差异,但喝着没有太大区别。在瓶装水被赋予品牌标识售卖后,不同的水开始出现差异,依云和娃哈哈的瓶装水价格相差甚多。在《制造消费者》一书中,法国学者安东尼·加卢佐(Anthony Galluzzo)也用瓶装水的例子解释了品牌的力量。

加卢佐指出,在我们从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进入相互依赖、用金钱换取商品和服务的工业社会后,“我们和他人劳动成果之间的关系被掩盖在物品之下。”消费者越来越疏远市场中绝大多数商品的生产过程,越来越难以衡量商品的成本、构造、所需劳动力和生产背后的困难,就只能以一种虚幻的方式去理解它们。而品牌,就是消费者理解商品本质、价值和意义的最重要途径。
具体而言,品牌通过激发联想对人们产生影响。这指的是,它将一系列想法和价值注入产品中,让消费者无需通过亲自接触和验证产品本身的质量,就能感到满足并欣然购买。品牌其实是一种符号工程,通过符号的打造和运用,产品具有了除使用价值之外的社会与文化价值,而后者才是品牌着力打造的。于是当我们购物时,不同产品的品牌形象和价格会造成种种先入为主的观感,影响我们的消费选择和对产品的实际体验。
为宣传品牌而发明的广告,就是一门“联想的艺术”:
“广告让商品得以象征个性、价值、属性、品质、社会地位等,广告可以告诉观众一件商品象征着什么,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商家希望这件商品能象征着什么。这种为商品增值的过程就是一种转移行为的过程,即把一些已经与特定人物、刻板印象和情境相关联的含义转移到商品上。”
加卢佐认为,在高度商业化的世界里,“我们是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拥有什么样的商品,通过拥有商品,附着于商品之上的种种符号也为我们象征性所有,这些符号往往与人类的普遍追求密切相关——比如快乐、自尊、友谊、爱情和家庭——我们通过追求它们获得幸福与满足,而品牌的力量正在于告诉我们,你可以“用钱换一件产品,再用这件产品换幸福”。因此,一件看上去平平无奇的产品也可以卖出高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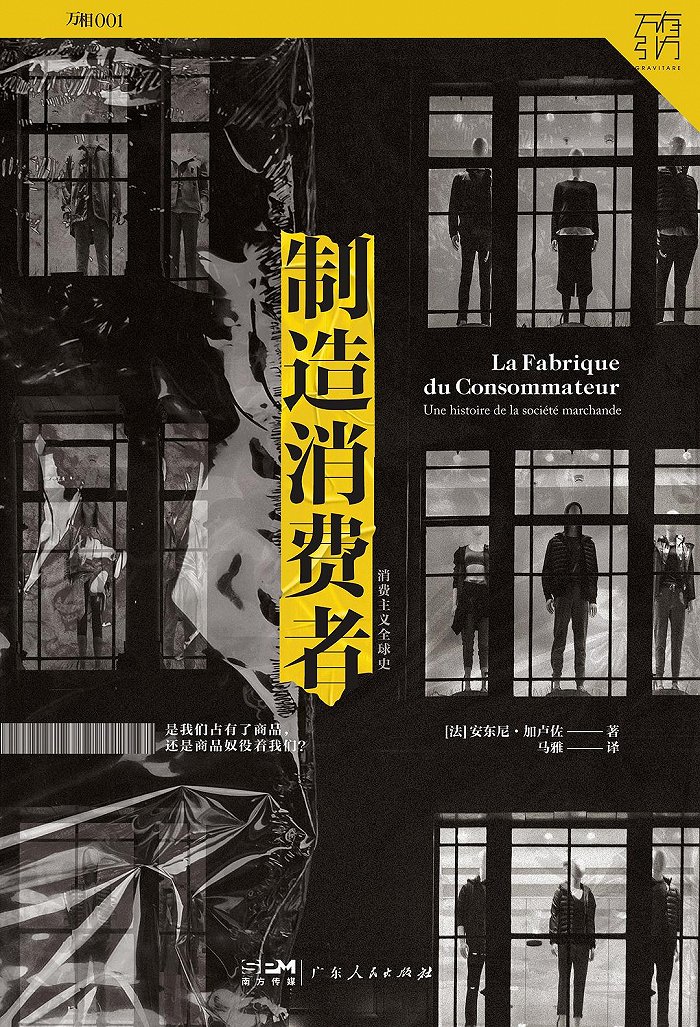
[法]安东尼·加卢佐 著 马雅 译
万有引力 |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2-6
在“雪糕刺客”热议中陷入舆论漩涡的钟薛高之所以有底气卖那么贵,很大程度上就是把握住了品牌营销的力量。钟薛高创始人林盛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像冰品这样没有太多技术含量的产品本身竞争壁垒并不高,“你不是高科技产品,你不是人造卫星,你不是火箭发射,你能做到的事情其他品牌都做得到。这种都做得到的情况下,大家比拼的是传播能力的问题。”
在加卢佐看来,在物流链进步和生产流程复杂化的21世纪,作为消费者的我们对商品的陌生与崇拜进一步加深,这也让我们更容易相信煞有介事的品牌营销所带来的符号联想。品牌“利用人们对安全、自尊、权力和抱团的渴望,也利用人们的认同和偏见,最重要的是,它利用了人们对事物的操纵欲和为事物赋予意义的欲望。商品一直是满足人们实际需求和心理需求的工具,也是一种表达人们思想和权力关系的语言,”《制造消费者:消费主义全球史》一书这样告诉我们。
被定义的消费者:消费明确“位置”也彰显“缺陷”
在商品极为丰富的当下,消费者不是应该享有更多元、更自由的选择权吗?如若真是如此,也就不会出现“雪糕刺客”这样的争议了。这个现象中引起我们同情与愤慨的标志性形象,是那些囊中羞涩的普通人,他们因缺乏“消费常识”而在冰柜中选中了高价雪糕,直到在结账台得知雪糕的真实价格后才恍然大悟并感到尴尬羞耻——这种因自身财力有限的事实被暴露而引发的耻感,反映的是一种已被我们深深内化的、与消费相关的评价体系。

加卢佐指出,随着传统等级制社会崩塌,被奉行平等价值观的现代社会取而代之,人们的消费行为也被重塑了。“这种新的社会模式下,阶级地位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人们的地位依附于市场,随时可能升级或降级。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全都取决于别人的眼光。”于是在当下,所谓的成功指的是“在别人的眼中显得成功”,而“成功”的表象往往由购买某些商品来打造。
因此,消费不能简单地看作购买一件功能物品的行为,它还有重要的社会文化功能——展示人在社会阶梯上的位置。这正是让·鲍德里亚提出的商品的符号功能,消费文化是一种由优势阶级控制的、高度符号化的文化,人们的消费选择看似自由,实际上是被符号所支配的,其目的是通过购买来证明自身地位的优越性。加卢佐指出,由于现代社会中没有谁天生比其他人更高贵,所以人们要相互竞争、比拼财力:
“这种通过竞争来实现平等的意识形态也在不断刺激着符号之战的爆发,而符号物就是正在孕育中的消费社会的引擎……虽然没有了旧的等级制度,但消费并没有因此变得平等,反而加强了人们围绕着符号物的竞争,成了一种‘总想高人一等,总想与众不同的执念’。”
消费相关行为及其意识形态的重塑,背后存在着一个更为深远的时代转向,即从生产者社会转向消费者社会。以无限扩张作为原动力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从开拓外部市场转向开拓以人的欲望为核心的内部市场,齐格蒙特·鲍曼指出,如今衡量人们声望和社会地位的不再是韦伯式的工作伦理,而是工资的差别,社会中的权力斗争变成了获得更多金钱的斗争,经济收益成为自治自主的唯一体现。以经济水平评判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倾向“也把人的动机和对自由的渴望牢牢地、不可逆转地转向消费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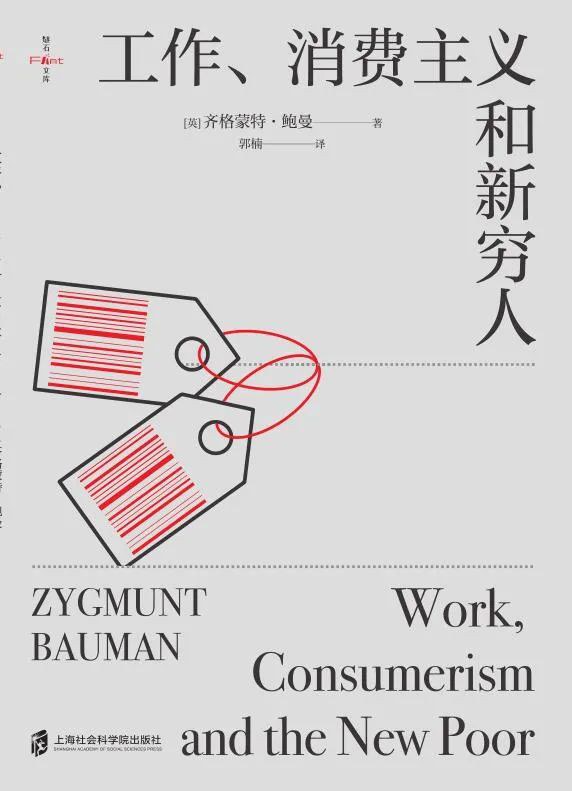
[英]齐格蒙特·鲍曼 著 郭楠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21-9
鲍曼指出,消费社会在国家和个人层面都将消费置于空前重要的位置。“经济增长”是衡量现代社会是否正常有序运行的首要标准,在消费社会中,经济增长与其说取决于“国家生产力”不如说取决于消费者的活力。自行构建社会身份是现代社会赋予每个社会个体的要求,职业曾是最重要也最有力的社会身份标签,但随着长期的、有保障的、确定性的工作越来越少见,社会身份也必须像当下的劳动力市场那样具有灵活性。消费文化与当代社会身份问题特有的矛盾性完美契合——人们可以通过消费在短时间内占有一种身份,但随着消费潮流的起伏变幻,人们需要不断地追逐更新、更好的消费品,以不断迭代身份、重新定义自我。
在这种情况下,“贫穷”也不再仅仅由失业定义,而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有缺陷的消费者”的困境。鲍曼提醒我们注意,贫穷并不仅限于物质匮乏和身体上的痛苦,也是一种因无法满足社会对“体面生活”的衡量标准而造成的负面心理状况。在消费社会中,“正常生活”是作为消费者在丰富的消费选择中自由驰骋的生活,如果一个人无法正常地生活,就意味着TA是一个失败或有缺陷的消费者,这种“达不到标准”会打击一个人的自尊心,带来羞愧感和负罪感。“今天的穷人是‘不消费的人’,而非‘失业者’,”鲍曼说。

了解消费者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为我们解读“雪糕刺客”现象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文化背景。在疫情反复、经济大环境空前复杂的当下,“新消费”和“消费升级”的光环正在失色。当随手在街边店的冰柜里拿起的国产品牌雪糕动辄几十元,雪糕这样的夏日甜蜜安慰似乎也成为一记打击,提醒着我们作为消费者的“缺陷”。而在“雪糕刺客”遭到热议之后,“荔枝刺客”“演出刺客”等网络新词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或许也在提醒我们注意,退出消费竞争机制对很多人来说已不再是一种文化姿态,而是一种事关基本生存需求的无奈。至于消费主义背后的结构性问题和人们面对的广泛困境,也绝不是声讨“XX刺客”就能解决的。
参考资料:
【法】安东尼·加卢佐.《制造消费者:消费主义全球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22.
【英】齐格蒙特·鲍曼.《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1.
安妮宝贝.《八月未央》.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
《风波之后,钟薛高有无可能卖平价雪糕?》,界面新闻
《中国人更有钱,但哈根达斯过气了》,ELLEMEN睿士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