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编辑 | 黄月
在文化批评领域,学者戴锦华素来以犀利敢言著称。近日,她在视频节目《未完戴叙》第49期中的一段发言在微博上引起了关注:
“中产阶级一边是文化生产者,一边他们是有消费愿望和有消费能力的,所以市场是为他们而生产的。大概五六年前有一个记者访问,说戴老师你怎么看待中产阶级趣味问题,我说中产阶级趣味不值得讨论,因为今天你说的所有文化现象,都是中产阶级文化。中国社会文化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除了中产阶级文化我们看不着别的文化了。”
虽然这段话的语境是中国社会文化整体,但鉴于戴锦华长期从事电影分析批评,许多人很自然地将这段话解读为她对中国影视文化的批评,比如微博上的一条高赞评论以《隐入尘烟》引发的争论为例,试图说明某种“中产文化”正在试图吞没农村现实:“《隐入尘烟》里海清的造型都能吵个八百楼,农村都得精致漂亮。”
纵观近年来的国产影视剧,学者毛尖发现,人们正逐渐与更富裕、更有权势的人而不是出身贫穷的人产生角色认同,这一点在青春剧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如果所谓的“中产文化”指的是影视剧里面的底层逐渐失语,中产阶级有更大概率被看到、演绎和讨论,这种情况在欧美影视剧中其实也存在,而且它的确与欧美国家中产阶级的整体境遇变迁有关。此外值得注意的另一点在于,政治、经济与文化语境的差异,使得简单搬运和套用同一套概念和分析框架对我们理解包括国产影视剧在内的中国社会文化帮助有限。
劳工阶层的“结构性缺席”与富人崇拜

劳工阶层在视觉再现中的“结构性缺席”远远早于我们这个时代。所谓“结构性缺席”,指的是体力劳动、贫困、工会运动和移民这些社会现象很少在大众媒体中被提及。法国学者安东尼·加卢佐(Anthony Galluzzo)认为,这与消费社会的兴起息息相关。自19世纪下半叶印刷品开始在大众中流行、大众媒体诞生起,资本主义经济就开始以此建立品牌资本和集体消费文化。1890年代广告成为纸媒的主要利润来源,报业与商业自此开始密切绑定,杂志则是首个完全致力于消费的大众媒体——相对于报纸的提升公民意识功能,杂志更多将目标读者对准大众消费者,致力于培养他们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文化,让人们对富裕的生活充满梦想,并且把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大众化”。

加卢佐指出,19世纪末问世的电影完整继承了杂志的功能——消费教育、社会想象的植入和商品平常化——且因其动态影像的属性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对消费的欲望。和经济劣势群体相比,富人显然是更完美的消费代言人。1940年代的一项研究发现,61%的好莱坞电影主角是有钱人,其中不乏顶级富豪,尽管实际人口中这样的人只占0.05%。事实上,20世纪初好莱坞电影中的人物大致属于一类“独特的中产阶级”,他们既没有经济鸿沟,也没有社会压力。有些电影中的女主角虽然是出身贫穷、境遇悲惨的年轻女孩,却穿着价值几千美元的衣服。“现代灰姑娘”类型的浪漫喜剧也在当时流行开来,此类叙事反映的是一种浪漫化的、阶级差异可被轻松逾越的社会想象。加卢佐认为,“电影不表现现实问题,而是‘让人们忘记现实的恶劣处境、忘记日常的烦恼,活在美丽的想象世界中’。”
从20世纪初开始,商人就意识到了电影在商品营销方面的潜力,有观察者认为,好莱坞之所以偏爱现代题材的电影,是因为它们更便于植入广告,很多时候场景设计就是为了给商品提供出镜机会,这些被商品渗透的场景包括时尚沙龙、百货商场、美容院,或是拥有现代化厨房、浴室和大客厅的上流人家。自然,能够出现在这些场景中的往往是富裕阶层的角色。

商业与电影的共生关系在时装行业尤为显著。早在1930年代,梅西百货这样的百货公司就会在电影上映前一年打听到明星在电影中穿的衣服,并制作仿制品,等到电影上映后第一时间出售。加卢佐指出,展示奢靡的高消费世界是电影的核心,明星则是沟通市场和观众/消费者的媒介,电影吸引观众陶醉在消费体验的白日梦中,提供一种梦幻的自我投射体验。
整个20世纪下半叶,从生产者社会转向消费者社会的时代转向意义深远,不仅在于它重塑了消费相关行为,还在于它将财富置于了一种近乎崇高的、引人膜拜的地位。齐格蒙特·鲍曼援引杰里米·希布鲁克(Jeremy Seabrook)的观点指出,当今社会依赖于“制造人为的、主观的不满足感”。于是人们切实拥有的东西在奢侈消费面前黯然失色,“富人成为被普遍崇拜的对象。”鲍曼注意到,富人崇拜本身也随着时间流逝出现了微妙的差异:曾经被大众崇拜的是“白手起家”的创业英雄,他们遵循严格的工作伦理并因此得到物质回报和社会尊重;但现在大众崇拜的是财富本身,是财富所允诺的奢侈梦幻的生活,富人获得普遍崇拜的原因不再是他们的经济成就,而是他们对消费美学的把握。
富人崇拜的趋势愈演愈烈。自撒切尔和里根上台,放松管制、鼓励自由放任经济增长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逐渐席卷全球。在以英美为首的许多西方国家,以福利国家改良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系逐渐瓦解,工作稳定性不断降低,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鲍曼指出,越来越多的人挣扎在贫困线上或可能坠入贫困,而富人却越来越富有,这一严峻现实导致了如下社会心态,“穷人越是贫穷,展现在他们面前的生活模式就越高高在上,越匪夷所思,令他们崇拜、觊觎,渴望模仿。”

在另一方面,随着福利国家的瓦解,穷人也显得越来越可疑可鄙。为了减少福利支出,国家开始用选择性保障取代普遍性保障,将社会福利局限于通过了经济审查的穷人。在鲍曼看来,此举导致社会立即被一种二元论撕裂:付出而没有得到任何回报的人和不付出就能有所得的人。于是,不被允许平等享用社会福利的中产阶级既不再对继续支持福利保障感兴趣,又开始对必须依赖社会福利的经济弱势群体心生怨愤与猜忌。
Quartz的一篇评论文章指出,近二三十年来,英美电视节目充斥着对劳工阶层的(无意识)偏见。一个针对劳工阶层的典型刻板印象是:他们整日看电视、吃不健康的快餐、酗酒、赌博、打架,而中产阶级则在努力学习、参观博物馆、享用高级美酒、去高端餐厅吃饭、培养出阅读量很大且能说会道的孩子。文章作者发现,近年来英国电视台开始流行播出一类“窥视英国穷人生活”的节目,比如2013年在BBC播出的纪录片《尼克与玛格丽特:我们支付了你的福利》(Nick & Margaret: We All Pay Your Benefits),片中中产“纳税人”被邀请走进福利家庭,评价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购物习惯。美国也有不少同类节目,比如在TLC播出的《甜心波波来啦》(Here Comes Honey Boo Boo)。这部真人秀关注的是一户姓汤普森的农村白人工人阶级家庭,这个家里的男女主人超重,且痴迷于让他们的孩子参加选美比赛。

“这些节目的核心是展示一种‘我们对比他们’的心态,鼓励占据社会主体的中产阶级成员批评不配得到支持的穷人……(劳工阶层的)人们变成了社会中一个统一的、让人困扰的群体,他们之中无论是显著差异还是细微差异都已不被关注。这些真人秀节目将工人阶级社区描绘成完全缺乏价值和重要性。”
与此同时,电视剧中的人物不再被真正的经济焦虑所困扰成为了一个明显趋势。上述Quartz文章援引《纽约时报》评论人Wesley Morris2016年一篇评论中的观点指出,在过去十年间,
“现实生活中的人失业、变穷,但电视剧中的人变得更富裕了,而且他们的工作似乎和经济越来越无关……近年来,电视剧致力于描绘一种另类的无阶级社会,医生、警察和律师都住在差不多的、装修精美的房子里,而工人阶级社区持续隐身。”
富裕阶层的审美取向和生活方式不仅改变了影视剧中的角色认同,还渗入了人们自觉参与的文化生产——社交网络。美国作家阿莉莎·夸特(Alissa Quart)援引一项分析来自曼哈顿的7442454张Instagram公开照片的研究指出,无论拍摄者自身的社会阶级地位如何、家庭住址在哪,他们发布的Instagram照片大部分都集中在相对富裕的区域。该研究的负责人列夫·马诺维奇(Lev Manovich)告诉夸特,Instagram等平台的用户自发地精通如何拍出透露“经济和社会特权”气息的照片——极简主义成为标志性的Instagram风格,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极简主义曾是特权阶层的审美。

我们每个人或许都有这种感觉:在社交网络上看别人的生活往往光鲜亮丽,自己也倾向于在社交网络上晒出生活中的“高光时刻”。研究者发现,在社交媒体信息中提升和夸大自己的社会地位,的确是一种普遍现象,这亦从侧面反映了我们时代的富人崇拜。
中产阶级的幻想与现实
劳工阶层的“结构性缺席”与富人崇拜,就等于中产价值观吗?在欧美影视剧的语境内,身为社会主流的中产本身的存在感也在变弱。如前文所述,阶级在一些影视剧中被抹平,理论上从事典型中产工作的角色在屏幕中过着的却是比真实中产优越得多的生活。
在夸特看来,美国观众偏爱的与其说是“中产”节目,不如说是“1%社会顶层”节目。在这类描述社会顶层生活的电视剧中,主角要么是野心勃勃、没有道德准则、为了成功不折手段的反派英雄,比如《绝命毒师》(Breaking Bad)中成为制毒专家的高中化学老师;要么是时尚大师、品牌专家、投资人或莫名有好出身的人。她注意到,“1%社会顶层”电视节目从2004年唐纳德·特朗普的真人秀《飞黄腾达》(The Apprentice)开始真正火起来。

夸特苦涩地承认,她自己也和许许多多美国人一样,将观看此类电视节目当作止痛药,来暂时遗忘不堪重负的现实中产生活。剧中描绘的巨额财富、奢侈生活仿佛脱离了财富创造的经济与社会基础,成为了一种毋庸置疑的、让人沉溺其中的超然存在。夸特曾痴迷于描述英国贵族生活的历史剧《唐顿庄园》(Downton Abbey),“演员们身着长外衣和天鹅绒烧花连衣裙梦幻登场,让我忘却了身体上的不适和对未来的迷茫。经济贫困的刺痛让我沉迷于这些真切反映20世纪初英国贵族生活的华丽景象。”《唐顿庄园》的大结局吸引了960万美国观众,但夸特也留意到,这部剧与1970年代同样讲述贵族生活故事的英剧《楼上楼下》(Upstairs, Downstairs)在角色认同上几乎截然相反:前者中的贵族往往是善良的,仆人多是邪恶或不守规矩的;而后者显然将关注点偏向“楼下”坦诚友好的女仆和厨子。
在影视剧中放纵幻想的中产所真实面对的是日益惨淡的现实。自1980年代以来,全球的收入不平等现象都在加剧。2018年的一项研究显示,截至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前的40年间,美国中产阶级的资本净值几乎完全来自持有的房产的升值,工资并无显著增加,而最富裕的1%的人群依靠股票等资本投资迅速积累大量财富。1970年代,英国最富裕的1%的人群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5%,2008年前夕上升至15%。美国社会学家厄尔·怀松(Earl Wysong)、罗伯特·佩卢奇(Robert Perrucci)和大卫·赖特(David Wright)在合著的《新阶级社会》一书中甚至提出,传统意义上的阶级划分(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已经失效,被一个双钻石型的阶级结构所取代:这个结构由特权阶级(占20%人口)和新工人阶级(80%的人口)组成,顶层和底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巨大,且两大阶级之间向上流动的机会非常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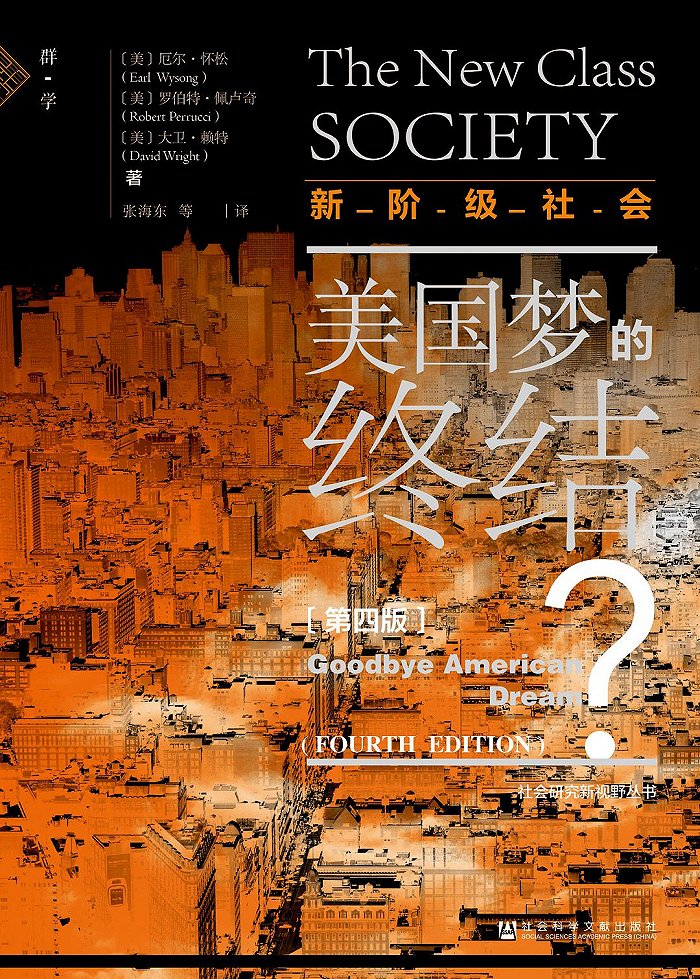
[美]厄尔·怀松 等著 张海东 等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07
夸特认为,如果说拥有反派英雄主角的“1%社会顶层”节目反映了某种中产价值观,那可能是对失去生活稳定性心怀愤懑的中产阶级的“复仇幻想”。夸特援引《绝命毒师》时期ABC电视台节目总监克里斯蒂娜·韦恩(Christina Wayne)的观点指出,《绝命毒师》首播于2008年,在2009年经济衰退到低谷的时候走红,“那时人们看到了金融界对美国的所作所为,看到华尔街的人越来越富有,人们想要看到他们的英雄让这些人付出代价。”在《绝命毒师》《黑钱胜地》(Ozark)等电视剧中,反派英雄可能很富有,但依然对超级富豪实施了复仇行动。另外,看到这些身居社会顶层的反派英雄掌握滔天财富,为所欲为,像神一样不必考虑行动后果,也可以说是观众对无力现实的“反叛”。
电视评论家Joanna Weiss在《政客杂志》(Politico Magazine)刊文指出,虽然当下美国是一个电视的黄金时代——各种电视网络、流媒体平台不断推出大量电视节目——但当下美国也进入了又一个文化意义上的镀金时代,鉴于惊人的经济不平等、收入增长停滞,如今本应是我们对讲述美国中产挣扎故事双倍下注的时刻,但事实却是,虽然许多社会议题能在电视中得到曝光和讨论,经济议题却常常被搁置一旁。夸特认为,“1%社会顶层”节目的流行反映了一种普遍社会心态,即我们会为陷入困境而自责,却不会去指责体制的失败。讨论导致社会不平等的原因或如何建立一个人人都能过上体面生活的社会,已不再时兴。
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新自由主义“去政治化”的时代精神使然。1970年代中期石油危机让欧美国家面临经济增长停滞的威胁,右翼政治力量适时地提出“新自由主义”,让人们相信资本主义痼疾的药方是更多的资本主义——减少市场监管促进自由竞争,强调个人责任和适者生存。至于传统意义上希望改写社会规则、持续改善社会的左翼/自由派则未能有效地回应这一时代趋势,如哥伦比亚大学人文学科教授马克·里拉(Mark Lilla)所言,从越战时期的新左派运动开始,自由主义政治放弃了建设共享的政治文化,转而沉溺于“文化政治”,强调性别、种族、性取向等身份对个体的压迫,而疏于分析阶级如何随着新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这或许解释了Weiss所说的社会议题往往能在电视中得到曝光和讨论,除了(最重要的)经济议题。
尾声:“中产”在中国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西方中产陷入衰落的同时中国因融入经济全球化而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期,为融入全球经济结构所必须进行的意识形态调整包括吸纳“无限扩张”的增长逻辑、接受商业社会对个体解放和社会流动的促进作用、将促进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把物质财富当作地位标识等等,中国人的生命经验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与发达国家同社会阶层的人趋同。
在此过程中,中国产生了自己的中产阶级群体,然而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具有权利意识和公民自觉的自为阶层(class for itself),而不仅仅只是一个自在阶层(class in itself),值得商榷。根据《学做工》和《中国走进现代》作者、英国社会学家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的观察,中国和英国的情况迥异,公众意识中阶级的存在感并不强烈,与“阶级”相比,用地域、城市化程度、家庭背景、教育水平等维度去区分不同群体或许更加有效。

比中产阶级更稳妥、更有确定性的群体身份应该是中等收入群体——根据2022年5月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数据,目前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超过4亿。截至2021年,中国总人口超过14亿。
假设具备一定消费能力、教育和认识水平(特别是公共关怀)的中产(或中间群体)是当下中国主要的文化生产者和消费者,那么他们应当也是公共舆论场中的主要发声者。
理想状态下的影视剧应当是反映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身处境——作为一种生动的、具有强烈戏剧性的文化媒介,影视剧潜在的社会动员力量是强大的。无论身处何地,具有社会关怀意识的电视人、电影人恐怕都会面对某种外部结构性力量的制约,当下影视剧底层失语、嫌贫爱富即为表征之一。但这种限制我们正视社会主要矛盾的外部结构性力量究竟是什么,恐怕不同的社会情况不同,也并非我们简单地用“中产文化”这一简单化的理论工具就能解释得清的。
参考资料:
【法】安东尼·加卢佐.《制造消费者:消费主义全球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22.
【美】马克·里拉.《分裂的美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英】齐格蒙特·鲍曼.《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1.
【美】阿莉莎·夸特.《夹缝生存:不堪重负的中产家庭》.海南出版社.2021.
【以色列】纳达夫·埃亚尔.《逆流年代:来自反全球化运动一线的报道》.湖南文艺出版社.2021.
【美】厄尔·怀松,【美】罗伯特·佩卢奇,【美】大卫·赖特.《新阶级社会:美国梦的终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TV Demonizes the Working Class, Two New Shows Finally Celebrate Them,” Quartz, April 11, 2018.
“Why Won’t TV Show People Who Aren’t Rich?” Politico Magazine, November 12, 2017.
https://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7/11/12/tv-shows-economic-diversity-215818/
《王梆×淡豹×黄月:我们如何保护自己》,单读
https://mp.weixin.qq.com/s/nPKI57Tig0Ujdx8XiL-HTQ
《【专访】<学做工>作者保罗·威利斯:中国年轻人正被物质秩序和文化秩序的同步变化深刻影响和塑造》,界面文化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