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2期主持人 | 潘文捷
近期,湘雅二院医生刘翔峰事件成为热门。人民日报“侠客岛”公众号的文章指出,刘翔峰受到的指控有“有异物一律按肿瘤治疗”“开最贵的药”“切开患者正常肠管”“使用其他病人的结石、血液来冒充自己手术的病人”……举报者涉及刘翔峰带的研究生、同事和患者家属。目前,医院已经通报初步调查发现,称其“在医疗过程中存在不规范行为”,免去其职位。后续湖南省卫健委网站消息,经初步调查,发现刘翔峰涉嫌严重违法。
该事件发生后,不少患者在社交平台发布消息,称自己曾经遇到过怎样类似的“魔鬼医生”,为赚钱不择手段,给自己及家人造成了怎样的伤害;也有不少医生在“自证清白”,称不要因为一个人而否定一个职业,还是有很多好医生在坚守岗位。

作为一种职业,医生当然也有医生的苦恼与重担。在“人物”公众号刊出的《越来越多年轻人被送进ICU,一位急诊科医生的忠告》一文中,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医师卢骁谈到,急诊监护室在负责抢救工作时,每五天要上一次24小时的班,第一天早上8点上班,第二天到中午才下班。有时候轮夜班,下了夜班也睡不着,这种作息对身体的伤害很大。“医生自己也有心梗的、糖尿病的,还有颈椎病,腰间盘突出什么的,因为很多操作都是趴着去做的。”除了身体上的压力,医生的精神压力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医生基本上是对错误零容忍的一个职业,当然你不可能不犯错,但是你会告诉自己不能犯错误,特别是急诊科,一旦犯了错误,可能就是一条人命啊,很严重。”
在 《医事:关于医的隐情和智慧》一书中,作者讴歌谈到,在一次骨科读片会上,她目睹了一个城市的200多位骨科医生在讨论一个病例。病人是一位股骨头缺血坏死的老人,需要做人工髋关节置换,但老人家里一贫如洗。医生为他向厂家争取,免费换了一个国产的人工髋关节。一年后,病人觉得髋部疼且活动困难。尽管可能有多重因素,但家属一口咬定是医生的责任,要求给老人免费做第二次翻修术,医务科也判定为医生的责任。当事医生感慨:“做好人未必有好报,除非你能坚持一辈子做好人,不计后果,无怨无悔。”
有过作为病患寻求医生帮助经历的我们,是如何审视自己与医生之间的关系的?我们要如何理解当下的医患关系?又可以依靠怎样的理解或沟通促进医患关系的改善?

病人和医生的关系如同顾客和理发师
叶青:从开的药里就能感受到这个医生是“好”还是“坏”。碰到过非常好的医生,详细地跟我解释开的方子里,哪些药在医院拿,哪些药去外面药店买,因为药店更便宜,药到病除之余还照顾了我的钱包。也遇到过可能不那么好的医生,我明明是去看胃,在没有做任何检查的情况下,这位医生断定是我是胆出了问题,给我开了四大盒益胆片,虽然心中充满了疑惑,但秉持着相信医生的态度,我还是乖乖开了药回家服用,结果不但症状没有得到缓解,还因为药物副作用疯狂腹泻,停药之后才好。当然不是说都要像前者一样完全从患者利益出发的才是好医生,我支持医生赚钱,也理解他们可能有所谓的“指标”,但总要坚守“对症下药”的底线吧。
徐鲁青:说起开药,我就会想到病历本上医生的字迹,一直很纳闷为什么所有医生写的字都很难看懂,像是医学院开过必修课一样。这些抽象的字迹放大了医患间本来就存在的专业壁垒,病人的问题大多只得到医生的口头澄清,至于病历本上写的是什么病,电脑上选了什么药,几乎都摸不着头脑,而一头雾水的病人只能乖乖为所有的药付钱。不过好像慢慢有医院开始改变了,前几天我去一家综合医院,发现病历本记录已经变成电子打印的,大大提升了就医体验,因为可以根据病历询问医生更具体的情况,回来之后也能根据关键词自己搜索更多信息。
林子人:我其实很怕去医院看病,小时候是怕打针,现在则是害怕在医生面前手足无措——如果我描述不清楚我的症状怎么办?如果我听不懂医生的诊断怎么办?在英国社会学家哈里·柯林斯(Harry Collins)和特雷弗·平奇(Trevor Pinch)合著的《勾勒姆医生:如何理解医学》一书中,两位作者指出,医疗咨询的本质是与专家打交道,但因为只有患者本人才最清楚TA的身体症状和治疗效果,医患之间的关系很像是去理发店,你需要不断和医生沟通,讨论合适的“处理方法”,在医学专业技能和病人自我诊断技能之间取得平衡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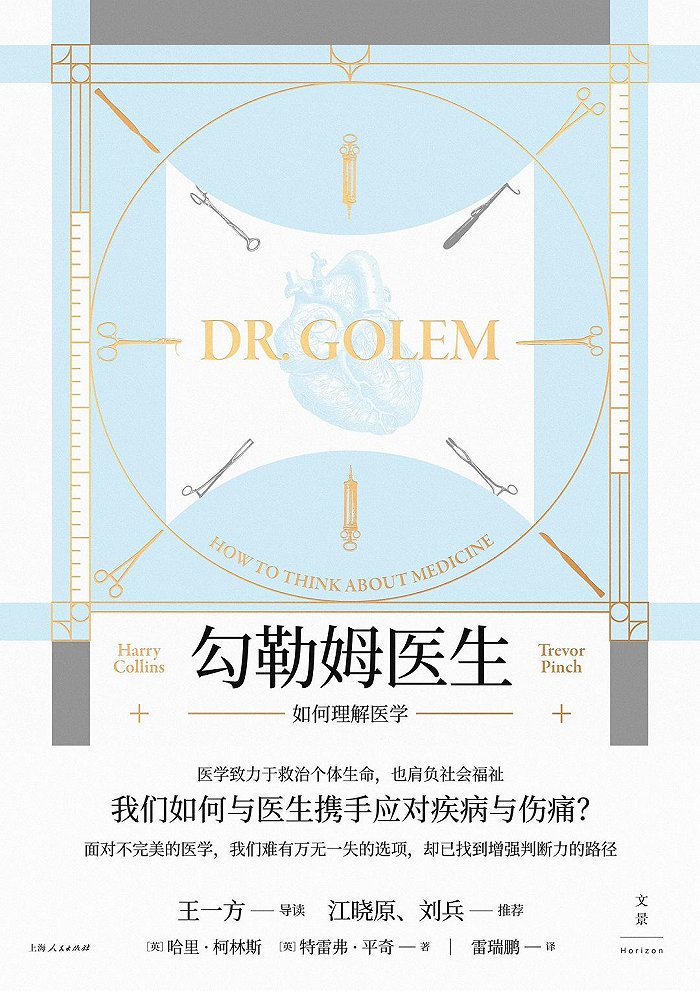
[英] 哈里·柯林斯 著 雷瑞鹏 译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2
随着医学的发展,一个略显讽刺的事实是,非医学专业的人或许是有史以来在医生面前最“弱势”的病人。在现代医学出现之前,病人和医生的关系的确就像是顾客和理发师的关系一样,顾客也许不能自己剪头发,但至少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柯林斯和平奇认为,随着尸检、听诊器等需要经过训练才能掌握的医学技术出现,病人逐渐被排除在日益专业化的医学话语之外,这一趋势在二战后的十年抵达顶峰,彼时科学的权威性高得几乎不容置疑。但从1960年代开始,“对医学的批评和对科学本质逐渐成熟的理解,一定程度上磨圆了医学骄傲自大的棱角。”但无论如何,一名好医生一定还是善于倾听病人的。之前界面文化采访了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胸外科主治医师王兴,他认为,比较合理的医疗模式是医生在给出方案后表明一些倾向性,但医生也要尊重和照顾病人的顾虑和特殊需求。
尹清露:“好医生应该对症下药”让我想起读初中时治胃病的经历,当时医生只诊断为胃溃疡,并没有细究其中的缘由,开出的药也没多少效果。后来我才发现自己可能属于“情绪性胃痛”,跟学习压力和不安情绪有很大关系,那名百思不得其解的医生之所以“开错药”,估计也是出于无奈,倒不是为了吃回扣或者医德欠佳。然而,这件事可能也提出了重要的一点:在治疗疾病尤其是慢性病时,好的医生应该注意到病人本身的在场,而不只是看到表面的病理症状。
法医病理学家葛文·阿德希德写到过一则1949年的案例,在为一名妇女做手术时,外科医生预见到怀孕对她来说有临床危险,未经她的同意实施了结扎,虽然这是基于“事实”做出的判断,但是他没有和病人充分交流、没有考虑到病人对自己身体的看法。我在读医学人类学家凯博文的《照护:哈佛医师和阿尔茨海默病妻子的十年》时,也曾感动于他对照料慢性病人的理解,比如照护应该超出简单的诊断范畴,意味着平等分享生活中的苦难,让病人也能积极参与进治疗过程之中。我觉得,这种相互的医患关系也有助于一定程度上解决纠纷问题,毕竟现在的情况是,由于病人只能单方面地依赖于医生、相信医生的专业性判断,一旦治疗出现问题,脆弱的依赖就很容易变成指责,即使是认真负责的医生也可能成为众矢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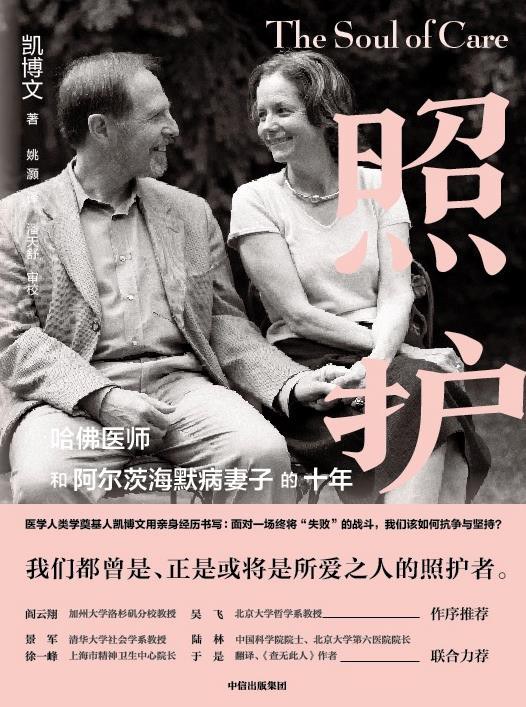
[美] 凯博文 著 姚灏 译
中信出版社 2020年
这并不能只责怪医生群体,凯博文指出,在高强度的工作环境下,与患者保持职业距离对于医生来说是一种自我保护;而如今的医患关系的不平等也是制度化的(就像子人所说的,病人被排除在医学话语之外),所以上述的“照护”能做到多少往往要看病人的“努力”,像是找人牵线熟识的医生(以前生病了,家里人的第一反应都是打电话托关系),来争取到更短的排号时间,以及医生额外的关心,在医院里随处可见对医生毕恭毕敬的病人,想必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外科医生自传《刀锋人生》也颠覆过我对“好医生”的判断标准,有胆量做心脏手术的医生反而会有一些“人格缺陷”,比如冷酷无情和自恋,唯其如此才能保持稳定的心态。慢性病医生需要漫长的耐心来逐渐抵达病灶,外科医生则更需要手起刀落和胆大心细。疾病是动态的、多种多样的,一名好医生所拥有的特质也要视情况而定吧。

[英] 斯蒂芬·韦斯塔比 著 高天羽 译
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
医患只能通过更友好高效的交流解决可能的矛盾
潘文捷:在《病患悖论》一书里,英国格拉斯哥的全科医生玛格丽特·麦卡特尼(Margaret McCartney)看到,健康的最大影响因素并不是医疗,而是经济条件、膳食水平、生活压力和工作环境,但在当下社会,过度包装的医疗使得越来越多的健康人变成了“病人”,而大量的医生和其他医疗资源也投入到了要求身体健康、毫无症状的人接受筛查和诊断上了。
刘翔峰事件中的很多指控便是过度医疗引申出来的问题,在一些指控中,他“有异物一律按肿瘤治疗”,没有病也找出病来治,就像麦卡特尼说的,“我们的目标不再是让患者好转,而是找到健康人群身上现有或潜在的疾病风险,即使他们身体状况良好、一点儿都不觉得难受。不是只有遭遇现实的身体或精神病痛,比如发现身上长了一个令人担忧的肿块或需要调整糖尿病用药时,人们才需要请全科医生的吗?”
林子人:医患关系紧张是一个长期的社会问题,王兴医生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也聊到了如何改善医患关系。他认为,在我们暂时无法解决医疗资源紧张这一现实问题的前提下,病人了解医生的工作逻辑、医生适当增加问诊时间能建立一种更好的医患关系。从病人角度来说,需要理解医生的工作模式,比如门诊是一个把情况更紧急、需要深度诊断治疗的病人筛选出来的部门,门诊医生因此倾向于以“是/不是”的收拢式问答快速做判断,病人在门诊提出的问题也可以偏收拢型。而对医生来说,适当增加问诊时间,更细致仔细地阅读医疗报告,给病人留下“很懂很用心”的印象,有助于提升病人的信任感和配合度。
潘文捷:子人在前面谈到,在二战后的十年,科学的权威性高得几乎不容置疑。当时医生的权力也达到了巅峰。《病床边的陌生人》一书也记载了这样的历史:二战后,美国科研人员在医学实验室取得了耀眼的成果——一系列抗生素,其中一种可以治愈结核病;多种治疗心脏疾病的药物;科学家对肝炎也有了新的认识。在这些可喜可贺的实验成果背后,是那些没有真正获悉实验真相的受试者。那些有智力障碍的、收容在押的、年迈糊涂的、酒精上瘾的、家徒四壁的边缘人,成为了为科学进步牺牲的人体试验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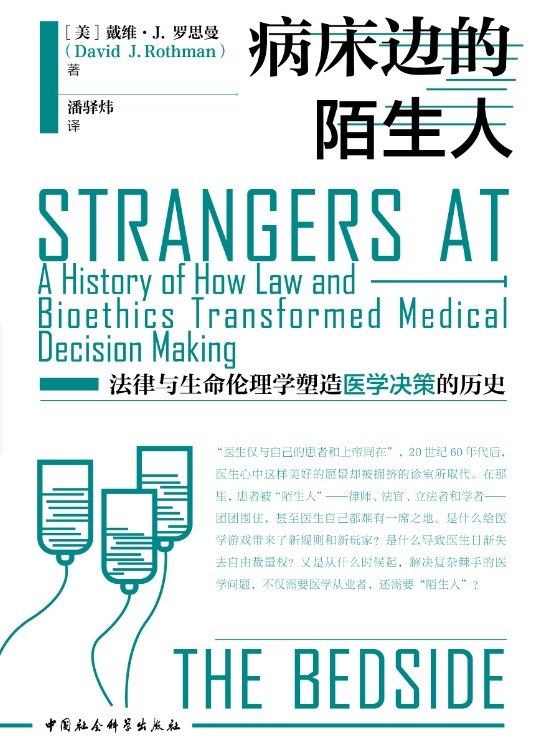
[美]戴维·J.罗思曼(David J. Rothman) 著 潘驿炜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年
在这种背景之下,新闻记者、哲学家、法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开始呼吁法律和生命伦理学介入医学之中。如果说过去医学决策的做出是在双方互相信赖的基础上,医生凭着自己的专业知识、职业道德,来给患者选定治疗方案,那么,新来的这些人物是在改变医患的天平,推动了医学决策的规范化,并确保患者在医学决策中的权利。
但是新的问题也可能随之产生——在双方信息非常不对等的情况下,“知情同意”可能流于形式;随着患者决策权的提高,患者对医生的尊重程度不如以前高,形成医学领域的消费主义。我们今天谈的医患关系,其实是在这样的一个新的背景之下形成的。
姜妍:良好的医患关系首先对医患双方都有要求,其次是医患所处的大环境、大背景一样会对关系的营造产生影响,可以说里面的环节多且复杂。比如作为学习现代医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西医)的学生,在入学时的第一课很多都是宣读希波克拉底医学誓言,那个誓言是很动人的,如果每个医生、医学生能够在学习和从业者日日温习,我觉得医德层面上的问题可能会大量减少。这是需要学校教育、医院体系,有时候还有师承教育共同作用的结果。
国医大师柴嵩岩常说“心不如佛者,不可为医;术不如仙者,不可为医”,我很欣赏的中医大夫孔令言当年跟随沙凤桐沙老学习的时候,入门第一天老师就说“本事可以学得不好,医德一点儿也不能欠缺,你学的玩意儿我可以慢慢教,你敢缺德我可收拾你”。学习期间沙老对他要求也是非常严格,医案上一个字写错就要整张重写,因为“你一句错,病人后半辈子就错了,你不知道,老天爷可知道”。医生这个职业有其特殊性,因为中间横着健康与生死,所以确实对从业者的要求会比许多其他行业更高,也需要从业者带有一些使命感和情怀。
反过来,作为患者,我们也需要给予医生一定的理解和支持,比如在就诊前是不是可以自己提前做好各种准备,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医疗建立一些基本常识,尽量节约就诊的时间,在回答医生问题的时候能够准确直接,而不是来来回回绕圈子。我们每个成年人才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疾病的产生很多时候也不是突然发生的,如果日常生活里不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一直放纵自己的欲望,生病后一味去要求医生,好像也说不过去。
徐鲁青:因为存在着专业知识上的不对等,医患之间的关系注定很难平等,只能通过更友好高效的交流解决可能的矛盾。哈佛大学教授Wendy Levinson曾经研究过大量医患法律纠纷,发现案例中有两个共性:一个是从未被告的医生同患者交流的时间比有过法律纠纷的医生平均多三分钟(前者为18.3分钟,后者为15分钟),二是未发生过医患矛盾的医生通常使用指导性语言,而不是用命令的口气说话,但医疗体制留给医生可以匀给每个患者的时间很少,于是总是会产生不满与误解。
另一方面,为患者提供更多了解医学信息的渠道也很重要,美国医生杰克·温伯格就主张推动赋予患者信息权,他提出使用统计图解释病情,而不是数字。他也建议在医院建立决策辅导员制度,帮助患者最自身病情有更充分的了解(当然,这个制度需要花不少钱,现在只有顶级医院配备,但从中可以看到让患者充分了解信息有多重要)。社会层面的医学科普更不可或缺,完善的科普渠道可以避免医疗资源挤兑,也能减少医患之间的沟通成本。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