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编辑 | 黄月
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认为,如果不了解瓦尔特·本雅明的生平,要理解他的思想几乎是不可能的。毕竟本雅明以其“思想图像”式的文本著称,而它们往往并非基于线性叙事,在跨学科研究流行起来之前,就已经超越了学科之间的疆界,变成纷繁散落的点点星群。
于近日译介出版的《本雅明传》由资深本雅明研究者艾兰和詹宁斯撰写,填补了本雅明日常生活和思想之间的空白——即便如此,就如伦敦政经学院的书评文章所言,本雅明本人仍然是神秘、难以捉摸的。他的好友肖勒姆在书中引用的日记中写道:
他要求每个人都看到他,虽然他在隐藏自己。可以肯定,从老子以来就没有人这样生活过。……在瓦尔特身上,有某种东西是无边的,超越一切秩序的。事实上,这样一种全然匿名的品质,使瓦尔特的作品正当化。
日前,在“本雅明与布尔乔亚世纪的终末”学术工作坊暨《本雅明传》新书研讨会上,多位中文世界的本雅明研究者从本雅明和其他学者的隐秘联系出发,共同探讨了这位“不可捉摸之人”的思想脉络,它们指向同一个关切,也就是“布尔乔亚文明如何终末”。

01 不仅关于本雅明

《本雅明传》对传主的一生做出了全景式描述,布满了本雅明和友人们密切来往的细节,以及随处可拾的思想断片,对读者而言可能是一阵晕眩的阅读感受。该书译者、美国布兰代斯大学副教授王璞在后记中说,“真的有必要知道这么多吗?我真的需要了解,儿童本雅明最初的性幻想来自一个穿水手服的妓女吗?”随着翻译的深入,他意识到,细节可以勾连出无边的历史真理,这正是评传的意义所在。
在工作坊上,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学者赵文提到,从本雅明的社会交往史可以看出,他本人是一个“在关系中存在的、非常独特的思想者”。虽然被贴上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标签,但事实上,本雅明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理论家们一直保持着较为松散的关系,“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是现代主义认识论之下的探索者,那么本雅明则对古典的犹太认识论拥有持续的热情。”赵文在这里使用了一个数学的比喻——现代政治论讨往往是在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建立直接联系,然而,本雅明想要寻找的是一种在这之外的、更为复杂的函数关系。
在《德国悲剧的起源》中,本雅明引用歌德的话说:“我们若想借学问获得整体,就务必将学问理解为艺术。”赵文认为,歌德的古典认识论提出了一个观点,要以艺术的方式回到事物本身,在事物中“呈现不可呈现的关系性经验”。所以《本雅明传》揭示了本雅明的思想发展——既是和同时代思想家们拉开距离的过程,也是和现代世界中广泛堆积的事物产生关系的过程。

上海文艺出版社·艺文志eons 2022-07
1929年见证了本雅明的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崛起。在本雅明的左翼转向中,就体现出了赵文所说的“在关系中的存在”和来自友人的影响。正如《本雅明传》中所写,这种“越来越浓的马克思主义腔调”既归功于本雅明的前苏联情人阿西娅·拉西斯的影响——阿西娅带他见识了革命无产阶级作家的多次会议,又缘于和阿多诺、布莱希特等思想家的交往,自此以后:
激进的左翼政治、自由取材于犹太教和基督教教理的多宗混同的神学关切、在德国哲学传统方面的深湛知识,以及一种足以处理疾速变化的现代环境中的研究对象的多样性的文化理论——这四者的结合将塑造他此后的工作。
本雅明的中文译者、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学者张旭东也提出,阅读本雅明会发现,我们打开的并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思想史。本雅明在中文世界很受欢迎,“不管是保守派还是激进派,文艺范儿还是所谓的哲学深度,大家都喜欢他,”但是如果要真正理解这位思想家,还需要去读本雅明读过的东西。张旭东提出,鲁迅研究也存在这个问题,“既然鲁迅读过达尔文和尼采,我们为什么不也去读一下达尔文和尼采呢?”
02 与马克思的相遇
张旭东认为,在本雅明和众多思想家的相遇之中,他与马克思的相遇是最为意义重大的转折点,马克思的文本成为了本雅明的理论基础之一。“本雅明归根结底是次一级的作家,不是说他不重要,而是说他不可能超越历史的地平线。”他发现中文世界经常会忽略一点,即资本并不只是经济意义上的商品或者剥削后的剩余价值,而是一种社会关系,一旦从抽象的社会关系领域转移到审美领域,就是本雅明可以发力的地方。
本雅明出生于1892年德国柏林的一个富商家庭,从小就被各种精致的商品物包围着:奢华的瓷器、吊灯,还有雕刻精美的玄关桌。张旭东提到,本雅明是布尔乔亚文明下成长起来的花朵,却也是反抗布尔乔亚的逆子,为了“从资本主义的世界中苏醒过来”,本雅明在马克思哲学中找到了出路,“第二自然”这一中介概念连接起了从马克思走向本雅明的通路。
“第一自然是一般意义上的大自然,第二自然就是社会意义上训练出来的自然。(就像是)我们觉得上班挣工资很自然,还以为这是非人工的、无历史的事实,而这一点就是资本主义批判的前提之一。”通过界定人和自然的历史关系,马克思主义对本雅明的研究就起到了定位和定向的作用。
王璞接下来提出,“当我们谈论普遍的人权时,真正所指其实是布尔乔亚,”布尔乔亚们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第二自然,又把第二自然密闭为拱廊街漫步其中,震惊于拜物教之中”。

基于马克思主义这一“历史地平线”,本雅明对资产阶级做出了自己的解读。王璞说,他们在本雅明眼中“既是腐败的现代生活中的反英雄,又是波德莱尔笔下的现代主义英雄”,“既是经济理性人,又恰恰是良心、法权,和心中的道义”。
那么,既然布尔乔亚的形象如此复杂难解,“从资产阶级世界中醒来”这一命题又如何可能呢?张旭东援引齐泽克的话提醒我们,“要做黑格尔式的马克思,而不是马克思式的黑格尔”,我们不应该以马克思为名,认为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就是现成的答案、就能终结这场幻梦,而是要去延续在世界史上还未结束的、仍在展开的辩证运动,这才是具有生产力和批判性的。
03 灵韵消逝,迷梦难醒
在文化评论集《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 : 在文化工业时代哀悼“灵光”消逝》中,本雅明写道,随着复制时代的到来,摄影和电影技术使得艺术作品中独一无二的原真性和“灵韵”(aura)消失了。在会议中,几位发言人也就“灵韵的消失”展开了讨论,而这同样展现出本雅明的辩证法思考。

重庆出版社 2006
耶鲁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学者初金一提出一个问题:本雅明发现,从战争前线回来的士兵往往不知道怎么去讲述自己的经验,而这些经验明明是非常值得被讲述的。
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情况,是由于“我们交流经验的能力已经被剥夺了”。初金一援引本雅明的文章《讲故事的人》指出,本雅明出于对上述现象的忧虑,开始关注到俄国作家尼古拉·列斯科夫的作品。19世纪是欧洲现实主义小说成熟的时代,出现了托尔斯泰笔下的大型小说,也就是文字的艺术。列斯科夫却反其道而行之,转而用书面文字去模仿口头叙述,“如同一群人围坐在火堆旁边,去听远行后归乡的人讲故事。”在本雅明眼中,这种口口相传的艺术形式能够把经验和智慧传递下去,同时塑造出一种集体性,而这是基于个体化生产、大规模复制的现代小说所无法实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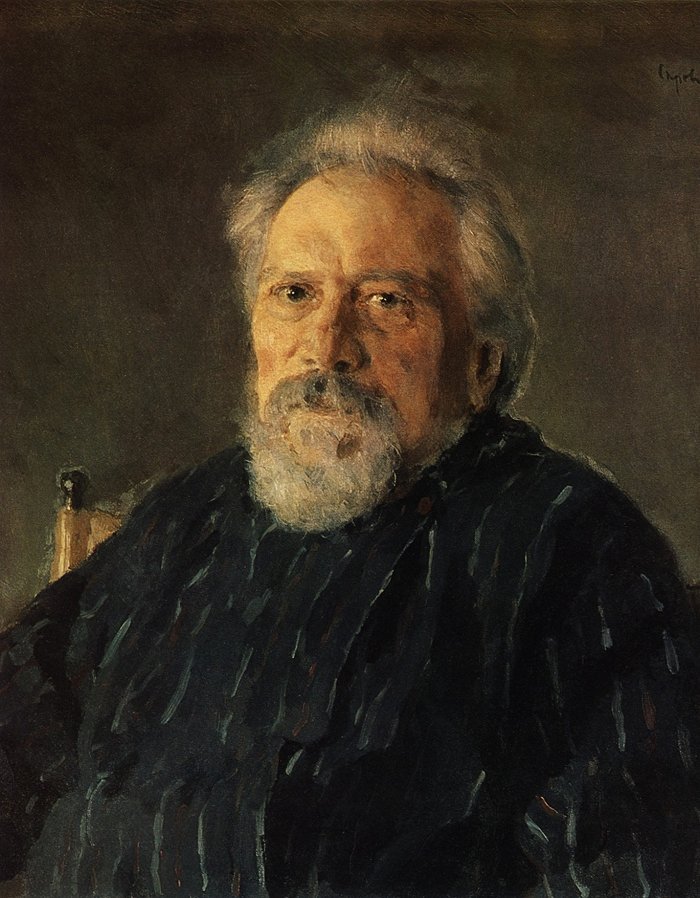
“本雅明对此有一个有趣的说法,他把讲故事的艺术比喻为陶工,陶匠把手上的痕迹留在器皿之上,每一件器皿都略有差别,就像每次转述故事都是唯一的,重点并不是故事本身,而是讲故事者的生命体验。”
初金一认为,故事被转述的次数越多,在故事中累计的生命经验也就越多,那么在讲述者和倾听者之间就产生了一种主体间的共鸣,这是一个具备灵韵的过程,是信息复制的过程所缺乏的。
看上去,本雅明对灵韵在艺术作品中的消失怀有十分悲观的怀旧情绪,但这并不是其思考的全部。就如张旭东所认为的,虽然本雅明力图寻找一种非布尔乔亚、前资本主义的思维方式,但他并不是将这些因素原封不动地拿过来,而是把这“层层的因素加入到当前的思想斗争里面”。
东京大学地域文化学者王钦回应认为,“用书写来模拟讲故事”其实是非常新颖的,它塑造出了一种全新的表达手段。王钦用赵树理的小说举例说明,它们的确是以小说形式呈现的,但是达到的效果却是本雅明所希望的“一方面动员群众、塑造集体性,一方面传达经验,带有讲述者个人的生活色彩”。原本处于对立位置的口语和书写,在列斯科夫的创作中被统一了起来。这不再只是风格和文体的问题,而是我们如何在今天应对先进的生产方式的问题。
初金一同样提出了存在于本雅明思想中的张力,虽然《讲故事的人》和《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都写到了灵韵的消逝,后者的口吻却比较乐观。这一点从书中便可得知,本雅明曾经在《机械》中写到,艺术品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价值根植于神学和礼仪,而当艺术创作的原真性标准失灵,艺术的社会功能就得到了改变,它不再基于礼仪,而是建立在另一种实践——即政治的根基之上,这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要如何解释这两种看似矛盾的观点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者汪尧翀认为,这一问题与本雅明如何思考“从资本主义中苏醒”或者“布尔乔亚的终末”有着深刻的关联。他首先提到了本雅明的学术同路人——格奥尔格·卢卡奇,在其著作《小说理论》中,卢卡奇把布尔乔亚文明设想为所谓的“骷髅地”,也就是传说中的耶稣受难地。在卢卡奇看来,布尔乔亚文明就是一个僵化和陌生化了的、如同骷髅般腐烂的内心世界。现代人创造了“第二自然”,却逐渐开始疏离于自身的创造物,从而造成了人的异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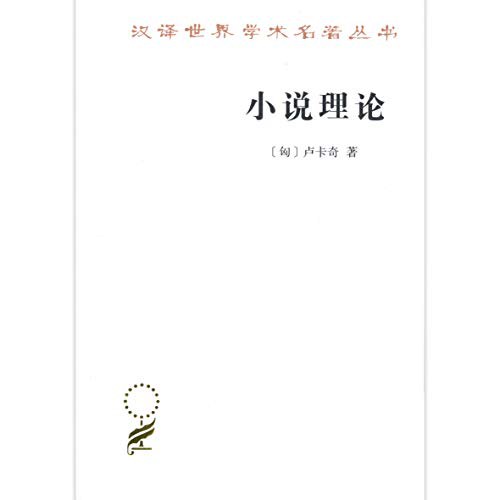
商务印书馆 2018-09
卢卡奇认为,这种异化带有谜语的特征,它是不可辨认、不可理解的,但是汪尧翀却指出:“本雅明认为这个谜语是可以得到解码的,哲学的任务就是要唤醒僵化的事物,从而激发出事物的世俗外壳中的拯救潜能,这就是所谓的世俗启迪。”
也就是说,即使是在被异化的人造物之中,也存在着转化的可能。《本雅明传》中写过一则例子,1927年底,本雅明答应参与一次药物迷醉实验,他首次尝试了大麻,并把大麻迷醉看做是一种既危险又充满魅力的研究形式。不过,本雅明追随的并不是感官错乱,而是理性本身的转化,在此,迷醉“松弛了推理的线索,造成一种必要的路线偏斜”,这也和《拱廊街计划》中的漫游者形象产生了关联——19世纪的漫步者就是这样被都市生活中的幻境所迷醉的。
王钦指出,或许问题根本不在于如何在一个灵韵消失的时代,重新达到对艺术作品灵韵式的接受方式,而在于如何看待布尔乔亚时代这样一个“没有终末论的终末”。他认为,放眼今天,在所谓的后现代时期,无论是灵韵式艺术作品时代还是电影所代表的复制时代,都已经被超越了。我们每天接触的媒体回应的也与以往不同,不再是关于叙事的渴望,而是生理性和本能的片刻欢愉,这不断地提出新的问题以及新的解决方案。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已饱受质疑,而在这之后,新的替代性方案也将像本雅明所言那样,逐渐变成需要解码的象征符号。
当然,今天的我们仍未从资本主义的迷梦中醒来,在发言结束时,张旭东援引了齐泽克的名言提出“现在,想象资本主义的终结要比想象世界的终结还要难”,不过,这也将成为我们不断阅读本雅明的动力,也是他的思考在今天仍然熠熠生辉的原因。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