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过去,亲历者将以何种语气讲述自己经历的一切?如果梦想在结束后重新又变得不可思议,梦想是否就已经一败涂地?如果相信的价值均告幻灭、一次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一代人将要如何面对“失败”的一生?这些或许是历史上的许多辈人都曾面对的问题。一部分人回望过去时的玫瑰色滤镜与另一部分人的其他色滤镜相碰撞,那画面既是河流的分叉、潮流的退却,也是在共同的经历中努力发掘出新的诠释与意义。
意大利理论物理学家卡洛·罗韦利(Carlo Rovelli)是《七堂极简物理课》《时间的秩序》等畅销科普作品的作者,他的特点不仅在于将物理、宇宙、量子力学写得动人,而且站在人文历史的视角上,为读者诠释我们所共同栖居的这个世界的真相。下面这篇《我和我朋友们的1977》节选自罗韦利今年推出中文版的《物理学家的智性冒险》,他回忆了青春岁月里一场“失败”的运动,“很快我们就尝到了幻灭的滋味。一些计划因为判断错误而被抛弃,更多的计划则是因为失败而被摒弃。我们理想的可能性就像阳光下的雪一样消融掉了。我们分道扬镳,在各自选定的路上走下去。”既然如此,“那么是否从一开始就不该有什么梦想?”答案是,不。
《我和我朋友们的1977》
撰文 | [意]卡洛·罗韦利 翻译 | 胡晓凯
最近我读了一些写四十年前那场席卷意大利的青年运动的文章,那是1977年,我和我的朋友们都是那场运动的亲历者,它就像暴风雨般迅猛而短暂。但大多数文章我都无法认同,里面写的好像不是我和我的朋友们多年前的所言所思所感。我不打算在这里做历史学或社会学分析,我也不想用我和朋友们的个人体验替代某种历史事实。但我知道,当年有许多人和我有同样的感觉,今天他们一定还在什么地方。我写这篇文章时心里想着他们,还有我当时的很多朋友,以及那些愿意听到另一个版本的,关于那个时期的叙述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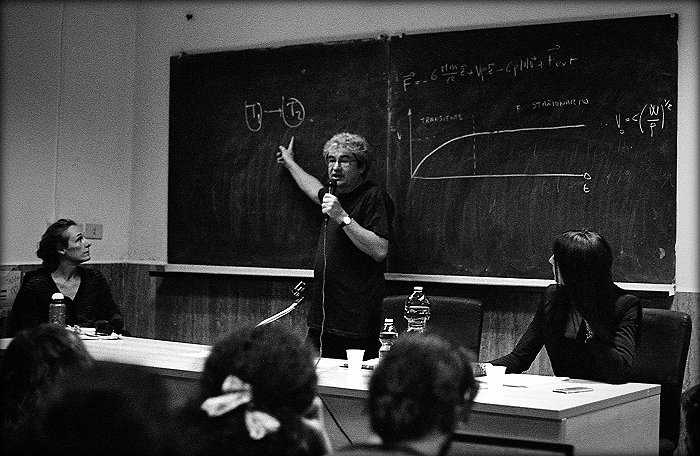
这些朋友中一些人会透过玫瑰色的滤镜回望那个似乎已是传说的时代。那是一个激烈对话的时刻,一个充满梦想、充满热情、呼唤变化、憧憬共同建立一个更好世界的时刻,现在回忆起来,他们还带着与当时同样强烈的怀旧情绪。相比之下,在那之后的人生就好像单调乏味多了。不过这绝不是我的感觉。我们当时二十多岁,正是大好年华,对生活的体验是带着浪漫色彩的,在回忆中尤其如此。那不是历史的芬芳,而是青春的芬芳。对我来说,那年发生的事件仍然是非同寻常的,甚至是奇妙的,因为它们开启了某种东西。我的面前出现了一条路。那之后的人生并没有显得更灰暗,因为我和大家一起发现了一道色谱,那些颜色至今还没有离开我。
尽管这样说,但1977年之后的那一年对许多亲历者而言无疑是一场溃败。我们热切地渴望改变世界,这似乎一度是完全可能的,但却在严酷的现实前触礁。先是政府的暴力制止,当时我们称之为镇压,接着发生了我们今天称为恐怖主义的暴力行为。当时我们许多人都认为在意大利做“武装斗争”不会有任何结果,它不过是一种极端和愚蠢的反应,是已经失败了的梦想在孤注一掷。我们很多人都知道,那些“叛逆的同志”是一些比同龄人有更加绝对的道德感的青年男女,因此也更容易被道德感蒙蔽,很不幸,历史经常如此。我们想要一些不同的东西,有一个短暂的时刻,和许多人一样,我们都认为变化就要降临;往那个方向前进是可能的。
是哪个方向?梦常有这种倾向,它们一旦结束了,似乎就变得不可思议。但是历史告诉我们,有时候恰恰是那些看起来不可思议的梦想最后变成了现实,与“现实主义者”的期待相悖,法国大革命成功地让贵族阶层和旧制度倒了台;基督教在多神论的异教罗马帝国取胜;亚里士多德的一个学生征服了世界,他的朋友们建起了图书馆,以及学问和研究的中心;一位阿拉伯传教者的信徒改变了数以百万计人的思想和生活……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更多的时候,崇高理想在庸常生活的重压下破灭了。它们昙花一现,它们轰然倒塌,而后归于沉寂。历史有许多无果而终的支流,然而实际发生的事通常要更复杂,历史在曲折的道路中前进。法国五人执政委员会处决了罗伯斯庇尔,威灵顿公爵击败了拿破仑,法国国王重登王位。革命被镇压……
但是它真的失败了吗?历史上的运动是由观念、伦理判断、激情和世界观来驱动的。它们通常会走到死胡同。但有时它们会留下印迹,对文明的思想结构产生深刻影响,使其产生不可逆转的变化。革命就像一只老鼹鼠,在历史的土壤中挖了一个深深的洞穴。有时,它会突然露头。掌权阶层会有这样的幻想,什么都不会改变。但是,老鼹鼠会在出其不意的时候出现。我们的文明,我们信奉的这一整套价值观,是历史上无数敢于热切瞩望和梦想的人们的愿景,是无数的观念给我们留下的遗产。
意大利1977年的运动,如果孤立来看,是无法理解的。它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席卷意大利乃至全世界的梦想的迟来的表达——不是最后一个,但应该是较晚的一个,也因此更加强烈。当然,它不是一个精心组织、目标一致的运动,其中有一千条不同的支流。然而,尽管有很大差异,所有这些支流都认为它们归属于同一条河,共享同样的水流——从布拉格广场到墨西哥城里的大学,从美国伯克利的校园到意大利博洛尼亚的威尔第广场,从加利福尼亚城市和乡村的嬉皮士公社到南美的游击队。还有从支持第三世界的天主教游行,到英国的反精神病学运动,从泰泽到约翰内斯堡。尽管在具体态度上有很大差别,但参与其中的人们普遍感到他们归属于同一个伟大的潮流,有同一个伟大的梦想,都是同一个“抗争”——这是当时人们常用的一个词——的组成部分,创造一个焕然一新的世界。

人们梦想着建立一个消灭了社会不平等和男权至上的世界,这里没有国界,没有军队,没有贫穷。在新世界里,只有合作,没有争权夺利,没有偏执狂热、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狭隘的“认同至上主义”,正是这些导致了一亿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丧生。这些都是崇高的梦想,展望一个没有个人财产、没有羡慕嫉妒、没有等级、没有教会、没有强有力政府、没有原子封闭式家庭单位、没有教条的世界。简言之,就是一个自由的世界。在那里,过度的消费主义没有容身之地,你可以为了精神愉悦而工作,而不是为了挣钱、消费或者阶层跃升。
今天,仅仅是提到这些理念,就可能被人怀疑是精神错乱了。但在当时,全世界许多年轻人都认为这是可能实现的。那时候,我去了好几个大洲旅行,所到之处都会遇到志同道合的年轻人。我和我的朋友们在1977年谈论的话题,不是当下的烦恼,什么经济上没有安全感啦,或者担心找不到工作啦。我们不想找工作,我们想的是拥有不工作的自由。关于那个年月,下面是我记忆最清晰的部分。
我们当时一起住在开放的房屋里,没有固定的睡觉场所。和每个年轻人一样,当时我们最主要的事,就是疯狂地恋爱,让自己迷失在激情中。性是被广为接受的一种和人相遇相知的途径,对男女都适用。我们对性的态度是严肃的,将它视作生活的中心,几乎像是宗教。就像宗教充满了它信奉者的生活,我们想用爱情和性爱来填充我们的生活。此外还有友谊、音乐和新的相处方式,总之和前代人那种灰暗、充满竞争的生活方式不同。我们尝试集体生活,消除嫉妒,尝试真正地共存。当然过程中会有争吵,关系会破裂,就像在任何家庭中一样。但是那种归属于一个大家庭的感觉是根深蒂固的:这个大家庭的成员散落在世界各地,正在往一起聚集,就像星际探险者们期待着建立一个新的不一样的世界。我一直在想,欧洲在美洲建立的首批殖民地上的贵格会成员,耶稣在巴勒斯坦时的门徒,最早的基督教徒,参加意大利统一运动的年轻人,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同志,乃至于柏拉图学园中的学生,一定和我们当时的感觉有相通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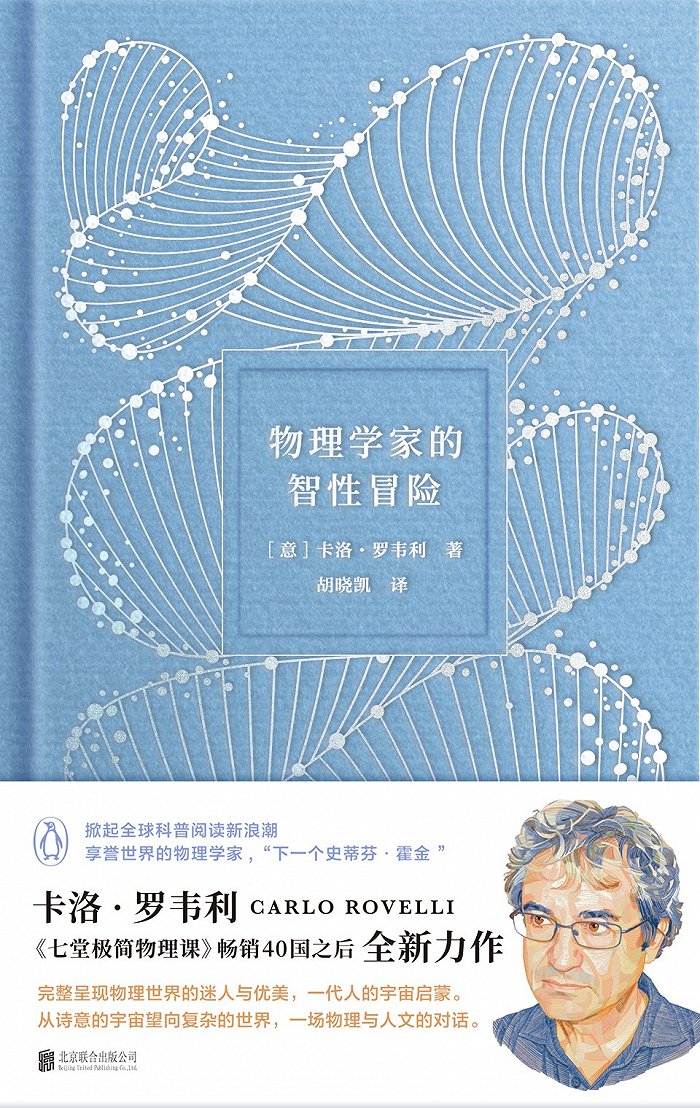
[意]卡洛·罗韦利 著 胡晓凯 译
文治图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2-2
但是我们在建立新世界的尝试上一败涂地。很快我们就尝到了幻灭的滋味。一些计划因为判断错误而被抛弃,更多的计划则是因为失败而被摒弃。我们理想的可能性就像阳光下的雪一样消融掉了。我们分道扬镳,在各自选定的路上走下去。
那么是否从一开始就不该有什么梦想?我不这样认为,原因有二。第一,对我们许多人而言,那些梦想为我们的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那时的一些价值观在我们身上植根,而正是这些抱负引领着我们向前。那些年所培育的自由思想的极端形式,就是认为一切皆有可能,都值得探索,每种观点都可以被修正和调试,这为我们许多人后来的人生选择提供了宝贵的滋养。
第二个原因我不知道是否可信,但它确实存在。在历史进程中,建设一个更好世界的梦想不断地被击垮,但是它们会转入地下,在那里继续保持活跃。最终,它们会促成真正的变化。今天的世界似乎比以往充满了更多的战争、暴力、极端社会不公和偏执、民族主义,不同种族和宗教团体之间互相隔绝、彼此争斗的程度更深。我仍然相信,这个世界不是唯一可能的世界。在这一点上,也许我不是孤单一人。
(《晚邮报》2017年2月15日)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物理学家的智性冒险》,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