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编辑 | 黄月
对于世界发展,有一些思想者持有乐观态度。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史蒂芬·平克在《当下的启蒙》里歌颂了人类取得的进步,证明理性、科学和人文主义促进了人类的福祉,并认为这种趋势不仅限于西方,而是遍及全世界。持有类似乐观态度的还有《人类之旅》作者、经济学家奥戴德·盖勒,他歌颂了19世纪以来的增长和繁荣,但他同时也认为,地理环境、社会多样性、制度和文化因素等初始条件的不同埋下了财富与不平等的种子,他给出的解药是因地制宜的教育方式和增长政策。
如果说幸福的国度不无相似,贫穷国家各有各的难处,那么这些贫穷国家之间,是否也存在一些共性?在《最底层的十亿人:贫穷国家为何失败?》一书中,牛津大学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教授、前世界银行发展研究部门主任保罗·科利尔想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

在求学时,科利尔一位朋友的父亲是小国尼亚萨兰的总督,这里是非洲最贫困的国家,后来更名为马拉维。改变一个国家的名字容易,但改变国家的处境却很难,几十年过去,马拉维依然穷得响叮当。科利尔也一直保持着对马拉维这样的国家的关注。他发现,虽然一度贫困的中国、印度等国家能够迎头赶上,可并不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能做到逆转局势,而那些发展失败的国家更是面临着独有的棘手问题。
在最初出版于2007年的《最底层的十亿人》一书中,科利尔指出,当时世界上存在着58个“不仅是在日益落后,而是在日益崩溃”的国家,它们都是小国,即使人口相加也比不上中国或者印度一个国家的人口。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非常低,其中典型国家的收入甚至比富裕国家大多数城市的收入还要低。科利尔担心污名化一个国家往往会导致预言自证(selffulfilling prophecy),在书中并没有给出这些国家的具体名单。不过,本书面世之时,在全世界最穷的十个国家里,非洲占七个,根据2021年全球人均GDP排名,倒数的十个国家有九个来自非洲……一些问题依然悬而未决,甚至可能愈发严重。
“陷阱”使发展不可能

右派倾向于否认发展陷阱的存在,坚称只要采取好的政策,任何国家都可以摆脱贫困;而左派倾向于认为全球资本主义在本质上造就了贫困陷阱。这些贫穷国家面临着什么“陷阱”,又该如何行动来摆脱它们?
科利尔将拥有最贫困人口的58个国家的极端贫困归因于四个“陷阱”中的一或多个:冲突陷阱、自然资源陷阱、深处内陆并与恶邻为伴以及小国的不良治理的陷阱。
他注意到,在最底层的十亿人所处的国家中,有73%最近已经或正处于内战之中。科利尔没有将内战归咎于社会不满,例如社会排斥或镇压,他发现,收入水平低、经济增长缓慢和/或依赖初级商品出口的国家最容易发生内战——低收入意味着贫穷,低增长意味着绝望,这些都是滋生战乱的温床。更糟的是,一旦一个国家开始内战和暴力的循环,通常很难摆脱,即被卷入内战会增加短期内再度被卷入内战的可能性。

对石油、钻石等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会大大增加爆发内战的风险,自然资源本身也在制造陷阱。“为什么石油对于挪威来讲是好的,对乍得来说却不是呢?”在科利尔看来,自然资源对这些贫穷国家来说可能是一个诅咒:如果一个国家自然资源丰富,根据“荷兰病”理论(指一国特别是指中小国家经济的某一初级产品部门异常繁荣而导致其他部门的衰落的现象),该国很可能在其他出口方面失去竞争力。“以20世纪70年代的尼日利亚为例。随着石油收入的增加,该国其他出口产品(比如花生和可可)变得无利可图,生产迅速崩溃。”“荷兰病”排挤掉了那些原本具有快速增长潜力的出口活动,破坏经济增长的进程。
在治理方面,“资源诅咒”的核心问题在于,资源经济租金造成民主失灵。丰富的资源经济租金改变了选举竞争的方式,它让恩庇政治(politics of patronage)——用公款贿赂选民——成为可能。既然选举贿赂大行其道,那么涉足政治的人就会对原本吸引选票的方式——提供更有效的公共服务——不感兴趣。
第三个陷阱,即深处内陆并与恶邻为伴的陷阱,往往发生在一个国家资源稀缺且与海岸交通连接不畅的情况下,可能是该国自身的过错,也可能是因为邻国基础设施差。没有沿海地区,国家就很难融入全球市场。不论是否为内陆国,都受益于邻国经济的增长:一国的增长有溢出效应。就世界平均水平来说,如果一国的邻国经济额外增长了1%,该国经济就会额外增长0.4%。科利尔认为,对于无法进入沿海地区的国家来说,他们最大的希望是依靠邻国实现增长。
然而,当他们的邻居同样陷入四个“陷阱”的一个或者多个时,发展几乎不可能。以乌干达为例:它的邻国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多年来因政策不力而经济阻滞;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索马里都受战争所困;卢旺达和乌干达一样处于身处内陆的困境,甚至它还有国内的大规模冲突。这样一来,乌干达无法连通全球市场,不仅因为肯尼亚公路上的运输成本很高,也因为它无法将自身经济定位在邻国那里,因为它的邻国同样身处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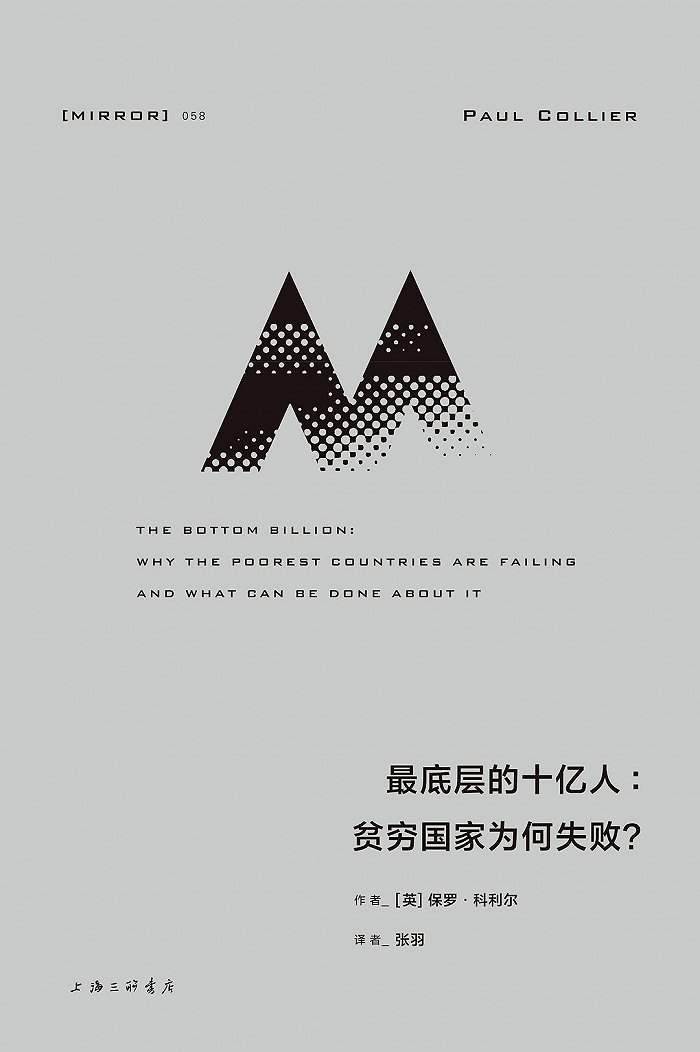
[英]保罗·科利尔 著 张羽 译
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 2022-9
小国的不良治理也会使一个国家陷入贫困。在小国,政府必然在引导经济发展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当本应指导经济发展的小政府发生腐败或管理不善时,发展根本就不会发生。科利尔估计了所有潜在的转型国家发生转型的可能性,并在其中寻找关键的特质:“对于一个失败国家而言,人口越多,受过中等教育的人口比例越大,以及如果刚刚摆脱内战(这一点最令人惊讶),那么这个国家就越有可能实现持续转型。”然而,不论在任何年份,开启持续转型的概率都非常低:只有1.6%。“因此,这些国家很可能长期处于失败的状态。由每年开启转型的概率,我们可以算出转型的期望值,即摆脱失败国家状态所需的平均时长。计算的结果是59年。”
变革必须来自社会内部
科利尔意识到,变革必须来自最底层的10亿人所在的社会内部,其他国家的政策可以让这些努力获得成功的可能更大一些,从而让人们付出努力的意愿更多一些。
他认为外部可以帮助最底层的10亿人的措施,包括军事干预、援助、法律和宪章以及贸易政策。每项措施的适用程度取决于每个国家的特定陷阱,因此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科利尔乐观地认为,他的建议能够起到作用,并且实施这些建议的意愿是存在的。
外部援助的举措一直面临争议:“左派过分强调援助,理所当然就遭到了右派的反击……右派人士对于援助的一种诟病在于,援助最终进入了瑞士银行账户,”科利尔说,贫穷国家需要的技术援助多于资金支持。在一次采访中他谈到,在当地政府已经相当称职的情况下,资金支持是正确的;但在公务人员和预算程序严重腐败的环境中,资金支持是错误的。在这些情况下,人们不仅仅是在浪费金钱,而且把钱交给了对社会造成最大破坏的人们。以乍得为例,“欧盟委员会对乍得这个极度贫困的国家的善意支持,最后大多都可能变成了对军事力量的资助。”另一方面,这些地区技术人员严重短缺,需要广泛的技术援助。

至于军事干预的作用,尤其是当国家陷入冲突陷阱时,科利尔认为,军事干预可以起到驱逐侵略者、重建秩序、维护战后和平和预防政变的作用。“外部的军事干涉对于帮助最底层10亿人的社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些国家自己的军事力量,反而要比外部的军事力量更称得上是这些国家的心腹大患。”
援助需要金钱,军事干预需要勇气,还有什么样的干预措施成本低、效率高呢?科利尔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措施通过改变我们自己的法律,让最底层的10亿人受益;另一类则是制定国际规范,帮助引导这些国家表现得更好。”他认为,西方银行长久以来都在将从最底层10亿人社会中掠夺来的资金作为存款接纳,这使得这些资金神不知鬼不觉地被掠夺者和银行纳入囊中,再也不会完璧归赵。通过西方消费者的压力和来自政府的压力,科利尔认为可以制定一系列国际标准和守则等来帮助进行改变。
除此之外,科利尔还提出要扭转边缘化的贸易政策。“制定关贸总协定的时候,最底层的国家并没有参与,大多数甚至都不是成员国。但是1995年世贸组织成立的时候,它们都加入了,加入这个组织就意味着它们属于现代世界。然而,在这个为讨价还价而设计的组织中,它们基本没有地位。对于世界其他国家来说,最底层国家的市场几乎无利可图,而它们的贸易壁垒很高,最底层国家一样无法从中获利。”这样的情况必须改变。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