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编辑 | 黄月
说来或许有些讽刺,《看不见的女性》的核心人物是一个男人。根据作者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Caroline Criado Perez)的观点,世界的运行方式是围绕“标准男性”(default male)设计的,标准男性就代表了“人类”本身,以至于虽然如今全球79亿人中超过半数为女性,但她们的存在感与数量是不匹配的,在生活中的很多方面,她们甚至是“看不见的”。
“自有记录以来,巨大的数据缺口占据了人类历史的大部分。从‘作为狩猎者的人类’(Man the Hunter)理论开始,编年史家几乎没有为女性在人类演化中扮演的角色留下什么空间,无论是文化还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演化。相反,男性的生活被用来代表全体人类的生活。而在谈及另一半人类的生活时,通常只剩下沉默。这种沉默无处不在,遍布我们的整个文化:电影、新闻、文学、科学、城市规划、经济学。”
佩雷斯在书中运用详实的事实和数字向读者呈现,性别数据缺口如何系统性地融入人类社会的肌理——不符合女性需求甚至可能为女性的生存发展造成障碍的设计、城市规划、职场规则、医疗措施、权力体系……
它给女性造成的种种后果中,有些或许只是让人感到恼火:比如男女公厕虽然面积相同,但女厕常常大排长龙;手机尺寸越来越大,让女性用户越来越难以单手掌握;办公室的标准温度根据平均男性静息代谢率设定,以至于女性员工总会觉得办公室太冷。有些则严重到可能致命,比如因为医疗研究对性别差异欠缺考虑,女性更容易因为误诊而死于心脏病,以标准男性为基准设计的汽车导致女性在车祸中受重伤的可能性比男性高出47%,死亡概率增加17%。
在《看不见的女性》问世约一年后,新冠肺炎酿成大流行病席卷全球。这一当下时代的“黑天鹅事件”,以一种出乎意料的方式呼应、强调了佩雷斯在书中提醒我们注意的一点:“在出现各种问题时屏蔽女性的声音是十分讽刺的,因为旧的偏见正是在极端情况下才最不合理,女性本就尤其受冲突、大流行病和自然灾害影响。”

《看不见的女性》于2021年在美国出版,佩雷斯为该书撰写了一篇全新的后记,特别指出了新冠疫情暴露出的女性困境。比如虽然医护人员中多数为女性,但她们拿到的防护服却是以标准男性身材设计的,这让她们暴露在更多病毒风险之中。佩雷斯在接受界面文化(ID: Booksandfun)采访时表示:“在这场危机平息后,我们尚需观察有多少国家会吸取这场大流行病的教训——它提醒我们女性的无偿照护工作在我们的经济发展和复苏计划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她承认年轻时也曾对女性主义充满误解,大学期间的一本女性主义语言学理论书使她豁然开朗,意识到自己对“女性主义者”标签所有的不理解和不耐烦,都源自那个无所不在的“标准男性”,“我们一直以为我们是以性别中立的态度在讨论问题,但其实我们在以男性的眼光讨论问题。”在佩雷斯看来,这个被默认的前提已经如人们呼吸的空气般自然,也让人们难以改变固有思维,做出切实改变。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佩雷斯成为了一位身体力行的行动者:2013年,英国央行宣布将在2016年去除英镑背面的女性历史人物——19世纪社会改革家伊丽莎白·弗莱。佩雷斯在英国民众中发起了一项请愿,要求在英国纸币背面保留一位女性历史人物。在她的努力下,2017年,新版10英镑纸币上出现了简·奥斯丁的形象。2018年,百年前为英国女性争取到投票权的妇女参政权论者米利森特·福西特成为伦敦议会广场上出现的第一座女性雕像,同样也源自佩雷斯的倡议。

佩雷斯觉得,自己进入女性主义的路径教会了她重要一课,思想和行动的改变是有可能的,尽管过程可能很漫长。为此,她希望所有相信平等和正义,愿为建设一个更好世界贡献力量的人都能从正视和挑战“标准男性”的存在开始,“消除‘男性至上’意识形态的最佳策略,就是指出来它确实存在。”
01 《看不见的女性》是对波伏娃《第二性》的21世纪阐释
界面文化:是什么启发了你写《看不见的女性》?“女性主义者”的标签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卡罗琳·佩雷斯:说来话长。我并非从小就是女性主义者,在更年轻的时候,我甚至是反女性主义者。我觉得女性主义让人尴尬,就好像在说女性就是很弱,像是充满了反男牢骚。在25岁左右,我已经是一名成熟的、需要去认真阅读一些女性主义文献的大学生,我的心态终于发生了改变。作为英语语言文学系的学生,我为了写一篇论文读了《女性主义与语言学理论》(Feminism and Linguistic Theory),书中讲述了男性如何在语言中被默认为常态的(“他”既可以指“他”也可以指“她”,“男人”可以指代“人类”)。
和许多其他人一样,我之前也听说过这个问题,但不以为然——大家都知道这些词是中性的,让我们讨论一些真正的问题好吧!但这本书援引了许多研究指出,当人们读到或听到这些词的时候,他们的脑海中浮现的就是一个男性,这一点让我吃惊不已。我第一次意识到,当我听到这些词的时候,我也自然而然地想到男性,我不敢相信之前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这一进入女性主义的路径让我开始意识到,“默认是男性”的现象无所不在,这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并会为女性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的严重程度远超“听到中性词但想象的是男性”。
本科毕业后,我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行为经济学和女性主义经济学,发现当我们量化经济成果时存在大量的性别数据缺口,比如说GDP的计算遗漏了许多女性的生产贡献,但我们以为这是一个客观的、性别中立的数据,并据此制定各种政策。我参与过一个女性难民慈善组织,发现即使是《联合国难民公约》这样的、在二战后制定且绝对没有歧视女性难民本意的文件,都会导致女性比男性更难寻求庇护,因为该公约是围绕着被迫害男性的经验设计的,忽视了女性的情况,比如女性比男性更难独自旅行。
我在生活和工作中无意识地收集这些案例,看到了某种模式,觉得居然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简直太疯狂了!我们一直以为我们是以性别中立的态度在讨论问题,但实际上我们在以男性的眼光讨论问题。
让我成为女性主义者的“最后一根稻草”来自我写第一本书的经历。我在收集资料时发现了医疗数据中的问题:女性不仅不一定会体验到在传统经验和流行文化中已定型的经典心脏病症状——胸痛和左臂下方疼痛——而且医生们也没有接受相应训练,识别出女性的典型症状,比如消化不良的感觉、恶心和疲倦。为此,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因心脏病病发身亡。我还发现许多医疗研究并不考虑性别差异因素,因为雌性的身体,无论是人类还是动物,被排除在了研究范围之外,理由是“荷尔蒙异常”。我认识到,这只不过是女性在学校课程、媒体和政治中代表性不足的冰山一角,我们一直对此视而不见。
这是我认为自己有义务写这本书的原因。我希望人们能看到这个模式,看到它事关生死,有必要引起重视。我觉得,我进入女性主义的路径也让我坚定地相信变革的可能性:只是通过阅读一本书,我就从一位反女性主义者变成了一位女性主义者。我希望我的书能改变更多的人。

界面文化:这本书在西方引起了强烈反响。你看到了哪些有意思的读者反馈?
卡罗琳·佩雷斯:我觉得最有趣同时也最让人心碎的评论来自一些女性读者,她们告诉我,读了这本书后她们终于理解了这个世界,也终于不再为一些生活中的不如意责备自己。女性太容易认为自己有问题(因为这个社会太过经常认为我们有问题),对她们来说,发现自己的身体无可指摘着实让人松了一口气,真正有问题的是这个假装50%全球人口身体不存在的世界。
界面文化:这本书引用了大量研究,展示了性别数据缺口如何系统性地融入人类社会的肌理。当你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最让你震惊的发现是什么?
卡罗琳·佩雷斯:一切都让人震惊!书中的核心前提——男性是性别中立的人类代表,因此我们无需收集女性数据了——让人震惊!也许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汽车安全问题:多年以来汽车制造商只会使用男性假人来做碰撞测试,如今,使用以中等水平男性为基准设计的假人来做碰撞测试依然非常普遍。但对中等水平的女性而言,这太高也太重了,也没有考虑到诸如肌肉质量比例或骨盆等方面的性别差异。结果就是,当女性遭遇车祸时,受重伤的可能性比男性高出47%,死亡概率也增加了17%。
界面文化:多年来(事实上是千年来),我们对性别数据缺口问题的深度和广度缺乏体察。为什么我们要等到21世纪才终于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了?
卡罗琳·佩雷斯:其实,我的书只不过是对波伏娃在1949年发表的《第二性》的21世纪阐释。波伏娃率先提出了男性的本体地位和女性相对于男性的次要地位。我所做的,是把这一重要洞见用来分析各种各样的数据,和以这些数据为基础建构的日常生活。当然,问题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这种偏见太过平常,难以觉察。我们不会去质疑它,不会注意到它,直到它被明确指出来。通过这本书,我希望唤起人们的注意力,让他们意识到将男性当做中性代表的后果就是50%的全球人口被忽视了,我们终于可以开始着手解决性别数据缺口导致的后果,有时这一后果甚至是致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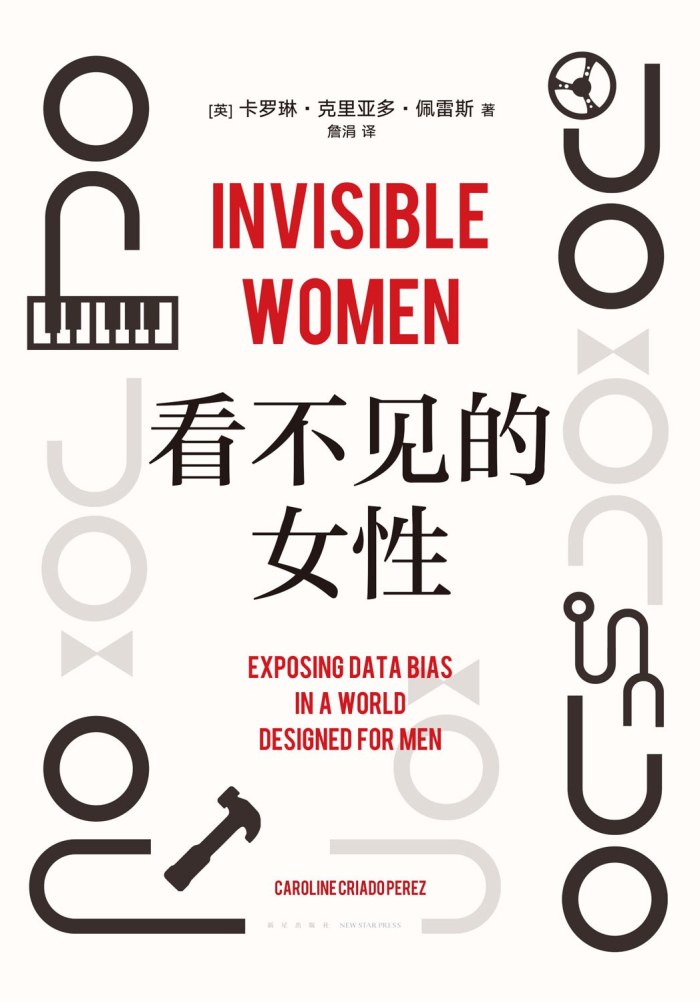
[英]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 著 詹涓 译
新经典文化 | 新星出版社 2022-8
界面文化:你给出了强有力的证据解释性别数据缺口如何让世界上的一半人口“隐身”,但对它的成因你好像没有给出过多解释。我们可以说这是出于文化惰性么?
卡罗琳·佩雷斯:部分原因确实是如此。我们抗拒改变。但这同样也是因为我们甚至没有意识到我们在抗拒改变。我们太过习惯将男性视作标准人类,以至于大多数时候我们的表现就好像女性人口不存在一般。
02 当我们讨论女性问题的时候,我们在讨论所有议题
界面文化:任何一个社会变革想取得成功都需要团结尽可能更多的人。就性别平等事业而言,一个很大的障碍是许多男性不是忽视这个问题,就是将之视为零和游戏。在你看来,我们应该如何建设一个对两性来说都更好更公平的世界?
卡罗琳·佩雷斯:安德丽娅·德沃金(Andrew Dworkin)曾有过一句名言,她说女人是唯一与压迫者同床共枕的弱者群体。她说这话的意思是,女性的生活与男性的生活太过息息相关(作为他们的母亲、姐妹、女儿),导致她们很难获得解放,很难有效组成起来成为一个利益群体,我们寄希望于我们生活中的男性能做得更好。不过我想,这个观点反过来对男性也适用——他们的生活也是和女性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他们是我们的兄弟、父亲、儿子。他们不会希望我们因为汽车的设计缺陷而在车祸中丧生,不会希望我们因为医生未能诊断出发病症状而死于心脏病。男性和女性的联结应当将男性拉入性别平等的斗争之中。
界面文化:女性主义者如今面对的一大质疑是他们沉溺于“身份政治”,他们给予性别太过关注,忽视了阶级、种族等其他重要议题,以至于无法有效地实现推进社会整体福祉的目标。你对此怎么看?
卡罗琳·佩雷斯:正如我在书中所写,每个人都有身份。问题在于,我们表现出来的样子仿佛只有女性才有身份,男性没有,这个问题在阶级和族裔维度同样存在。因此,女性因为谈论女性问题而被指责陷入“身份政治”(请不要忘了她们构成50%的人口),但当男性谈论男性的时候——大多数政治辩论的关切目标——我们表现得像是这就是普适性议题。问题在于,由于男性占据了性别中性的制高点,这个优势让我们难以看清真正发生了什么。另外,我们也不要忘记女性构成了50%的工人阶级和50%的少数族裔,当我们讨论女性问题的时候,我们在讨论以上所有议题。

界面文化:对那些有意识用女性主义视角看世界的年轻女孩和男孩,你有什么建议吗?
卡罗琳·佩雷斯:我能给出的最佳建议是给家长和老师的——不要让标准男性的形象坚无不催。绝大多数的儿童电视节目、书籍、玩具充斥着男性角色,仿佛这个世界上90%的人是男性似的。把这一点向我们的孩子指出来,了解他们的想法,询问他们怎么看这个世界的呈现方式。消除“男性至上”意识形态的最佳策略,就是指出来它确实存在。
03 对女性领导者寄予太多期望,是因为她们实在太少
界面文化:这本书首次出版于2019年,在其中一章,你谈到战争、自然灾害和大流行病会让女性更加脆弱。对很多人来说,新冠肺炎可能是第一次大流行病的经历。至少在中国,许多人意识到了你在书中提到的一个问题:女性在公共卫生危机中的工作与贡献难以得到应有的认可与回报,女性工作者在抗疫前线的需求难以被满足,比如卫生巾和尺码准确的个人防护用品。如果你要为新版《看不见的女性》加入新冠疫情相关的内容,你会写什么呢?
卡罗琳·佩雷斯:我确实为《看不见的女性》美国平装本撰写了一个新的后记,这本书于2021年在美国出版。我写到了新冠肺炎——大约在《看不见的女性》首次出版一年后,它被官方宣布为大流行病——如何以一种我当初未曾预料到的方式呼应了我在书中提出的观点。
最严峻的问题之一是,全球各地医务工作者拿到的个人防护用品是根据高加索白人男性的平均身材设计的。导致的后果是,在这一由女性主导的群体中,很多人难以得到充分防护,在挽救我们生命的同时却令自己暴露在风险之中。同样让人非常沮丧的是,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在系统性地收集患病率的性别数据,更不要说如此多的治疗研究压根没有考虑性别因素。
在这场危机平息后,我们尚需观察有多少国家会吸取这场大流行病的教训——它提醒我们,女性的无偿照护工作在我们的经济发展和复苏计划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目前来看,前景并不乐观。
界面文化:2019年至今,英国的政治环境发生了许多变化,伊丽莎白·特拉斯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三位女性首相,媒体称她或将成为下一位“铁娘子”。我们都知道女性身居高位依然困难重重,你觉得特拉斯有可能拓宽女性政治家或女性整体在公共生活中的边界么?
卡罗琳·佩雷斯:的确,甚至自你提出这个问题以来,英国政治都发生了剧烈变化!这篇采访发表的时候特拉斯或许都已经不是我们的首相了(记者注:特拉斯已于10月21日辞去首相职务,在任仅45天)。
让我从更宽泛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吧。证据清晰地显示,女性领导人意义重大。首先,女性体验世界的方式是不同的,这不仅是因为女性身体的特殊之处,也是因为我们被对待的方式和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女性领导者会因此考虑一些和男性领导者不同的优先事项。经合组织国家数十年的研究发现,女性议员的比例极大影响了政策讨论和国家预算的制定策略。
另外一个我很喜欢的例子是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在《向前一步》(Lean In)中提到的:她在谷歌工作期间让公司启用了孕妇停车专位。她直接去找谷歌老板要求此事,他立刻就同意了,发现自己此前从未想过这个问题。这个案例告诉我们一个关键问题:很多时候不是说男性不是好领导、女性才是好领导,而是男性体验世界的方式和女性是不同的,有一些问题他们不可能想到,不可能了解,但女性领导就能意识到那些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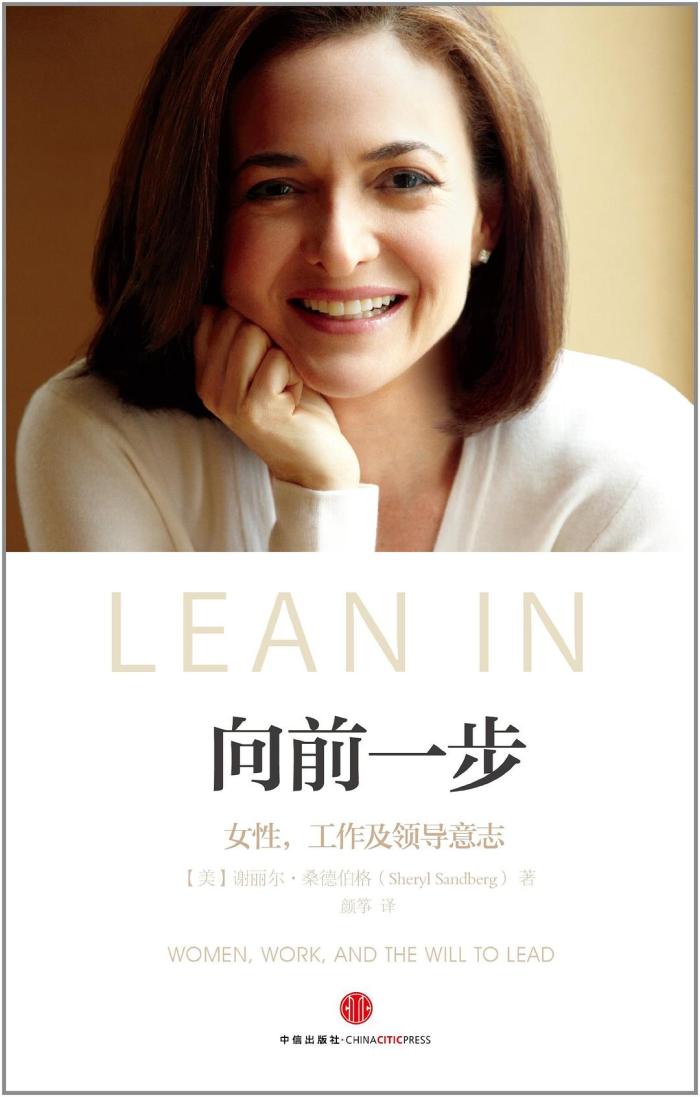
[美]谢丽尔·桑德伯格 著 颜筝 译
中信出版社 2013-6
最后我想说,我们对女性领导者寄予太多期望了,这不过是因为她们实在太少了。我们觉得她们需要成为所有女性的榜样,需要证明女性也有能力做大事,甚至是做那些男性做不到的事。男人可以只代表他自己,但如果一个女人成为了一个失败的领导者,就让人们觉得女性整体不行——这种情况只有当平庸的女性领导者和平庸的男性领导者一样司空见惯时才会有所改变。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