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编辑 | 黄月
在感官文化研究者康斯坦丝·克拉森的眼中,中世纪曾经是触觉的时代,人们喜欢围炉而坐、用手抓饭来吃,使用刀叉反而会被认为是做作可笑的。在中世纪的文学世界里,人们对触觉也有着敏锐的意识。在乔叟的小说《贤妇传说》中,讲述者整日游荡于绿草如茵的的田野,“顾盼着新鲜的雏菊,直待太阳由南方而转向西沉。”对于那时的写作者来说,大自然曾经只有前景。
后来的事我们都知道了,从十六世纪开始,城市里到处都是陌生人,消费行为无需跟邻里接触就能完成,身体接触越少越好,亲密的拥抱留给家中的爱人就够了。我们变成更受规训的、更加文明成熟的身体,而现代性的箴言变成了:“可以看,但不要摸。”
在《最深切的感觉:触觉文化史》一书中,克拉森发现,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对于触觉体验的忽视都十分严重,这种明显的忽视对应着视觉的中心地位,也勾连出一系列人类历史中的不平等偏见:注重隐私的贵族和挤作一团的平民、高高在上的人类和依赖触觉的动物,当然,还有运用心智、习惯于凝视的男性和依赖身体感官的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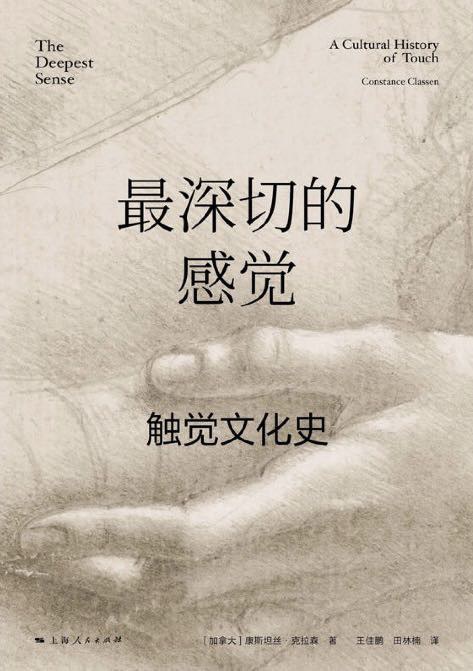
[加拿大] 康斯坦丝·克拉森 著 王佳鹏 / 田林楠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2-9
为了让历史事实不再是干瘪的骨架,克拉森找到了许多具身性的历史案例。在这其中,她还单辟出一章来讲述女性的触觉,以及它所代表的、迥异于现代的宇宙观思考,而这对于今天不断滑动着手机屏幕、与朋友相隔万里的我们来说,无疑是深具启发性的。
如同编织的女性写作,超越藩篱

“女人说出的言语可能是轻柔的,也可能如蓟草一样锋利,如荆棘一样刺人。”
这句话既表明了女性的感官特征,又说明了女性触觉的二重性:既能治愈人心,也潜藏危险。在克拉森看来,即使是富裕的女性也会被限制在家庭里,做一些缝补衣物、照顾孩子的工作,而一个出门在外的女人是与周遭格格不入的,即便她什么都不做,也会被看作威胁。因为女人的身体本来就具有令人愉悦的触感,在一幅以感官为主题的十九世纪讽刺画中,其他四种感觉都是由男性来表现的,唯有触觉是由一名裸体女模表现。
那么,写作的女性应该被放在什么位置上?这个问题颇有点复杂,克拉森认为,书写和编织衣物有相似之处——都可以在家内进行,也都是某种手工作业。但写出的作品有获得公众关注的可能,所以女性写作时常被视为混乱的、流变的,会威胁到男性的社会支配,因而受到惩罚。诗人艾米莉·狄金森喜欢待在家里,墙壁栅栏和悉心照料的花园保护着她,她对公开出版不以为然,评论家便拿狄金森的自我隔绝大做文章,认为她在文学上”没有母亲,也没有女儿“,如此一来,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把她扫除于传统之外。

“少用她们的舌头,多用她们的针线。针越是尖利,产出和快乐越多,但牙尖嘴利,却会咬掉快乐。”诗人约翰·泰勒在1624年的《针的赞美》中这样写道。
但是,一旦尝到甜头,“牙尖嘴利”的快乐又岂能被轻易地收回?写作如同编织,织成的不只是文本,也是多彩的幻想和女性交际网,这些幻想冲破了闺门,引起更多人的讶异和赞叹。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是明末清初的江南才女文化,在著作《闺塾师》中,作者高彦颐注意到,那一时期存在着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妇女结社,结社中的女性通过读和写的创造性行动,在家内和公众、想象和现实的界线间穿梭,即使生活在异地,妇女们也会互相传递诗集、序跋和随笔。
有时,这种传递甚至超越了世俗的藩篱、阴阳的相隔。在当时的女性中间,汤显祖的名作《牡丹亭》十分流行,读者们着迷于它的新奇和炽烈,因受到感动而自己撰写评论,因为她们认为男主角柳梦梅没能理解杜丽娘的感情。最著名的《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就出自三名女性之手,她们在不同时期嫁给了同一名男性吴人,其中两名女性陈同、谈则在写完评论后就患病死去了,再由后来的妻子继承她们的精神、完成评注的撰写。最终,就如高彦颐所说,“一个爱情受创的女人杜丽娘的简单故事,被编织成了一套有着冲突信息的传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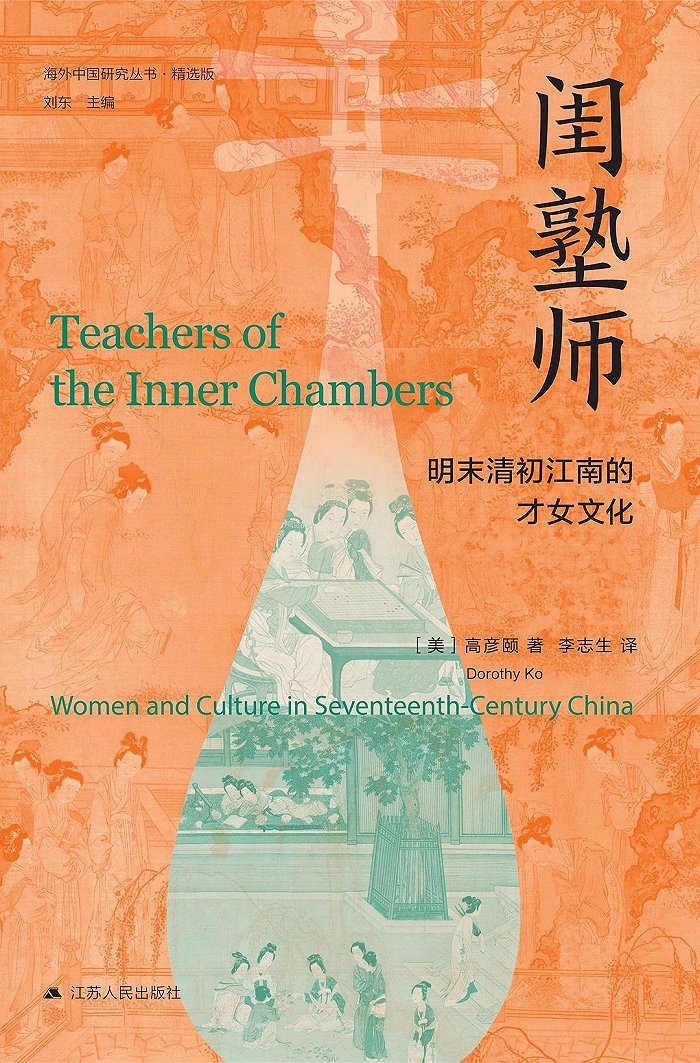
[美] 高彦颐 著 李志生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2-5
触觉艺术与空间:从围墙的家中眺望窗外
高彦颐认识到,虽然中国社会经常被认为是建立在“男女有别”、内外空间的分离基础上的,但真实的实践更加复杂,比起这个理想中的规范,女性栖居的领域更像是一个从内向外延伸的统一体,高彦颐将其称为“浮世”,在浮世中,城市商品化而增长的财富让妇女受教育的机会不断增加,社会关系不再是预设的,而是因情境关系而定,儒家秩序中的长/幼、男/女、旧族/新门也日渐松动。
于是,妇女结社在闺阁的私人领地内组成,并延伸至亲属关系、邻里和社会,她们一方面依赖着男性文人的交际网络,一方面也自觉地参与印刷文化、诉讼、反清复明的颠覆行动,更重要的是,她们运用着才智和想象,栖居于远大于闺阁的世界。
从内向外、不断延续的空间塑造了女性的创作,这一点在《最深切的感觉》中也有所提及。手工艺品经常被看做是琐碎和微不足道的,人们期待女性用她们灵巧的手工技能,为家里增添一点温柔的气息,但又不至于喧宾夺主,就如同打扫、缝缝补补那样,可以被安全地带回到女性的感官领域。
但事实上,克拉森发现,许多女性承担了大规模的室内设计,而当众多女性,比如母亲、女儿和朋友们一同合作完成项目时,她们的成果尤其引人注目。
在十八世纪的英国,富裕的酒商约翰·帕明特的女儿简·帕明特和她的表妹曾经建造了一座举世闻名的“围屋”,据说是基于大教堂的形状建造的,但又更像是乡村的度假屋。它有着不同寻常的十六边形设计,墙上覆盖着亲友们周游外地带回来的贝壳、羽毛、树枝和地衣,会客厅里装饰着精致的海藻和沙地景观。克拉森认为,这些材料产生了一种“持续转化”的感觉:
收藏品变成了墙,墙变成了桌子,桌子变成了画。房子里那些保持着平坦光滑的表面,通过对比的方式,使自身具有了一种令人颇感兴味的质地。

通过这些自然材料,房子周围的田园风光也被引入了室内,人们可以从房里向外眺望风景,也可以和风景建立亲密的关系,八扇菱形的窗户创造出既统一又裂变的视觉,简直像是万花筒的隐喻。克拉森写道,帕明特姐妹不仅仅是在用手工装饰房子,房子就是她们的作品,她们生活在自己的艺术之中。
无论是“围屋”,还是闺秀创造的文学“浮世”,它们都不只是女性的手工实践,而对应着一种与触觉更为相连的空间概念。克拉森在书中描绘这种空间的模样:人们在世俗世界仿效宇宙的同心圆模式,建造起四周城墙环绕的城市、屋子和花园,从界限到界限,从宇宙层次到宇宙层次,一直到最后在上帝之城之中安息。
在相当程度上,这样的宇宙观在现代已经失落了,人类的思维直接暴露在无限和失控的空间中,但同时又把自己作为主体封闭起来,身体陷入了孤独的境遇。在《性差异的伦理学》中,女性主义学者露西·伊利格瑞曾经这样写道:“看筑起屏障,冻住触觉的姻缘,麻痹感觉之流,结冰,让触觉沉淀下来,取消它的节律。”

伊利格瑞认为,我们其实一直拥有对触觉的渴望与激情,只不过这种渴望被扼杀了,就像是把编织和手工艺品贬低为无关紧要,或者否认女人们的写作能力那样——“男人给她买房子,把她关在里面,凭借墙壁来拥有她、包装她”,然后,男人就可以自己去受苦、背离肉身,为了营生去开发自然。跳出这种孤独的封闭回路,不仅能够让女人拥有言说的机会,也意味着找回我们的触觉。当相遇的机会愈来愈珍惜,或关爱的空间愈来愈狭窄,试图拥有一点肌肤之亲,也算是为这具身化的历史,增添了一把小小的火苗吧。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