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编辑 | 黄月
生死是无法更改的大事,但是科幻作品里总有另一种畅想。在那里,死亡可以被改变,甚至被彻底抹除。
在2022年的小说《在黑暗中我们能去到哪里》(How High We Go in the Dark)中,为了减轻送别亲人时的伤痛,人们发明出了各种荒诞的“新式葬礼”;改编自刘宇昆原著的美剧《万神殿》则讲述了一名已死的父亲通过意识上传实现“永生”的故事。当我们不必再以传统方式经历生离死别,这一美好愿景的结果会怎样呢?这些故事看似来自未来,却处处都在指涉我们已有的生死观。
01 假如我们在高级酒店或游乐园迎接死亡
美国小说家永松红杉(Sequoia Nagamatsu)的《在黑暗中我们能去到哪里》写于新冠疫情前几年,却似乎拥有先见之明,它描写了大瘟疫流行后的世界——由于气候变暖,科学家在融化的西伯利亚冻土中发掘出一具史前女性的遗骸,结果激活了威力强大的病原体,疫情很快遍布全球,人们也接二连三地死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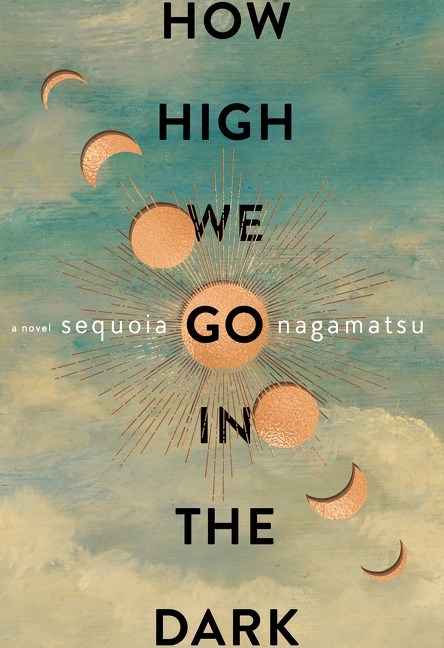
William Morrow 2022-1
整个故事就建立在“当死亡成为常态”这一设定之下,其中有些情节今日听来已非荒诞——比如超负荷运转的医院、被用作太平间的大型体育场——也有一些介于真实和虚幻之间。在小说中,殡葬业最先嗅到商机,它们纷纷抛弃过时的土葬和火葬,代之以更人性化的丧葬服务,业内的佼佼者还会获得一尊“金棺材奖”。面对这一局面,新开发的瘟疫疗法也要想方设法分一杯羹,但他们只是让病人陷入长久的昏迷,勉强称之为活着罢了。即使有些人幸存下来,也要么无法完成学业,要么成为了失业者,只能终日待在VR咖啡厅,在网上结交新人来取代死去的朋友和恋人;更孤独的人们则在论坛发帖抱团取暖,或者寻找着一起自杀的伙伴。

书中最精彩也最具讽刺性的部分就是那些送别死者的新奇方法。儿童和体弱者最先被感染,痛失爱子的亿万富翁便建立起一个“安乐死游乐园”,绝望的父母带着孩子来到这里,让他们坐上过山车,冲上云霄之际再被人为地停止心跳,以此来保证孩子最后几秒钟的生命中只有欢乐、毫无痛苦。随着死亡蔓延开来,下一个声名鹊起的项目是“殡葬酒店”,在这里,人们可以和将死的亲人悠闲度假,而不是在冰冷的医院与之告别,宣传标语如此写道:“当你所爱之人沉睡时,和他们睡在一起吧!”
这些做法看似荒谬,细细想来却又能够理解。人类学者露丝·贝哈曾在著作《动情的观察者》中做出判断,现代的死亡传递着双重的悲伤,悲痛不仅来自失去了心爱的人,同样来自内心深处的那种挫败感——觉得自己能做的还有很多,与死亡的抗争结束得太早;同时,即使在面对死亡的瞬间,人们也想要消除令人不快的负面印象,既为了减轻患病者的恐惧,也为了抚慰自己的伤痛,殡葬酒店就是敏锐地发觉了人们的这种心理,才能借此机会、大捞一笔。

然而,这些做法的背后,似乎仍是生命高于一切、尽量回避死亡的价值观。讽刺的是,无论人们怎样努力,潜藏其中的死气终究是挥之不去的,反而在掩盖之下显得更加狰狞。我们于是看到,游乐园其实是监狱改造的,象征快乐的过山车变成了恐怖的杀人机器,而为了不让父母反悔带着孩子逃离游乐园,守卫塔上设立了步枪手,准备随时射杀叛逃者。
作者还让我们看到,在瘟疫遍布的世界里,死不仅仍然保持着高低贵贱之分,商业化也让死亡变得更加不平等,而看似热闹的殡葬市场也只是以另一种寂静无声的方式利用着还有价值的人,淘汰着不被需要的人。有人原本是前途似锦的脱口秀演员,如今却要在安乐死公园逗将死的孩子们开心,还要向家人隐瞒自己的工作性质;殡葬酒店的经理原本是一名无业游民,却十分吊诡地在这里找到了为数不多的人生价值。某天,酒店经理走在街上时发现,当一些人可以被“负责任”地死去,他却很少看到流浪者们在长椅上睡觉、在餐厅里摆摊了,谁又会为他们的死负责呢?
02 假如意识上传让人质疑肉身的意义
新式葬礼虽然听来可笑,在技术上却不难实现,如果人类可以以数字形式永生,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刘宇昆的《奇点遗民》就写了这样的故事。以意识上传为主题的小说的关键,通常在于身份问题,也即“数字化的你还是真的你吗?”,但刘宇昆的重点更像是经由“爱”这一古老母题来探讨“怎样的活法才更为可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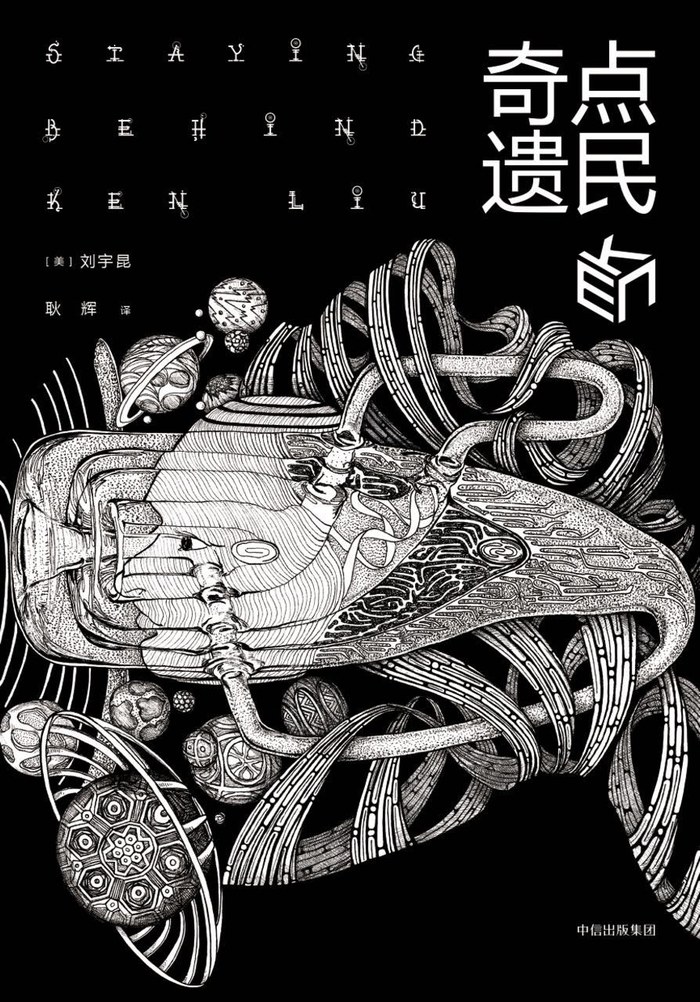
[美] 刘宇昆 著 耿辉 译
中信出版社·木晷文化 2017-9
在小说中,奇点时代已经到来,大多数人都留下大脑扫描后血肉模糊的躯体,成为了数字神灵。艾米的妹妹也自愿上传了意识,但是对艾米来说,妹妹不过是被困在一块机器存储阵列中,因为缺失了身体,艾米不知要如何爱对方,甚至没办法找个合适的方式悼念她。而艾米选择“专注于收藏明信片和烤蛋糕,用早晨的阳光和咖啡香味滋养我的身体,等待自己大限到来,这样别人就能用合适的方式悼念我了”。
在拥有肉身的生者和意识上传者之间,总是充满了隔阂和罅隙,这体现在他们不同的生之理念。在固守生死规则的人看来,身体才是最值得信赖的,也只有身体才能去远途旅行、尝出苹果的酸甜滋味,而数字人只是数字洪流的仿真算法,是“活死人”罢了。但是对于上传者来说,身体才是既薄弱又有缺陷的,它会衰老、会背叛你,只有摆脱肉体的束缚,灵魂才能得到自由,他们也给肉身人起了一个名字——冥顽不化的“古人类”。
有意思的是,肉身人认为,随着自然生长和凋零的生命才具有内在的善,祖父母、父母、子女,每一代都为下一代让路才能成为人的永垂不朽,数字人只是短视的鼠目寸光之辈。数字人却认为,肉身人的“活着”如同动物,仅仅是依靠本能的苟延残喘,人应该超越动物性、走向不朽,而此时的地球的确走向了末日——城市不堪人口过多的重负,成为了野草遍布的废墟,人们只靠罐头食品维生,虚拟世界则不存在资源匮乏、贫富差距,当然也不再有死亡和衰败。
这种种矛盾指向的,正是在未来的技术之下,原本的生命理念不得不时刻质疑自身的境况。书中的情节就彰显了这一点。女孩麦蒂的爸爸是第一批上载的人类,爸爸又创造了一个数字女儿,也就是麦蒂的妹妹。因为妹妹生于云端也长于云端,她仿佛没有弱点,从不惋惜没有肉体这件事,因为“人不会怀念不曾拥有的东西”。麦蒂以为妹妹只有虚无缥缈的意识,从没有吃过人间的食物,于是给妹妹品尝了种在花园里的番茄。然而麦蒂失望地发现,妹妹早就在自己的世界尝遍了几百种西红柿,她一直在以具体的方式生活,具体到我们远远无法理解。
03 假如死亡不再是永别
在许多族群的信仰和文明中,死对于生者而言都并非结束,而是在另一个世界拥有了精神意义上的生命,所谓“事死如事生”。正如民俗学者郭于华在《死的困扰与生的执着》中指出的,阴间的景况通常十分生动具体,无论是鬼门关、奈何桥还是无常殿,都是一套完整的、与人间对应的地方。但是另一方面,生与死又有着严明的界限,各地的丧葬仪式都有摆脱和防备死者的方式,有的在埋葬完毕后说一句“我去担水、砍柴”之类的托词,然后赶紧跑回家中,以防亡魂跟回来。
于是,当这个界限被打破,就意味着死者无法被顺利地送往彼岸,自己也难以放下对方、开始新的生活了。在《奇点遗民》中,麦蒂的妈妈以为爸爸早就去世了,当爸爸的数字灵魂出现在电脑屏幕上,妈妈并不开心,反而感到十分困惑。对她来说,丈夫的死曾经是内心难以迈过去的坎,她花了很长时间接受这一现实才走出阴霾,甚至结交了新男友,丈夫的归来却打乱了好不容易建立起的秩序。
与麦蒂妈妈的感受类似,早在1961年,科幻作家菲利普·K·迪克就在小说《尤比克》中借“中阴身”的概念,描绘了一个徘徊于生死之间、充满了困惑和断裂的世界——在其设定中,人们即使死去也可以用冷冻技术储存在亡灵馆中,通过短暂的大脑激活和前来的探访的亲友交谈、互相抚慰。然而,这个世界也总是在坍塌和腐坏,时光会不断倒流,咖啡刚煮好就发霉了,硬币也变成了四十年前的过时货;主角明明想要拯救死去的上司,却发现自己好像才是已死之人。这一切似乎在说,亡灵世界的规则不容侵犯,如若不然,受到侵犯的便是我们。

[美] 菲利普·迪克 著 金明 译
译林出版社·译林幻系列 2017-10
不过,故事也有温情的一面,如果思念和意志都足够深刻,那么生死也是可以跨越的。作者这样描述一名丈夫探访亡妻的场景:
他能对她说话,听她作答,交流彼此想法……但那双亮眸不会睁开,朱唇也不再翕动。对他的造访,她没有笑脸相迎。离别之时,她也不会伤心落泪。这样是否值得?他扪心自问。这样的探访是否好过传统的生离死别——从一个活生生的人径直走向冰冷的坟墓?不管怎样,我们依然彼此相守。别无选择。
不顾形式,只要能陪伴彼此就够了。这也是《奇点遗民》中麦蒂的想法。并且,与一尊棺材中的冷冻躯体相比,虚拟人反而更好,虽然看得见摸不着,但至少能在线上相见,爸爸的记忆、口头禅和对女儿的爱都与往常无异,甚至在技术的加持下,虚拟的陪伴可以比现实中更牵动人心。爸爸还活着时,麦蒂就经常和他在房间里玩网络游戏,而当爸爸“转生”之后以化身(avatar)的面貌出现、用户名也再次显示“在线”,那一刻的感动是真实的,也是无比独特的——毕竟只有在游戏里,爸爸才长得像是所向披靡的、身穿铠甲的战神。

这样的相守是我们想要的吗?小说无法给出答案,读者们似乎也不能。无论如何,复活死者或上传意识仍然只是想象,但它们的确指向了一些矛盾,既想要挫败死亡,又自觉应该顺应天命。在平凡和超凡之间生活着的,就是我们人类。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