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在今天这个时代,一些年轻人感觉自己是‘地下室人’,感觉自己是螺丝钉。尤其是在科技发达的今天,人们感到自己在被算法控制着。这种情况下,如何从俄罗斯文学中汲取养料?”面对一位年轻读者的困惑,首都师范大学俄语教授王宗琥谈到,俄罗斯文学本身就是苦难和严苛的社会环境下诞生的,探讨的是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做到自我心灵的救赎。“在人被异化的环境下,如何真正做回自我,做一个大写的人——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都提供了很多可能的答案。虽然俄罗斯文学提供不了唯一正确的答案,但能够提供可能性。”
这是日前在《俄罗斯文学的黄金世纪:从普希金到契诃夫》新书发布会上发生的一幕。王宗琥与本书作者、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教授张建华进行了对谈。王宗琥认为,对于今天感到苦闷的年轻人来说,读俄罗斯文学之后,会觉得别人和你有着一样的苦难,甚至还要比你苦难得多,会“形成一种众生平等的感觉”。不论是什么样的阶层、有多高的官位,每个人要受的苦都少不了,这样“对你承受的苦难有一种释然”。而且,俄罗斯文学是理想主义的文学,会提供希望,他引用奥登的话“辛勤耕耘的诗歌,把诅咒变成葡萄园”称:“人就生活在两个世界,一个是严酷的、丛林法则的现实世界,一个是理想主义的文学世界。”

苦难中产生的俄罗斯文学
俄罗斯文学为何会与苦难相关联?在《俄罗斯文学的黄金世纪》中,张建华给出了这样的回答:“俄罗斯千年文化史中有近二百五十年鞑靼人的统治史,三百余年残酷的农奴制。历史上最严酷的政权,社会上最长久的动荡与混乱,暴力与流血,世界上最可怕的战争都曾经发生在俄罗斯的土地上。”因此,俄罗斯作家的精神探索、灵魂拷问的文学旅程穿越了一个“充满苦难、不幸的世界”。
张建华也谈到俄罗斯文学的黄金世纪从何而来——“黄金世纪”的说法最早出自学者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将人类历史分为了五个时代: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黑铁时代,后来这些称呼成为了衡量文化现象、社会体制等盛衰的标志。作家王小波也著有《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等作品。在文学上,所谓的“黄金”意味着一个民族文学的繁盛时期,例如唐朝就属于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

他看到,英国文学的黄金时代是维多利亚时期,法国文学的黄金时代是19世纪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折时期,两者都与俄罗斯文学的黄金世纪有很大重叠,但不同之处在于时代背景。在18、19世纪的英法,社会相对稳定,资产阶级制度也已经比较完善,中产阶级发达,因此大多数作品不会写不稳定和灾难性的内容,而是聚焦于市民阶层的思考与生活。而俄罗斯则还处于封建农奴专制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动荡历史时期——从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到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再到19世纪末,社会浪潮风起云涌,“俄罗斯文学的黄金世纪的关键词就是危机和苦难。”
美国文学批评家乔治·斯坦纳提出,西方文学发展史上出现过最为辉煌的三个阶段:古希腊时期、莎士比亚时代和19世纪后半期的俄罗斯文学。英国作家劳伦斯也曾提到,就19世纪的欧洲小说而言,到19世纪后期,欧洲文学思想艺术的高峰是以俄国文学为代表的。张建华认为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期始于普希金,以1910年托尔斯泰的逝世为结束的标志,其间俄罗斯文学呈现出了多种多样的现实主义表现形态——以普希金为代表的“文化复兴型”的现实主义,果戈里“巴洛克式”的现实主义,以屠格涅夫为代表的带有“抒情性”的现实主义,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的“存在式”现实主义。
俄罗斯文学的内容比西欧文学更为丰富,张建华说,其中人物形象的丰富程度是西欧所不具有的。既有有教养的贵族也有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还有在探索俄罗斯悲剧根源的知识分子,以及鲜明各异的女性形象,这一切都构成了对人类精神灵魂和对民族历史的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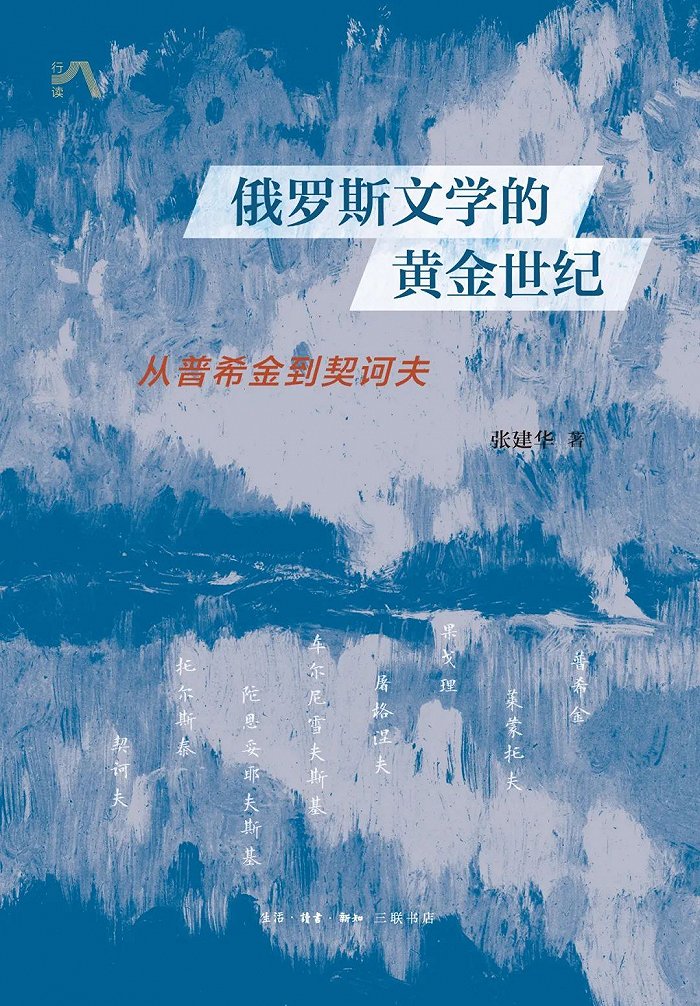
张建华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3-2
中国人读俄罗斯文学
“俄罗斯文学早就广泛深入到中国人的精神和物质生活中了,”王宗琥认为。新中国在成立七十余年的历史中,参考了前苏联的路线,所以,中国人了解俄罗斯文学也是在了解自己,体会俄罗斯作家对民族性的反思也是在反思自己。
他继而提到,阅读俄罗斯文学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学。张建华在书中对果戈里和鲁迅做出对照: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在果戈里的《狂人日记》的基础之上演化而来的,但是果戈里对民族文化心理批判时,是从宗教精神进行思考的,他认为治疗民族心理痼疾的方法是人的道德自新和灵魂忏悔,意图弘扬一种基督精神;鲁迅则有所不同,小说《风波》描写赵太爷,说革命党来的时候他把辫子盘上去,听说皇帝又坐稳了龙椅又把辫子放下来。张建华认为,这体现了中国人“乃至是现代社会中人的一种趋附潮流、迎合时代的生存哲学”,这也使得中国作家的小说和俄罗斯文学区别开来。
在五四前后的知识分子中,最早注意到俄语文学的是鲁迅兄弟。1906年,鲁迅在课间放映的幻灯片上目睹了神情麻木看杀头的中国人,忧愤不已,从仙台医专退学到东京,抱着以提倡文艺运动来改变精神的信念,开始大量搜读外国文学作品,“特别是被压迫民族文学和有民主革命思想的俄罗斯文学。”每月初各种杂志出版,鲁迅和周作人就忙着寻找,如果有俄罗斯文学的介绍和翻译,就要把杂志买来,把文章拆出保存。1907年鲁迅写下《摩罗诗力说》,热情地把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果戈里等介绍到中国。后来他做了这样的概括:
“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辛酸、的挣扎……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从现在看来,这是谁都明白、不足道的,但是那时,却是一个大发现,正不亚于古人发见了火可以照暗夜,煮东西。”
在上个世纪50年代之后,中国在经济发展、教育模式上也学习了前苏联模式,王宗琥说,在这一阶段,文学创作者纷纷“以俄为师”。他曾经带着俄罗斯作家团访问中国多个地区,每到一处,当地的中国作家都对俄罗斯文学如数家珍,作家铁凝也带着其中一位作家的作品请对方签名。“当时完全是学习心态,”就连学术研究也是这样,以俄罗斯思想家、作家的观点为主要观点。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才有了中国视角,也就是从中国人自己的经验体会出发去研究俄罗斯文学。张建华指出,中国读者并没有俄罗斯的文化经历和传统,所以必须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去解读。他认为,近年来中国视角可能已经成为一种学术上的流行,但“中国视角不是方法论,而是出发点”。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