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鼠鼠我啊,月薪三千。”不少以“鼠鼠我啊”开头的帖子,正流传于社交网络。从中我们可以读到类似这样的故事:“鼠鼠想改变,想要一个自己的家,鼠鼠也不想回到六十平米挤了三代人的出租屋,鼠鼠的父母也分开啦,没有房子,没有家庭,鼠鼠就像是没有根的浮萍。”
“鼠鼠我啊”首先出现在孙笑川贴吧,发言者以男性居多,以略带调侃的语气自我贬低、自我嘲讽。接着,鼠鼠梗在百度各个贴吧流行开来,连所谓“精英”出没的“985吧”都屡现鼠鼠发言,偶尔将自己就读的著名学府比喻成“带专”,哀叹“脱不掉孔乙己的长袍”。
目前看来,“鼠鼠我啊”已出现在各个社交网络平台,发言者不仅有男性也有女性,不仅有打工鼠鼠也有精英鼠鼠。鼠鼠形象从较为底层的男性演变得更加多元,“鼠鼠我啊”这句开场白也发展出了比原始帖子更丰富的内涵。
将自己比喻成老鼠,态度显得过于随和甚至自贬,意为我这样的像老鼠一样生存的人,本来就没有什么前途,所以说这样的话也不奇怪。我们对自贬文学并不陌生,杜甫在诗中还将自己比喻成丧家狗——“昔如纵壑鱼,今如丧家狗。”可问题在于,人们为什么会对自我贬抑为老鼠生出某种体认,甚至自我代入和模仿这种视角讲述经历?我们或许可以从“鼠鼠我啊”的底层视角谈起。

蜗居在阴暗面的耻感

“我是个老鼠,猥琐地活着,在这个纸醉迷金的世界,他们来到我的身旁,不感到绝望或者一丝慌张,也不知道自己过来什么地方。他们赤裸地来到我的身旁,没有一丝羞愧或者苦恼。”
在白皮书乐队的《老鼠》里,打工送外卖的我被比喻成一只在城市里奔波的老鼠,在现实与他人的交错中感到愤怒,渐渐迷茫,随波逐流。老鼠是自我形象的比拟,也是对他人的激烈回应——正是在他人的眼中,我变成了一只老鼠,在他人的嫌弃目光中,我真正地完成了变形。
将自己比喻成老鼠,不仅与真实处境相关,比如在大城市中打工生活漂泊无根,更与自我认知、羞耻的感觉深度相关。许多鼠鼠将自己形容为地下室与下水管居民,事实上,藏匿与蜗居也最能剖开这种耻感。比如童伟格的小说《我》,描绘的就是在台北做建筑工人的外来青年的生活。与其说要扎根城市出人头地,不如说他们想要暂时隐匿。两位青年住在水泥隔成的一间宿舍的上下铺里,高个儿的要屈起身体,青年喜欢在房间里用偷牵的电视线看电视,也很好奇租借图书馆的藏书不还会怎么样——对于界限的试探也展现了边缘者的好奇。平常没事的时候,他们就在平台上抽烟,看看旁边高架桥上的车流。
日本作家北杜夫的一篇名为《为助叔叔》的小说也描述了类似的蜗居生活。事实上,“鼠鼠我啊”本来就源于“叔叔我啊”的谐音,这不禁引人遐想,叔叔难道都是不成器的人?小说中这位将自我不断压缩的尴尬叔叔,是家族里最小的儿子,也是兄弟中最具有奇思妙想、不务正业的一位。孩子们叫他叔叔,大人也跟着如此称呼,调侃中略带轻蔑。叔叔的特点就是栽培和养殖奇怪的东西,例如在广口瓶里培养蘑菇啦,养出冬天也会飞舞的蝴蝶啦,或是养殖袋鼠占领澳洲。在这些创意想法一一破产之后,叔叔在家里的地位也变得尴尬,他的行为日渐谨小慎微,跟家里的嫂嫂们说话都用近乎卑微的措辞,然而属于成功者的顽固自尊仍然统治着他的灵魂,只不过被镇压得缩小成了一团。为助叔叔自己都不知如何处置这样经历过膨胀又遭遇急遽萎缩的灵魂,最终成为了家族这部井然有序的大机器里的“怪异同居者”。怀有强烈的羞耻感,叔叔远离了家人,“蜗居在人生背阴的角落”,他的亮相没有人关心,也不会比收破烂的老头更惹人注意。
蜗居在人生背阴的角落,这不正是许多鼠鼠的目标吗?鼠鼠身处下水道,偶尔想要看看天,但总体上清楚自己没本事,因此还是不要去追求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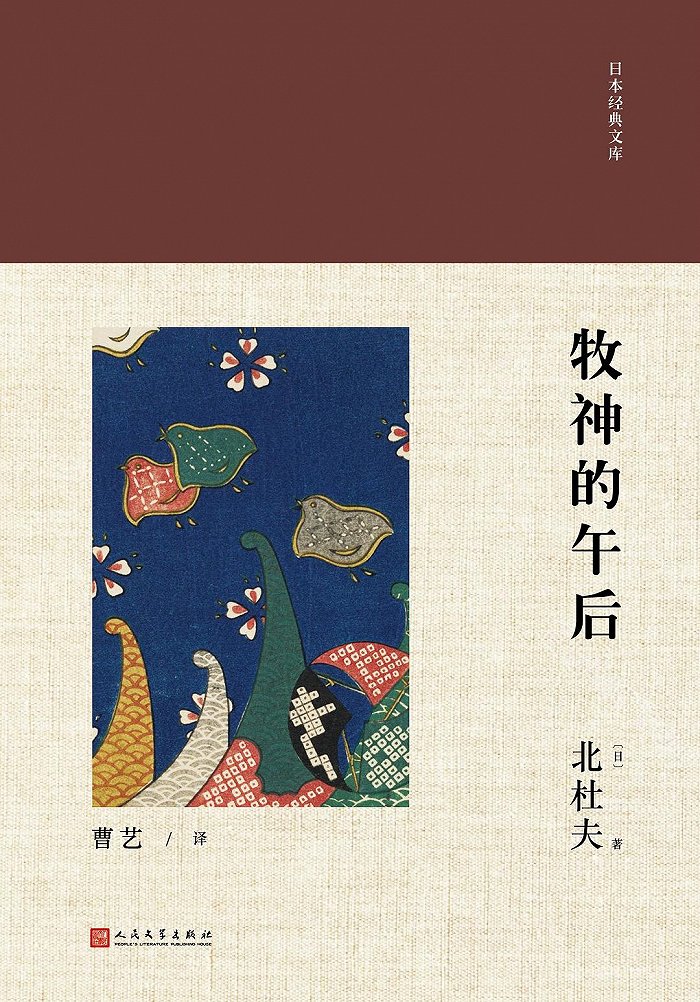
北杜夫 著 曹艺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年
并不是所有处于蜗居状态的都属于鼠鼠一族。最近出版的作家徐坤的长篇小说《神圣婚姻》讲的同样是外地人在大城市(北京)扎根的生活,但其中人们的种种盘算,包括通过玩弄婚姻制度“钻限购”的空子——主角之一、一位来自铁岭的中年女性已经到了拆散家庭,和一位专门办理假结婚的本地陌生人领证假结婚的地步——并没有让人“自我变异”,以至于“神圣婚姻”这个标题看起来有些自我讽刺的意思。主角的自我认知仍然是条达通畅的,也没有显得羞愧的地方。虽然小说构建了足够使她感到尴尬的情形:邻居被他家炉子烧的黑烟熏够呛,怀疑房主是外地来的,因为北京市早就煤改气了,只有外地人才不知道北京的规定,进而质疑男房主与她的关系。但即便惹出了如此事端,她也表现得非常适应,并不害怕袒露自己的真实情况,仿佛因为烧煤被针对为“外地人”并不尴尬,北京与铁岭的区别也并不要紧似的。与深谙世情的主角不同,鼠鼠一族对于曝光自己的真实状况耻感十足。
岁月流逝等于包浆
鼠鼠文学中弥漫着一种过来人语调,一个常见模式是今昔对比,经历了励志成功、努力挣扎、遭遇挫败的鼠鼠,以过来人的角度讲述成功之不易,更多的人还是失散了,走失在人海茫茫中。岁月流逝也是令鼠鼠感到敏感或苦涩的东西,过去年少轻狂,而今认清真相,事到如今,别无他法。
对于这种深深的无奈,鼠鼠文学也做出了一些具有特色的回应。在B站视频《献给那些努力自律一生却不快乐的鼠鼠文学》里,up主向观众强调,努力——成功——幸福三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各自独立;如果将这个模型简化为努力——幸福,就会让无数的鼠鼠越努力越不幸福。这类观点令人豁然开朗,毕竟前提肯定着鼠鼠的努力上进。

努力却不那么成功,是许多鼠鼠的心头遗憾。毛不易的歌曲《像我这样的人》如同对“鼠鼠文学”的注解,鼠鼠对应着人群里形形色色的人,“像我这样的人”也有许多种,优秀的、聪明的、迷茫的、寻找的,都是我,这既是对自己的动情慨叹,又有几分对世界的感伤——像我这样的人还有许多,所以无论怎么样都没有关系。就像网络上广为流传的那句鼠鼠名言,“鼠鼠我呀即使是独一无二的,但还是茫茫人海中最卑微的存在捏。”这样的自我认知因为契合了许多人的经历和感受,从而给人带来某种抚慰感。
比起《像我这样的人》,《少年》显得更为自恋,文本的自我矛盾也更加显著。歌词一方面赞美着真我不容易被外部环境改变,还是充满生命力与活力(“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时间只不过是考验,种在心中信念丝毫未减”),另一方面却讲究通达潇洒、随遇而安,没有什么值得真正执着(“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路在脚下,其实并不复杂,只要记得你是你呀”)。
执着真我与随遇而安在此奇妙地统一了,我是不会改变的,即使改变也是为了更加舒心快乐,外部环境无论怎么变迁都不会让我变得复杂、丑陋或者衰老,岁月只如同包浆。与杜甫的“自觉成老丑”相比,这相当地抚慰人心。S.H.E的《你曾是少年》还提醒人们,“习惯说谎就是变成熟了吗?……再过几年,你也有张虚伪的脸,”一如郑智化的《水手》对进入城市青年的劝诫,“如今的我,生活就像在演戏,说着言不由衷的话,戴着伪善的面具。总是拿着微不足道的成就来骗自己,总是莫名其妙感到一阵空虚。”这些提醒和劝解基本化为了一种心理按摩,既然外部怎么都无法撼动真我,那么何必区分真假,虚伪与谎言不也一样可以被宽恕吗?堕落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真我是如此清晰。用毛不易《消愁》的歌词来说,就是“宽恕我的平凡,驱散了迷惘”。
可是,宽恕平凡、驱散迷惘真的有这么简单吗?20世纪美国著名批评家特里林在《诚与真》里批评了“文化庸人”的形象,这种人格的整个存在都是在捕捉社会舆论以及相应的社会文化力量发出的信号,总在力求步调一致,以至于根本不是一个自我,而像一只学舌鹦鹉。特里林提示道,这类人如果能借由艺术领略文化的能量,发现并坚信个人的意义,却全然不是因为自主,而是因为来自他人的规则和意见,而结果就是将热情用于扮演想象中的自我,从一个陈词滥调的地狱走进另一个陈词滥调的地狱,这与多愁善感的自我歌颂相通。
鼠鼠文学有时看起来略带伤感,也是因为它不完全是自我贬抑,还有自尊自恋与自我膨胀的部分。或者说,“宽恕我的平凡”和“以岁月包浆”的想法,或多或少有一些安慰作用,对抗着年纪增长希望渺茫的残酷现实。鼠鼠回顾小时候得过的荣耀、擅长的事,想象着在那个未曾失落的世界、未曾远离的故乡,当年的我向往着初恋的白月光,相信着努力就能出人头地的梦想,对比成长后发现的事实,再轻轻调侃道,“别看鼠鼠我呀现在这样,鼠鼠也想过出人头地捡回儿时的荣耀。”而此时的解决方法,就像新裤子在《生活因你而火热》中所唱的,经历了疯狂、难过、刻骨铭心的伤害后的“我”,不得不去大楼的角落上班,发现格子间的女孩时间久了也很美,平淡如水的生活也可以沸腾火热。只不过,那个格子间的女孩想的可能是——再借用一句歌词,来自小缪《血汗写字楼》——“现在的我目标就是准点下班。”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