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树木仅仅是静物吗?花园又是何方天堂?在植树节这一天,让我们借由一份关于树木与园艺的书单,去看到人与树木的紧密联系:人们如驯服的植物被花园的院墙包围,有时又能穿过黑暗的泥土自由生长。
树木的旅行与叹息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可能对树木太过熟悉而忽视了它们的生命力。日本女诗人茨木则子在题为《树木喜欢旅行》的诗中想象了树木的一生,她写道,树木总会梦见开始旅行的那天,即使已经在某处扎根,新的果实也可以借着小鸟的口腹,再一次踏上征途,直到发现一个不错的地方,再次选择生根。树木渴望远方的证据写在它们的枝干与表皮之上:“用手触摸树干/就会彻底明白/树木有多喜欢旅行/明白对流浪的憧憬/和对漂泊的思绪/是如何使它们身体扭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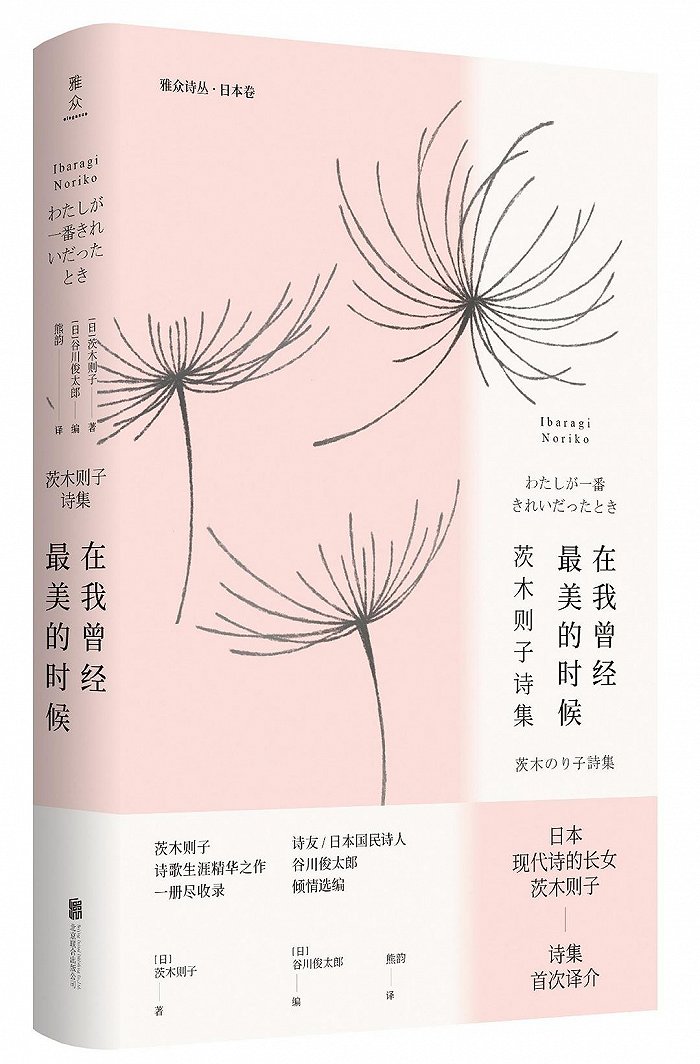
[日]茨木则子 著 熊韵 译
雅众文化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0-8
童话里的树木不仅渴望旅行,还会说话与叹息。爱沙尼亚童话《树木为何飒飒作响》里写,树木原本都会说话,可因为太会向樵夫求情,以至于樵夫没有办法做出抉择,就被老天爷集体噤声,如今只能通过飒飒声抒发叹息。
在一些传说中,树木与人们的灵魂相通。宗教史学家米尔恰·伊利亚德曾引用过这样的故事——在出生之前,人的灵魂像小鸟一样栖息在宇宙树的树杈上。生命树有一百万片叶子,每一片叶子都写着一个人的命运;一个人死去时,一片叶子就掉下来;一个人出生时,坐在一座七阶天山上的女神便在一棵长着七棵熟知的树上,写下这个人的命运。

天堂与地狱皆花园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在小说《天堂》里描写了令人神往的天堂般的花园。被父亲典当给商人的男孩来到了富人的花园,深深震撼于其美丽。花园与外部隔离,凉爽而宁静,有树木与灌木,还种着花草,薰衣草、迷迭香、芦荟还有一簇簇百合花,有些地方零星种着橘子树与石榴树。男孩仿佛一个闯入者,心怀愧疚地闻着花香,想象着到了晚上这里的香气会飘在空中,令人晕乎乎的。他甚至生出古怪的念头,想要久久流放在那片宁静的树林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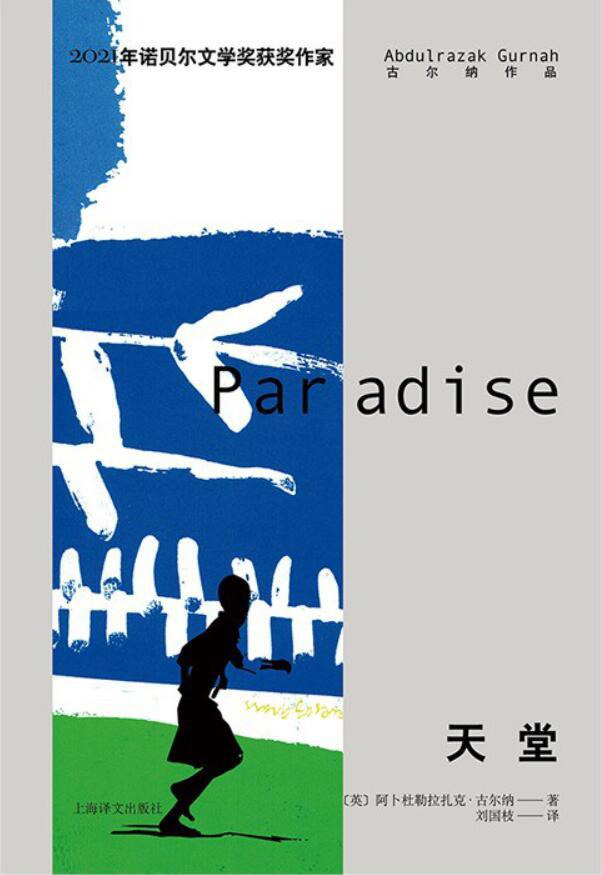
[英]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 著 刘国枝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2-9
花园代表着生命的富饶与勃发。男孩在院子里吃伙伴递过来的石榴,听到这样的介绍,“石榴集所有水果之大成,既不是橙子,也不是桃子,也不是杏子,却包含每一种水果的元素。石榴树是丰饶之树本身,树干和果实就像勃发的生命一样坚实而饱满。”那么杏子是什么味道呢?男孩问,伙伴没好气地回,没有桃子好吃。那么,我就不喜欢杏子,男孩坚定地思考。他被认为是有福分的,因为他在花园劳动时,所有他碰过的东西都能茁壮成长。
只是,在接下来的年月中,男孩发现富人的花园夜间飘着香气,偶尔传来乐声,种满水果树的美妙地方,对有些人来说更像是地狱,比如花园的园丁——那是一位身份为奴隶的“老头”。驯服与胆小听话的人们被困于美丽花园中,只能选择自我解救。男孩预备离开时,头脑里想的仍然是关于花园的比喻:那广阔的自由去处,白天不会有橘子树液的苦味,夜晚不会有茉莉花香,不会有流水的声音也不会有令人心醉的音乐,但不会更糟了。
狄金森的百合与北方
古尔纳将富人的花园同时看作天堂与地狱,对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而言,天堂就是花园本身。三十岁左右的艾米莉就厌恶社交辞令,也不愿待在客厅,宁愿前往野地,如诗里所写的,“一颗心,永远宛如裸足。”
她是隐居者,也是花园与温室的拥有者,她的花园可能比她的诗歌更为著名,当时的评论者也将她的诗比作植物,不过是柔弱而美丽的那种——就像温室玻璃墙里那些古怪的花,那些“根茎不在土壤里的兰花与空气凤梨”。
《狄金森的花园》为我们呈现了园艺对她而言的意义。花园带给了隐居的诗人另一种生命形态,同时也帮助她在更广阔的意义上融入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群体。花朵与树木构成了她的主题和修辞,如果不熟悉植物的习性,可能就无法理解她的诗歌。狄金森热爱花园里的鳞茎,水仙会生长多年,百合能够疯长,她热爱植物这样顽强的生命力。
在一首小诗里,她将百合的发育比喻为灵魂生长的过程:穿过黑暗的泥土——受教——百合一定能够成长。艾米莉宣称,她此生永远持守的戒条便是“想想百合”,这引用了典籍中百合既不劳苦也不纺线的比喻。在日常生活中,她也乐于选择较有美感的而非繁重的劳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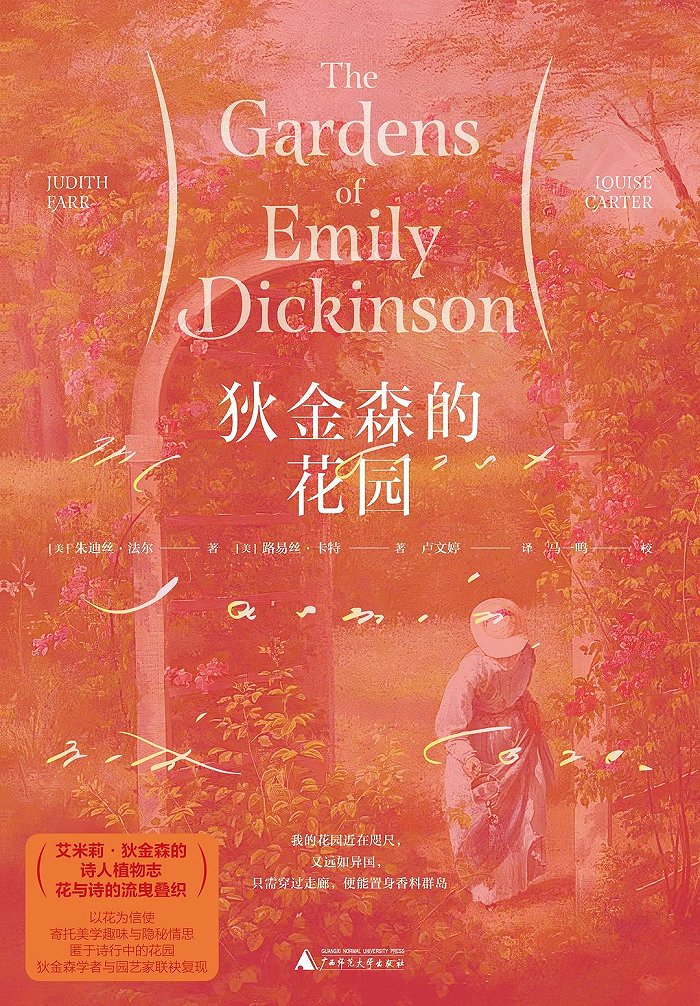
[美]朱迪丝·法尔 著 卢文婷 译
新民说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3-1
事实上,自然诗人都不足以形容艾米莉·狄金森,因为她总是通过花园来发表对人类世界的观点,这超出了自然诗人的一般内涵。而有意思的是,照料花园与对气候的关注也让狄金森产生了对北方而非南方的认同,她将自己的才华个性与北方联结,就像她年少时期最爱的丁尼生的诗里写的那样:明媚、热情、变幻无常,是南方/沉郁、纯朴、柔软温存。是北方。在她看来,南方象征着感官快乐,北方的艰苦更能激起创作的火花。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