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作家彭剑斌曾在小说集《我去钱德勒威尔参加舞会》和《不检点与倍缠绵书》中写下自己在贵州做业务员的经历,年轻人的困厄唤起了许多读者的共鸣。时隔七年写下新作《寂静连绵的山脉》,他却戏称,这是“一个中年男人无奈地开始了他的表演”,创作之初就烙上了商品属性。
日前,他和评论家张敞借新书出版之机探讨了写作者的心境转变,以及作为更宏观的社会背景的某种“现实主义回潮”。这种回潮来自何处?写作者应该怎样呈现底层生活?为什么好作家要在作品中“自我暴露”?

想象力“飞不起来”,写作有了表演性
文学编辑陈凌云最早从《西湖》杂志和黑蓝网上发现了彭剑斌。2019年,彭剑斌把旧作编成《不检点与倍缠绵书》,同名散文回忆了他在贵州跑业务、穿行在盘山公路上的生活,他在廉价旅馆里写小说,这些小说出现在了书的后半部分。
在陈凌云的观察中,最近国内文学出现了一阵现实主义回潮,“简直像是20世纪的文艺变革白过了。”但彭剑斌写底层人物时没有直接呈现现实苦难,而更倾向去写人的基本处境。他认为《我在北京送快递》的作者胡安焉和彭剑斌很像,“他们不是作为业务员或者快递员去写作,而是始终有阅读写作的意识。”事实上,在2012年写完《我去钱德勒威尔参加舞会》后,彭剑斌也曾做过一段时间快递员。

谈到现实主义的问题,彭建斌认为自己的《寂静连绵的山脉》中多了一些现实主义倾向,但他又对现实主义的人物形象塑造“恨之已久”,认为叙事应该有更广阔的空间,所以他对新作不太满意,只能打3星。
随着结婚生子后生活日渐安稳,彭剑斌自嘲想象力“飞不起来了”,心态也发生了改变,写作有了表演性。“最早写东西是出于热爱,完全没有作家意识,很多小说直到出版也没有发表或投稿。但这次却写得很痛苦,因为创作时就意识到它会变成商品,会拥有艺术之外的自我期待。”他此前在自述中坦诚地写到:“我受不了它(指《寂静连绵的山脉》同名短篇)流露出的批判姿态,我在写的过程中已经可悲地意识到自己不再锋利,于是像表演杂耍一样挥舞起了批判这柄正义之斧。”

彭剑斌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铸刻文化 / 单读 2023-3
文学是面对泥潭的墨镜,保护读者眼睛不被灼伤
在张敞看来,好的作家既要看到残酷,也要用文字去消解这种残酷,而不是采取俯视的目光。彭剑斌也是如此,“他写一个人‘躺在地板上穿着短裤像条虫子’,内心可能会有点厌烦和不适,但也恰恰是这种真实的视角体现了他的悲天悯人。”
陈凌云评价彭剑斌的小说有一种“紧张兮兮的幽默感”,比如写农村里青春期的小伙伴荷尔蒙无处释放,只能打来打去,形成了一种开玩笑的基调。彭剑斌认为,从堂吉诃德、伏尔泰到米兰·昆德拉和贝克特,这批外国作家有一个很好的文学传统,他们写的东西有时很搞笑,但里面确实有深刻的命题,读者能在快乐的同时不知不觉参与到严肃的思考中去。
“文学就像是面对泥潭的墨镜,你不能真的把读者的眼睛灼伤吧,某种程度上要保护读者。”他说,“世界读书日这天很多人要推荐些沉重的书目,我更希望通过写作把现实变成一个审美对象,让人能和生活愉快相处,再带着阅读小说的心情看待现实中那些坎儿。”
张敞还想到《卡夫卡传》里的一个场景,卡夫卡去找他的上司进行工作谈话,结果卡夫卡突然哈哈大笑,把自己从职员的状态里抽离了出来。写作者有时就需要这样,一个自己在参与生活,另一个自己超然地看着这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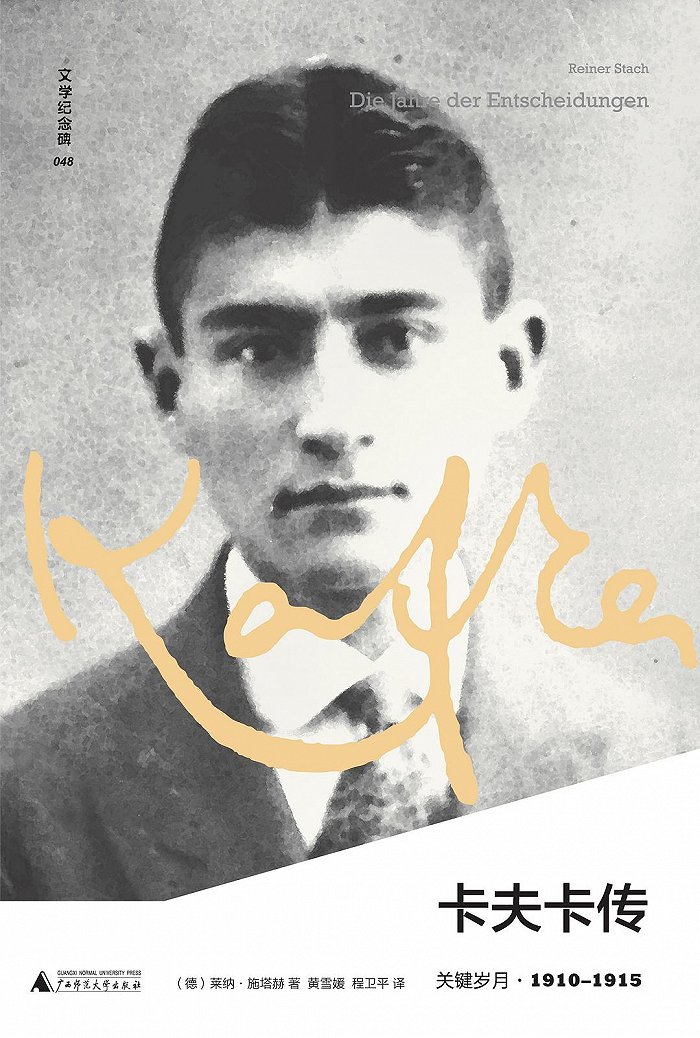
[德)]莱纳·施塔赫 著 黄雪媛 / 程卫平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4
另一方面,好的作者也必须克服自我暴露的耻感。彭剑斌把写作的过程形容为“把我自己在作品里生出来”,而这是很让人羞耻的,“卡夫卡就想过把自己的作品全部烧掉,因为这哥们实在太真诚和实在了,就像把自己剥光给人看一样。”
张敞补充道,如果在小说里看不到作家本尊,这个小说可能是失败的。“张爱玲的很多作品就有一种自毁倾向。据说李鸿章的后人都不太喜欢她,觉得她在暴露家族的丑恶。她也在散文里写父亲和母亲,他们很有可能因此跟她断绝关系。但如果做不到那么残酷和残忍,她也没办法成为小说家。”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