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界面新闻编辑 | 林子人
母亲,我们最亲近却又最捉摸不透的人,她饱含绵延不断的柔情,却又时刻让我们感到混沌。她总是,也将永恒影响子女的存在,而这种影响对女性而言尤甚。荷兰精神分析学家伊基·弗洛伊德就曾指出,“相比于男性,女性与他们的母亲间的纠葛更频繁。”
母女关系成为近年来文艺作品刻画的重要主题。它成为恒定的线索,串起了代际间的联系,也牵引出了一个又一个问题。正如《始于极限》所述,“女儿是母亲最激烈的批判者”,铃木凉美一次又一次通过反叛向自己的母亲证明“我和你不一样”。但在试图逃脱母亲的期待的同时,她也暗自希望得到母亲无条件的爱。
这样的矛盾也在众多热门影视作品中得到呈现。在《瞬息全宇宙》中,母亲伊芙琳与女儿乔伊穿越无数个宇宙,彼此纠缠、撕扯,却依旧在拥抱中结束;在《青春变形记》中,13岁的小美在进入青春期后开始厌倦无限迎合和顺从母亲的期待,她一面竭尽全力去实现母亲的期望,一面又感到痛苦。

似乎母女总在爱与恨中牵绊,她们共生,却又不断分离;她们之间有着浓烈的感情,而这份浓烈饱含着爱意与混乱。在母亲节到来之际,我们希望通过五本书,来重新思考母女关系,也借此思考我们生命中长久的疑问。
母亲的爱是“她会与我相斗,但我依旧将魂魄赋予给她”

喜福会是吴菁妹的母亲创办的神秘集会,四位来自天南地北的中国女人凑在一起,组一桌麻将,在一圈一圈的麻将中,将琐碎的日常诉尽。母亲去世后,吴菁妹短暂地成为喜福会中的一员,与三位母亲一同打麻将,也被告知母亲的遗愿——找到另外两个女儿。为了完成母亲这一遗愿,关于母亲的记忆再次被翻开,与此联结的,也是喜福会中四对母女的经历。她们的经历并不完全共享,但女儿似乎都曾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反抗母亲的约束。
在吴菁妹小时候,母亲不断尝试挖掘她身上潜藏的天赋,试图实现“神童梦”。最初,她也总是充满期待,希望自己成功,以换得母亲的宠爱,但当她一次又一次失败,并看到母亲失望的表情后,吴菁妹心中的某种东西开始衰亡,她决定“绝不会被母亲改变”,并理所应当地辜负母亲的期望,直至母亲去世。
韦弗利因讨厌母亲对自己的炫耀,不惜毁掉自己的国际象棋生涯,落一个鱼死网破的结局。丽娜则认为“入母亲慧眼的全是不好的部分”,恐惧让自己恋爱对象与母亲见面,因为她早已料到母亲嫌弃的眼神。
面对女儿们的反抗与恐惧,母亲们无奈却又洞若观火——她们也曾是女儿,再清楚不过那种“害怕被母亲所吞噬的恐惧与极度渴望母亲的爱”的感受,母亲知道“女儿会与我相斗,但我终将自己的魂魄赋予她,因为这就是母亲对自己女儿的爱。”

[美]谭恩美 著 李军 章力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7
在《喜福会》里,母亲形象或多或少体现出主流文化所寄予女性的传统品质,然而母亲的形象远比“母亲神话”要复杂和多样。在谭恩美的笔下,母亲是女儿捉摸不透,却依旧尝试靠近的人。
母女的共生幻想隐藏着仇恨
母女之间似乎总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悲壮感,从业经历长达五十年的荷兰著名心理学家伊基·弗洛伊德在《厄勒克特拉vs俄狄浦斯—母女关系的悲剧》一书中,用兼具理论与通俗的笔触,刻画了这种悲壮感。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认为父亲是中心人物的信念相反,这本书希望填补俄狄浦斯情节的空白,将希腊神话中“厄勒克特拉”的命运斗争作为原型,提出了“厄勒克特拉情节”。
在这一理论中,“女孩从一种同性别的爱的关系开始自己的人生,即从和她们的母亲的关系开始。直到后来,才加入对父亲的异性爱。”然而,对女性而言,和母亲的内在联结既可以是力量的源泉,也可能是混乱的根源。这一混乱来自于“共生幻想”与“不当分离”。
共生,意味着母亲与女儿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结,她们极端依赖、相互卷入。孩子努力满足母亲的要求,以向母亲诉说爱意;而母亲则以牺牲作为爱的表现。最终,共生意味着“双方都不能放松对彼此控制的缰绳”,孩子似乎成为母亲生命的延续,自己的欲望被消解,第三人也不再能够闯入共生主体中。

[荷]伊基·弗洛伊德 著 蔺秀云 译
漓江出版社 2014
在伊基·弗洛伊德看来,如果孩子一方面想要独立,发展自己的身份认同;另一方面,却也渴望和母亲重新统一,在这两难的困境中游移,她就可能一直处于“共生幻想”的状态中。而共生的另一极端则是分离与攻击,女儿为了逃离被吞没的恐惧,防御性地远离,甚至表现出厌恶与仇恨,但这也意味着另一种毁灭,毕竟独立与攻击并不等同,以仇恨式的摆脱作为手段,依旧意味着拉扯。
因此,对女孩而言,分离的变迁既是重要的,也是有负担的。一方面,分离是痛苦的,充满内疚情绪;另一方面,依赖母亲、弱小都是令人羞愧的,也是对自我感有伤害的。
母女一场,就是先学会依赖,再学会离开
然而分离依旧是母女关系中至关重要的课题。在心理学家简·戈德伯格看来,“在一步步通向成功分离的旅程中,我们逐渐发展出了安全、自信、完整的自我意识。”那么,应当如何实现分离呢?简·戈德伯格通过讲述自己与母亲和女儿的关系,重新思考这一问题,试图定义健康的母女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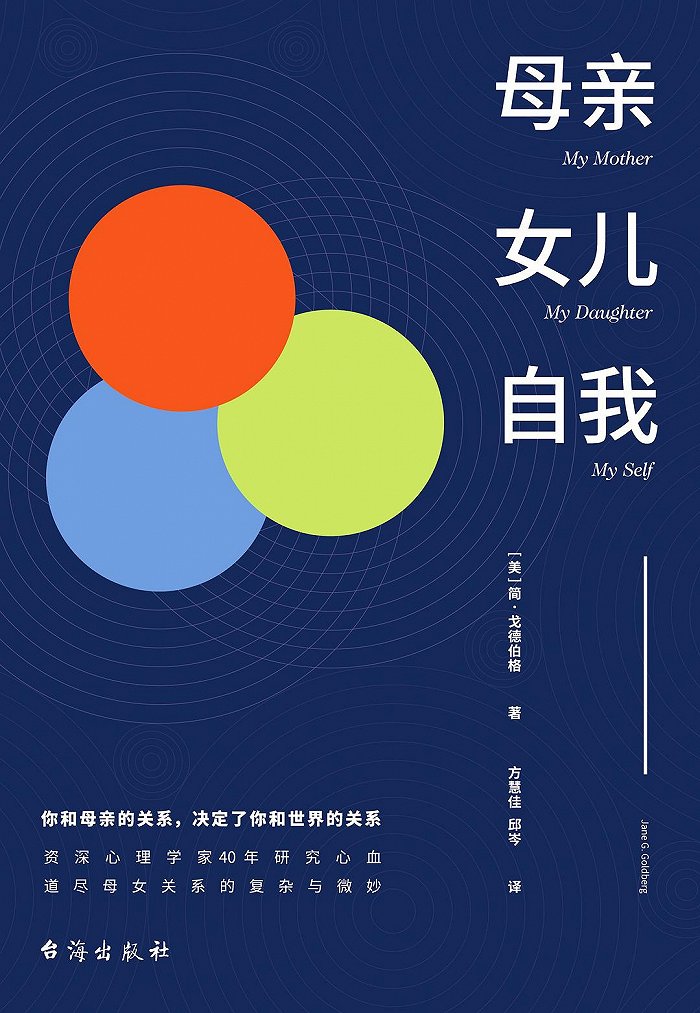
[美]简·戈德伯格 著 方慧佳 邱岑 译
台海出版社 2023
学会对母亲说“不”,是孩子实现分离的第一步。从孩子口中说出的一个个“不”代表的并不是对母亲的消极回应,而是孩子为成为独立个体而付出的努力,尽管这时常让母亲感到沮丧,但母亲应当学会将孩子说出的“不”视为她正在不断扩充的词汇库中尤为宝贵的一个词。
孩子放弃对全能母亲的幻想,在与母亲的亲密关系形成后,适时地放弃它,为必须的分离做准备,则是分离第二步。
除此以外,作为母女关系的第三人,父亲对于分离也十分重要。戈德伯格认为,父亲应当承担起改变母女间依赖关系的任务,帮助切断她们之间的心理脐带,割裂母女的二元关系,并转化为构成家庭生活延续的三元关系。只有摆脱“甩手掌柜”的形象,积极地与家庭互动,才能够真正构成良好的亲子关系。
追求“共生与分离”,是必定矛盾重重的,但“每一位母亲与孩子的终极挑战就是从最初的肉体共生中得到升华,欣然迎接由此而生的独立个体”。
成为母亲,也可能会后悔
“不错!我当初就不该生你下来!”母亲没说这句话,但从母亲的极冷的目光里,六六分明读到了。
六六总感到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人。她是家里的第六个孩子,是母亲的幺女,但母亲对她的态度她总是暧昧不清难以形容,好像她是别人家来串门的孩子一样,从不宠爱,绝不纵容,管束极严却又十分周到。
大部分情况下,母亲和六六都很难朝对方露出一个笑容。母亲不愿意让六六上学、不记得六六生日、对六六有意冷漠;而六六则总是会挑母亲的毛病,在她眼中,母亲是一个粗野甚至有些丑陋的女人,总是出口成脏且脾气火爆。
岁月逐渐在六六和母亲之间砌了一堵墙,随着六六自我意识的觉醒,她越来越想要越过这堵墙,去解开自己命运之谜,也走进母亲封闭的心。六六逐渐得知,自己是于饥荒年代出生的,在那个众人横死街头的年代,母亲与自己却从一段奇妙且荒谬的经历中存活下来。
六六于是明白了,原来母亲并非没有注意到自己未被填满的心,只是她也不能给予更多的安抚,六六的存在本就是母亲的创伤。后来,六六执意要逃离母亲,她虽然理解了母亲,却依旧感到疼痛,于是她如同母亲当年一般,选择出逃。在这里,母亲与六六实现了从共生到分离。
《饥饿的女儿》开篇刻印的是“献给母亲”,这当然不是献词,但作者虹影确切地通过望向母亲,向我们展示了母性的复杂,正如我们知道人性复杂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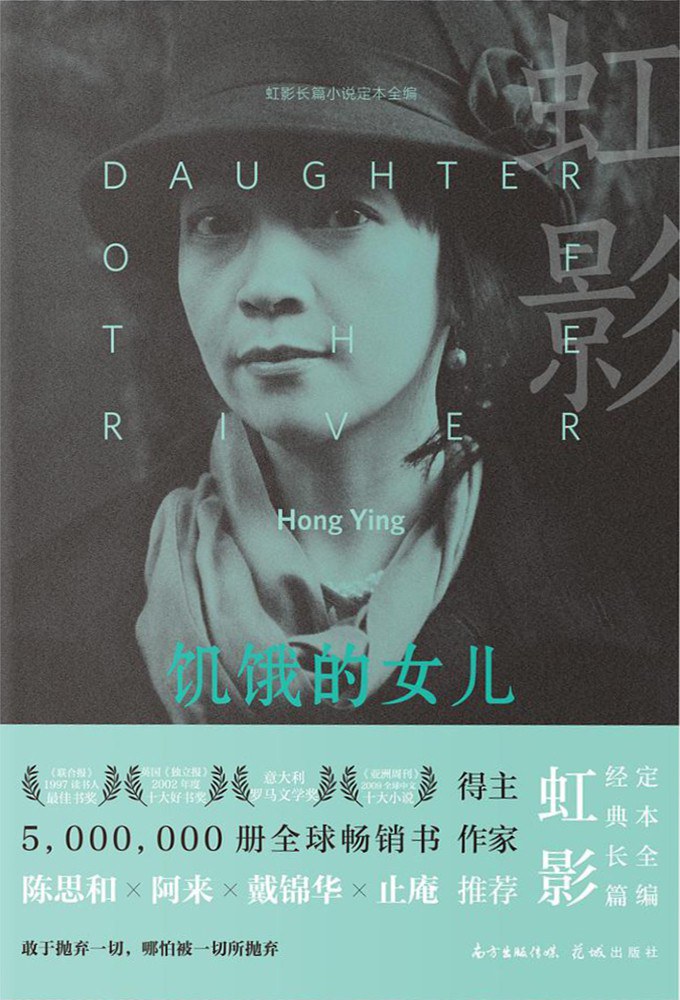
虹影 著
花城出版社 2022
这正是以色列社会学家奥娜·多纳特在《成为母亲的选择》中试图向我们展示的观点之一。她认为,“我们应当理解,母亲们也是人,可能有自觉或不自觉地伤害、虐待甚至杀人的情形。”除此以外,多纳特更是将“后悔”作为讨论的中心,让我们进一步了解母亲的困境:她们被要求不能有“越轨”的渴望,然而她们偶尔也会想要将母亲的身份从人生经历中抹去。作为女性,“你绝对会后悔没有生孩子”是经常会听见的话,但事实是,成为母亲,也总会感到后悔。然而,后悔却成为她们不敢表露的情绪,在多纳特看来,不敢表露“后悔”的情绪,与社会期待相关。
这种社会期待总是以两种面貌出现:第一类是“自然论”,它是一种基于生物学上的天命论,鼓吹“女性除了成为母亲以外没有别的选择”;第二类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以及后女性主义的论述”,在这类论述下,人们往往认为,如今女性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她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生儿育女,因此,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是应该的。然而事实上,“自由选择”只不过是假象,这个概念天真地忽视了不平等、强迫、意识形态、社会控制及权力关系。这些隐形的规范弥散在生活的各处。
社会期待“好妈妈”形象的同时,也勾勒出了坏妈妈的轮廓。坏妈妈意味着永远不能对生下孩子感到后悔。在多纳特的采访中,许多母亲都表示她们爱自己的孩子,但是恨自己的母亲身份,这是一种对“母亲功能性的抗争”,但另一方面,也再次印证“坏妈妈”是不被允许的。人们不但将女性的后悔诠释为缺乏母爱,也把后悔和对孩子的伤害挂钩,“这导致母亲们不愿在未经过滤的情况下讲述她们的感受,我们永远无法更全面地理解她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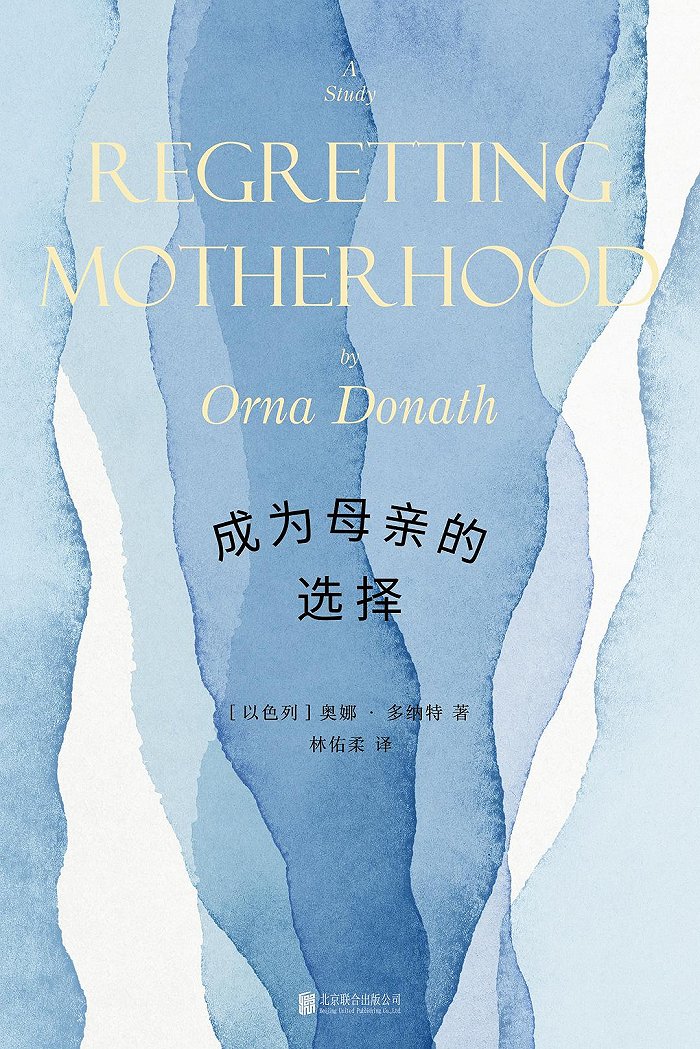
[以]奥娜·多纳特 著 林佑柔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2
“后悔也许可以协助我们推翻过去深信不疑的概念,例如:母亲就是不断为他人付出的角色,母亲的幸福只和孩子的幸福紧连在一起。而后我们得以认知到母亲也是独立个体,拥有自主的身体、思想、感情、创造力和记忆,并能判定眼前这一切是否值得。”多纳特在《成为母亲的选择》中写道。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