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美国最高法案在上个月末做出历史性判决,裁定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平权行动招生政策违宪。该案件始于2014年由“学生公平录取组织”(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在波士顿联邦地区法院对哈佛大学提起的诉讼,指控哈佛大学在本科招生中歧视亚裔美国人,违反了《平权法案》。哈佛大学于2019年和2020年先后两次获得胜诉,但原告坚持将案子打到了最高法院,该案终于尘埃落定,并极有可能对美国高校乃至职场的种族版图产生深远影响。
《纽约客》记者Jay Caspian Kang在五年时间里跟踪报道了上述案件,他指出了一个关键问题:虽然亚裔美国人是诉讼的核心——更确切而言,平权行动招生政策的反对者中有不少华人的身影——但在法庭内外的公共讨论中,他们却奇怪地缺席了。无论是在法庭内还是在媒体报道中,亚裔原告都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值得注意的是,“学生公平录取组织”没有让亚裔学生出庭作证);为平权行动辩护的评论者几乎从未正面回应亚裔学生是否真的在招生过程中面临歧视,即使他们指责原告是一些被一位保守派法律活动家(指爱德华·布鲁姆)欺骗的棋子。
在大法官杰克逊的29页异议文件中,“亚裔”只出现了三次,她详细阐述了黑人的种族歧视历史,却没有提及亚裔美国人经历的种族歧视史,无论是19世纪被私刑处死的华人移民,还是《排华法案》,以及二战期间遭到大规模监禁的日本移民。“如果一个社会希望在正视历史的基础上做决策——我认可这一观点——难道曾经被美国驱离的群体没有权利与那些这么做的群体区别开来么?他们当下对歧视的主张难道不值得任何严肃对待么?”Kang写道。
种族主义被定义为“白人”与“黑人”的问题——这种叙事框架在哈佛大学校史《真理:哈佛大学与美国经验》中也有所体现。根据安德鲁·施莱辛格(Andrew Schlesinger)在该书中的记述,这所在1636年由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大议会批准成立的大学于1865年秋季招收了首位黑人学生,哈佛在种族战线上取得的种种进步主要由该校对黑人学生和犹太人学生的限制如何一步步解除确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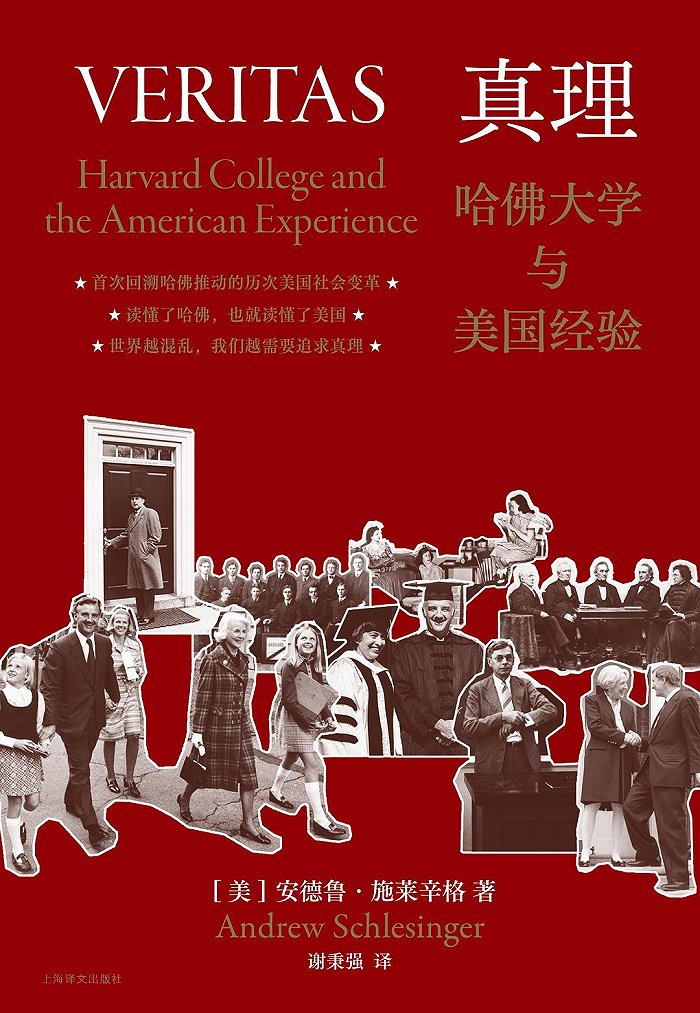
[美] 安德鲁·施莱辛格 著 谢秉强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3年
那么亚裔——特别是华人——在美国种族主义的图景中究竟位于哪个位置呢?他们是否真的是“优秀”的少数族裔,并能因此从种族主义强加于非裔群体的种种不公正中豁免,而今反倒因为反种族主义的“矫枉过正”而遭到利益受损呢?
华裔美国移民的复杂历史
美国历史学家孔飞力(Philip A. Kuhn)的《他者中的华人》为我们理解上述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孔飞力指出,华人移民在全球各个移民社会的生存环境因统治国的特性而呈现出天壤之别。中国人最初抵达北美时,当地政府正准备废除奴隶制,“在美国,当地人对于奴隶制度的深恶痛绝,却在对待中国移民的问题上起着奇怪的、具有讽刺意义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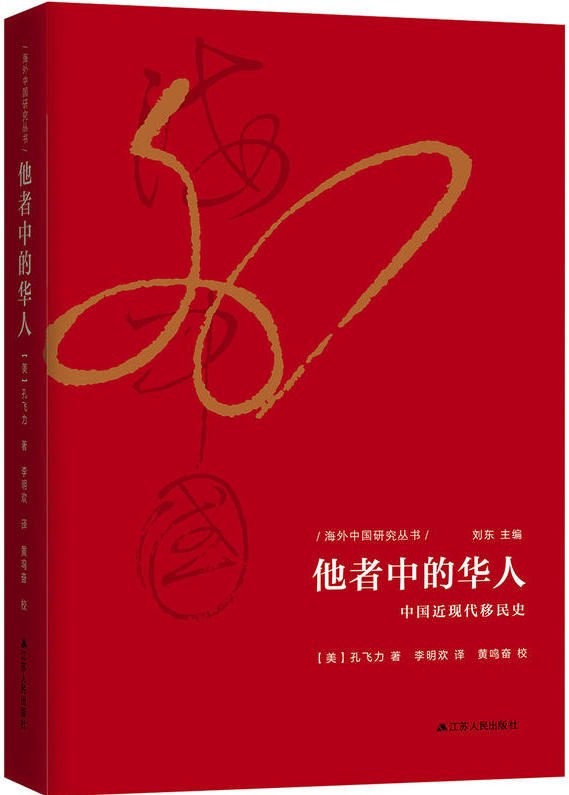
[美]孔飞力 著 李明欢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8年
1848年,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消息一经传出,在短短一年内就有10万新移民(绝大多数为男性)涌入加利福尼亚。当时,华人在加利福尼亚的总人口中约占9%,在淘金热的激烈竞争中,他们发现自己更容易遭受攻击,公开的和私下的排华行动从未停止:华人被驱离尚未被开采的新采矿区,只能去那些白人已经开采过并且抛弃了的地区进行再度开采;当局确立了一个又一个法案,对华人课以歧视性税收,剥夺他们的公民自由(包括出庭为不利于白人的事件作证的权力、参与陪审团的权力、投票和拥有土地的权力),华人在加利福尼亚的人身和财产都得不到任何保障。
1882年《排华法案》出台的决定性因素是白人工人日益上升的敌意——它首先影响了加州的州政治,随后蔓延到全国层面。孔飞力在书中写道:
“早在19世纪60年代,排华骚动就已经在城市工业领域产生,特别是在如同卷烟、制鞋类的轻工业领域,以及那些半熟练工作岗位,排斥华人工人的现象尤为严重。在这些领域,华人主要是与下层白人劳动大众发生直接竞争,事实证明,华人参与工作机会竞争而引发的矛盾,甚至比当年华人因为参与淘金而引发的白人的敌意,还更加严重。”

孔飞力认为,白人反对华人有若干原因。首先,白人劳工阶级存在身份焦虑。北美社会的种族鄙视链在白人群体内部实际上也存在——在所有白人移民族群中,爱尔兰人因其另类的生活方式和天主教信仰而备受歧视和虐待。在美国东部地区,爱尔兰人发现自己与那些获得自由的、或者从南方出逃的黑人一样位于社会阶梯的末端,他们的策略不是联合黑人共同抗争,而是将黑人作为难得的工作机会的竞争者加以反对攻击。同样的心态也出现在了白人劳工阶级对华人的态度中。
其次,白人对华人的排斥也与他们对奴隶制的仇恨和恐惧有关。在《排华法案》出台之前,华人移民常常因其特殊的社会组织方式被指认为“苦力”或“奴隶”,华人移民的迁徙过程被认为与奴隶贩运相差无几。比如1852年加州议会提出,华人移民无一例外都受制于其雇主,如果不能尽快解救他们,那么准许使用准奴隶的“苦力制”将蔓延全国。
而实际上,华人移民是通过契约劳工制移民美国的——他们与某雇主签订契约,承诺在抵达后为其工作一定年份,以偿还雇主为其预付的远洋路费。这种契约制在17-18世纪美洲殖民初期阶段实际上司空见惯,绝大多数早期离开英国来到美洲的移民都无法支付漂洋过海的船费,通过契约制才得以成行。直到非洲奴隶制开始超越并最终取代了契约制,“自愿”移民与“非自愿”移民之间的界限才越来越与种族界限重合。在白人劳动者之中,“自由劳动者”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殖民地法律也不再允许任何“以强迫劳役偿还债务”的现象存在。华人移民的迁徙与工作方式,也因而显得越来越陌生。
“奴隶制”的污名还与美国普遍存在的对待非白人的种族歧视态度有关。对黑人的敌视从施行奴隶制的南方州蔓延到西北地区,主要是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和伊利诺斯州。1802年,俄亥俄州率先通过了《黑人法》,随后该法在所有新建立的西部各州都获得通过。《黑人法》排斥所有非洲人,无论他们是奴隶还是自由人,规定在当地定居的黑人没有投票权,也不能出庭作证,不能与白人女性通婚。对于大多数白人定居者而言,与对黑人发自内心的仇视与恐惧相比,他们对奴隶制的厌恶只能排在第二。加州的白人移民不少来自中西部各州,带来了这种种族主义意识,向往维持一个纯粹由白人组成的社会。因此,在他们关于驱逐华人的提案中,诸多措辞用语与《黑人法》如出一辙。

1882年5月6日,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在10年内禁止华人劳工进入美国(不包括商人、教师、学生、旅行者和外交人员),并禁止所有华人移民入籍美国。它不仅是美国第一部大范围限制移民的法案,还是第一部根据种族和社会阶级限制移民群体的法案。对华人的结构性排斥一直持续到1943年《排华法案》的废除(尽管如此,当时仅仅给予华人每年105人的移民配额),排华行动从那时开始才慢慢有所收敛。
196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哈特-塞勒法案》,取消了民族来源限额体制,给予每个国家2万个移民配额(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地区和中国台湾地区每年各享有2万配额)。另外,法案允许美国公民的“直系亲属”(包括配偶、未婚子女及父母)通过家庭团聚条款移民。孔飞力指出,中国的新移民给原先的美国华人社会带来了重大变化。在这些来自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以及1980年之后大幅增加的中国大陆新移民中,不少人是专业人士、技术人才,接受过高等教育,或具备投资能力。其中,25岁以上年龄群的平均受教育水平高于美国全社会的同一比例,“提升”了华人社会的总体水平。
这一事实提醒我们注意,包括华人移民在内的亚裔美国人内部存在显著的移民代际和社会经济背景差异。相对而言,新移民在一个种族主义被批判反思的时代落地生根,他们的个人成功与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性提升更容易被认为是个人奋斗的结果,更少考虑到制度性制约可能对有色人种的生存状态产生的种种影响。美国历史学家李漪莲(Erika Lee)认为,平权行动的争论揭示了华裔美国人的内部分裂:在种族和大学招生问题上变得政治化的不少为第一代中国移民,他们在政治倾向上更加保守;然而大多数亚裔美国人,包括老一辈的华裔美国人,都支持平权行动。
经济竞争中谁成为了替罪羊?
回顾排华运动的历史,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值得注意。孔飞力指出,排华运动的巅峰时期是19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也是美国经济萧条的时代。当时在美国东部和中西部工业城市,工会组织蓬勃发展,反抗大资本家的罢工运动此起彼伏。“这一时期仇视华人的排华运动,与当时资本家们普遍加重了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密切相关,铁路公司的情况尤其严重,”孔飞力写道,“在加州,所谓‘华人问题’与工人失业、工资下滑、破坏罢工,以及工人阶级的诸多不满和抱怨相关联,故而也就赋予了‘反苦力主义’以令人尊敬的而且实际上更是英雄主义的表象。”
无论是修建铁路还是垦荒耕种,当时大多数华人从事的是那些白人不愿意做的艰苦工作,华人吃苦耐劳且能接受低廉的薪资,对资本家而言是再合宜不过的劳工。在制造业领域,不少华人进入卷烟和制衣行业工作,因为那些在与美东大企业竞争中处于弱势的企业特别需要降低劳动力成本,因此就很愿意雇佣华人劳工。农业和渔业也有华人活跃的身影,一些华人向白人大农场主租赁土地,再通过兄弟会关系去雇佣与自己说同一种方言的老乡,从事农业种植。1920年前后,在加州农业地区定居劳作的华人已达数千人。
华人招募华工的方式和他们对低工资工作的接受,让白人工人深感威胁。资本主义制度通过大批引入华人劳工而压低工资,激化了白人工人与华工的矛盾,这与仇外心理、对“奴隶制”的社会焦虑感交织在一起,共同引发了排华运动。孔飞力指出,“排华运动是由多个方面的引擎共同发动的,但是,所有这些引擎的动力都源于根深蒂固的种族仇视,源于他们深埋在心中的狭隘的部族主义。当他们缺乏安全感时,当他们在经济上产生恐惧时,就把弱势群体当成了替罪羊。”
工人群体内部的彼此攻讦是精英阶层乐见的结果。正如女性主义学者、纽约州霍夫斯特拉大学荣休教授西尔维娅·费代里奇(Silvia Federici)在《凯列班与女巫》中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欧洲统治阶级占有和调动规模空前庞大的廉价劳动力,为了让劳动力顺从资本主义的制度安排,统治阶级将劳动者“分而治之”,让对处于等级下方的劳动者的剥削自然化,“(原始积累)也是工人阶级内部差异和分化的积累。借此,建立在性别、‘种族’和年龄基础上的等级制度成为阶级统治和现代无产阶级形成的构成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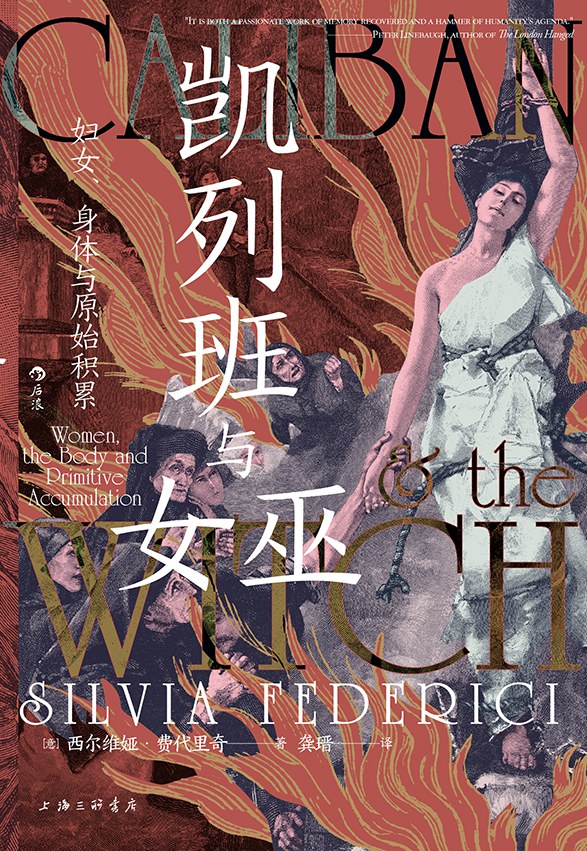
[意]西尔维娅·费代里奇 著 龚瑨 译
后浪·上海三联书店 2023
而今,工人群体内部最显著的等级制由教育水平决定。“技能性”劳动者(有大学学位的劳动者)与“非技能性”劳动者(没有大学学位的劳动者)的差距不断拉大。行为基因学家、美国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分校临床心理学教授凯瑟琳·佩奇·哈登(Kathryn Paige Harden)注意到,在当今的美国,一个人是“富人”还是“穷人”,越来越取决于是否拥有大学学位。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处于顶端的0.1%的美国人的收入增长了400%以上,但1960年代以来,没有大学学历的美国男性的实际工资没有增长。
上大学——特别是上精英大学——带来的“技能溢价”是如此关键,足以让所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拼劲全力将孩子送进大学校门。我们有理由认为,反平权行动的这部分亚裔美国人是经济不安全感激发了某种狭隘的部族主义,把黑人与拉丁裔当作替罪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种族与宪法研究学者Ian Haney López认为,在一个白人相对黑人享受巨大特权的等级制社会里,“我在等级制的哪个位置”是所有人都暗自思忖的问题,而通常情况下,所有人都会希望自己不在底部。这问题对来自欧洲以外的移民来说尤为棘手,他们往往需要为了融入美国付出更多努力。
“非欧洲血统的人认为,‘我就要靠近肤色线中白人的那一端’,这种人并非罕见。”在López看来,这正是爱德华·布鲁姆所利用的心态,通过贩卖靠近白人与权力的承诺,位于政治光谱右端的一部分亚裔美国人正在变得极端化,“他告诉他们——‘嘿,亚裔美国人,你们也看到了黑人和棕人要求的公正与融入(equity and inclusion)是对你们的威胁。与种族融合的白人反对者、与对平等(equality)心存怀疑的白人联合起来吧。”

李漪莲指出,21世纪的亚裔美国人在美国社会处于一种非常矛盾的地位:他们在经济、学术和政治上取得了巨大进步,却仍然容易受到全球经济变化和政治斗争的影响;他们从新的权力和特权地位中获益,但也依然是仇恨犯罪和微侵犯(microaggressions)的受害者。“模范少数族裔”叙事美化了亚裔的生活经验,让部分亚裔忘记了,“9·11”事件如何让一些亚裔美国人从“模范少数族裔”转变为“可疑危险的移民威胁”;新冠大流行的爆发又如何激发了针对亚裔的仇恨言论和暴力事件。美国对亚裔美国人的包容性依然无比脆弱,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值得反思的是,在种族主义问题中“置身事外”将使华人陷入怎样的困境。
参考资料:
【美】安德鲁·施莱辛格.《真理:哈佛大学与美国经验》.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
【美】凯瑟琳·佩奇·哈登.《基因彩票:运气、平等与补偿性公正》.辽宁人民出版社.2023.
【美】李漪莲.《亚裔美国的创生》.中信出版集团.2019.
【美】孔飞力.《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
"Why the Champions of Affirmative Action Had to Leave Asian Americans Behind", The New Yorker, June 30, 2023.
“How Affirmative Action Myths Divided People of Color”, NPR, July 2, 2023.
https://www.npr.org/2023/07/02/1183981097/affirmative-action-asian-americans-poc
《“猎巫”从未远离:厌女是如何成为一项社会工程的?》,界面文化
《为什么特朗普的“移民新政”是<排华法案>的一再回响?》,界面文化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