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月,罗伯特·考克尔(Robert Kolker)为《纽约时报杂志》撰写了一篇讲述两个作家打官司打到天昏地暗的故事。表面上看,二人的纠纷是围绕剽窃展开的:唐·多兰指控索娅·拉尔森窃取了她在现实生活中捐赠肾脏的经历,并将其用作某短篇小说的蓝本。
考克尔的《谁是艺术损友?》一文引爆了社交媒体,因为它不止关乎两个名不见经传的作家之间不为人知的剽窃之争。凭借其高超的报道技巧,考克尔捕捉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东西,即我们对生活经历的所有权太过单薄,以及小说写作中的“吸血鬼”现象。
在文学文化的镜厅里,安德鲁·李普斯坦(Andrew Lipstein)近来出版了一部讨论艺术损友的小说《最后手段》(Last Resort)。没人会指责李普斯坦抄袭考克尔的文章——他的小说早在纽时文章面世之前就已完成——但《最后手段》对考克尔探究的问题进行了不可思议的戏剧化处理。显然,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对本真性(authenticity)充满焦虑的时代。
故事始于每个作家都怀有的梦想:迦勒·霍洛维茨吸引了一位大人物的关注,此君认为霍洛维茨的手稿非常出色。这也许是霍洛维茨结束为某个他完全弄不懂的发薪日贷款app而工作的绝佳机会。 他以体操选手一般的灵敏跨越了高雅与低俗的鸿沟,创作出了那件最受热捧的珍宝——一部以丑闻为主题的文学小说。其情节相当“劲爆”,关乎一对在希腊小岛上度蜜月的美国情侣与一名垂死女子之间的风流韵事。
在达成交易的优雅午餐会上,霍洛维茨听闻他的处女作将会受到包括泰芮·葛萝丝(Terry Gross,NPR知名广播主持人)以及塞斯·梅耶斯(Seth Meyers,深夜秀主持)在内所有人的喜爱。纽约出版社的出价很快就从4.5万美元、8.5万美元一路飙升到了22万美元,而“年度最伟大商业文学成就之一”的称号也必将落到霍洛维茨头上,这对于一个27岁的作家而言也算是个好兆头。
不巧的是,这场改变人生轨迹的大胜还有一个小障碍:霍洛维茨的小说大纲乃是从一位名叫阿维的大学老友那里“借来”的,后者也曾写过一篇自己在希腊的浪漫冒险故事。回想一下,霍洛维茨本来应该跟阿维通个气,承认这个故事是其新小说的灵感来源。起码霍洛维茨应该把里面的人名改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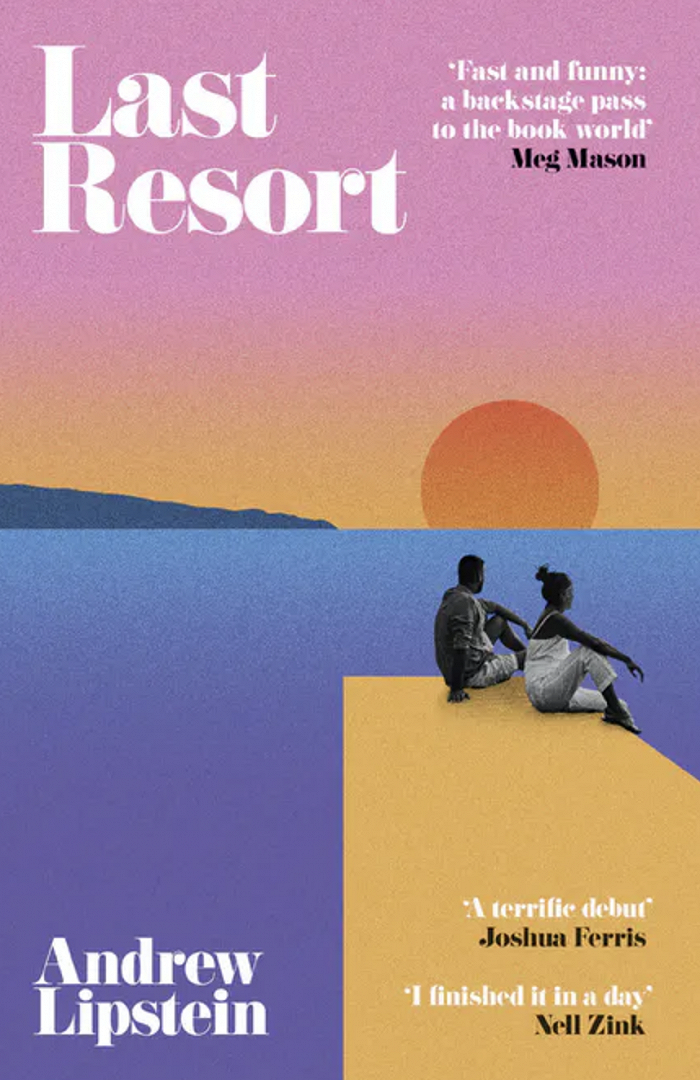
如果你想知道作家的想法从何而来,那《最后手段》读起来会很有意思。如果你是作家,那《最后手段》业已出版这件事想必会让你妒火中烧。任何有创造力的人胸中深藏的黑暗可怕一面,在书页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些令人尴尬的事实也许会推翻种种以文学创新之名义提出的光鲜观点。
霍洛维茨这部小说的叙事带有一种忏悔与自我辩解相交织的口吻。李普斯坦批驳了文学野心的自负与妄想,而霍洛维茨则点出了令作家把自己设想为只关心艺术而对金钱或名誉毫不在意的一些心理花招。他还揭露了小说家忽视、掩盖乃至于否认其资料来源的作为可能会达到何等程度。
随着霍洛维茨的处境日趋尴尬,他的腔调也愈发令他变得像一个勉力保持冷静的人。“这不过是一部小说,正如历史小说也还是小说,”他在纽约散步时这样告诉自己,“事实都只是脚手架,作品竣工后你立马就会抛弃它们。”可惜的是,这个隐喻在技术上并不为真,甚至在隐喻层面上都不为真。
霍洛维茨一面假设阿维正拿起一本他的小说,一面想道,“我已经把他的故事改得面目全非,他就算读到了,又能在差异之外发现什么别的东西吗?”他定了定神,坚信自己是无辜的,即便他会在谷歌上疯狂搜索“剽窃”字样,并将他的小说与阿维的故事输入某个检测相似程度的电脑程序。好消息:“2%的相似性。”
“我觉得这是无罪释放,”霍洛维茨装出一副松了一口气的样子。
然而,即使在这些自信爆棚的时刻,霍洛维茨还是忍不住想得到赞美,并幻想着受害者(指阿维)的感激之情。“他的角色并没有足以为其当下自我增光添彩的背景故事,”霍洛维茨想道,“他的情节也谈不上跌宕起伏。我想知道他能否意识到这一切,以及是否能认出我手稿背后的思想,还有技艺——最要紧的是,我想知道他对这本书的整体观感。”
事有凑巧,此时阿维恰好发来了短信:“明天有空出去喝个咖啡吗?”
这就很尴尬了。
伴随着这一让人把心提到嗓子眼的时刻,《最后手段》也发展成了一出有关文学名望的荒唐喜剧。这只是李普斯坦的第一部小说,但他却已经对一名作家在激烈竞争中赖以发财——或恶名远扬——的招数有了一针见血的理解:集书评、宣发、签名售书、Goodreads评论以及浮夸的作者简介于一体的组合拳。
各方的反应尽在于此:《纽约时报》的头条很机灵但却有些牛头不对马嘴(“E.L. 詹姆斯,遇见E.E. 卡明斯”),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在《纽约客》上的大脑宕机之笔(“评论的前三分之一甚至根本就没提到这本书”),还有绿光书店人头攒动的读书会,在那里作家可以“表现出忘我的姿态,和被邪教洗脑到崩溃阶段的样子差不多”。
但《最后手段》归根结底关乎“我们口头上宣称自己需要些什么”与“我们愿意自担风险去追求些什么”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任何人都有碰上这种冲突的可能,哪怕我们并没有剽窃过朋友的故事——暂时还没有。
(翻译:林达)
来源:华盛顿邮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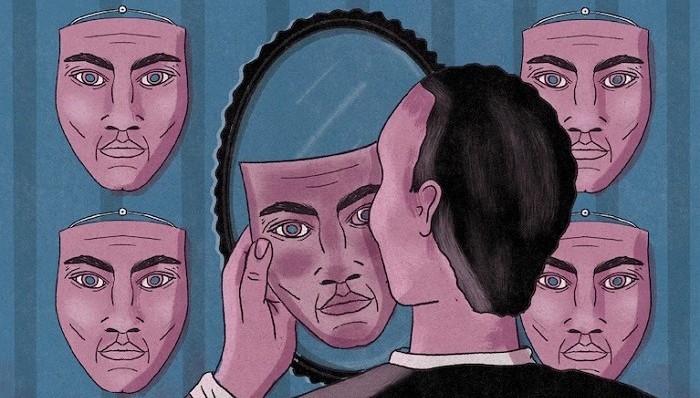
评论